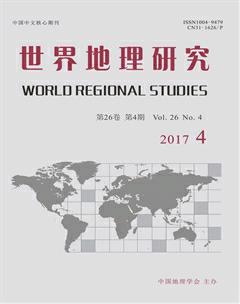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王舒馨 杨永春 史坤博
摘 要: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②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③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④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乌鲁木齐市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因素[1]。而且,制造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坚实基础,是“链式反应”的起点,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2]。不同类型制造业在城市各区域形成集聚,制造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要素的运行效率和区域空间格局[3],城市制造业空间结构的演变也是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动力[4-7]。因此,对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和演变的研究无疑是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国外对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本国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探索,如制造业呈现明显的郊区化趋势[8-9];二是制造业跨国迁移研究[10-11]。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港澳台资投资大陆地区,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城市制造业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国内学术界对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主要关注了城市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演变及其机制。贺灿飞等[12]研究了北京市外资制造企业的区位特点,发现市场机制对北京市外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张晓平等[4]、孙磊等[13]对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影响着北京市制造业的空间重组;刘涛等[14]研究了北京市制造业分布的圈层结构演变,认为电子电气和金属与矿物类产业、私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是北京市制造业圈层结构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曹玉红等[15]研究了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演化,发现都市型工业企业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王俊松等[16]通过研究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吕卫国等[17]、蒋丽[18]、郭杰等[19-20]则分别研究了南京、广州、成都和兰州等地的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成因。
伴随着制造业向西迁移,西部地区城市包括乌鲁木齐、银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制造业发展迅速,其在西部城市内部的空间重构进程日趋显著。但我国的此类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都市区[12-18],对西部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的研究相对较少[19-20],因此选取西部典型城市进行制造业空间格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交通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城市。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在全市经济比重中地位显著,2014年,乌鲁木齐市第二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为38.1%,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总产值167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429亿元的69%。因此,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以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烏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展开研究,以期为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来源于2004年新疆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2008年新疆经济普查数据和2013年乌鲁木齐市经济普查数据,涵盖单位名称、所在区县、街道(乡镇)、行业代码、成立时间、注册资金、年末从业人数等信息。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中制造业分类代码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1]75号)汇总出乌鲁木齐市3个年份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最终整理出2004年1549家、2008年2111家、2013年2550家企业信息,并进一步将样本根据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进行统计,其中2004年、2008年按照营业收入分类,2013年因数据缺失按照从业人员数进行分类(表1)。根据制造业行业特点并参考郑国[3]的分类标准,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29个行业类别归并为四大类,分别为都市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表2)。
1.2 空间单元划分
由于经济普查数据均以街道(地区)办事处、镇和乡为最小空间单元进行统计,数据资料准确性高,故选取“街道(乡镇)”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2004年至今,乌鲁木齐市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包括街道(乡镇)行政单元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变化。如2007年,乌鲁木齐市成立米东区,由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市和乌鲁木齐市的东山区合并而成,增加行政区域面积3407.42平方公里;2011年初,原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与原乌鲁木齐新市区(简称新市区)实行“区政合一”,并将原乌鲁木齐县两乡一镇(青格达湖乡、六十户乡、安宁渠镇)增划并入,由新市区管理。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对比度,本文以2013年的街道(乡镇)为标准,对部分街道(乡镇)进行合并,使合并后的街道(乡镇)与历年普查资料的行政区划标准保持一致,并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以及相应的属性数据。基于上述界定,乌鲁木齐市8个区县共包括105个街道(乡镇)基本单元。本文中的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指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和新市区。
1.3 研究方法
1.3.1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Gi将某产业分布与其他产业对比,是使用最广泛的系数之一。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如果产业在各区域平均分布,基尼系数为0,如果产业集中在一个区域,基尼系数为1[21]。计算公式为:
1.3.2热点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的重要指标[22]。空间对象的属性值的相似性与其位置的相似性存在一致性称为空间依赖性[23]。本次研究采用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中的空间“热点”分析方法(Hot-spot Analysis(Getis-Ord Gi*))。Getis-Ord Gi*是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高值和低值,可以用地区可视化的方法揭示“热点区”和“冷点区”,通过计算Z得分和P值,得到高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发生聚类的位置。对于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正的Z得分,Z得分越高,高值(热点)的聚类就越紧密;负Z得分,Z得分越低,低值(冷点)的聚类就越紧密。P值表示所观测到的空间模式是由某一随机过程创建而成的概率,P值越低表明观测到的随机空间模式的概率越低,Z得分和P值都服从正态分布。相关公式参照已有参考文献[23-24]。
1.3.3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认为在研究区域内的任何一点都有一个密度,而不仅仅是在事件点上,即地理现象可以发生在空间任一位置,但是不同位置发生的概率存在差异[25]。本文采用ArcGIS软件中空间分析工具里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将乌鲁木齐市各街道(乡镇)制造业分布抽象为点,通过计数一定区域内点事件数量,进行核(Kernel)估计,得到一个K值,K值越高表明制造业空间上越聚集。根据核密度估计定义:对于从分布密度函数p中抽取的样本数据x1,x2,…,xn,采用核函数估计p在点x处的核密度p(x),选用Roren-blatt-Parzen核函数进行估计,计算公式为[26]:
2 制造业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2.1 制造业企业集聚特征
基于基尼系数对乌鲁木齐市制造业及其四大产业类别的集聚程度进行综合测度(表3)。总体来看,乌鲁木齐市制造业基尼系数2013年>2008年>2004年,说明从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集聚程度在逐渐变大。这与前人对无锡制造业时空集聚演变的研究结果一致[27],即从2004年到2013年,乌鲁木齐市的制造业企业也以集聚为主,表现为制造业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核心集聚区连片发展。
从静态来看,集聚程度2004年、2008年和2013年表现为相同的特征,均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最高,都市型产业的集聚程度最低。从动态来看,制造业四大产业类别的集聚程度呈现倒“V”形和递增型变化趋势。其中,都市型产业为倒“V”形集聚,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65上升到2008年的0.71,再降到2013年的0.67,集聚程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趋势;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81上升到2008年的0.89,后降到2013年的0.88,集聚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呈递增型集聚,机械设备产业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71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0.80,基础型产业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69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0.75。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28-29],通过对比发现,各城市间不同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都有所差别,这可能与各城市的主导产业不同以及区位因素等有关。
2.2 制造业时空演化:总体特征
利用ArcGIS空间统计工具分类中的热点分析方法,以制造业集聚强度指数为评价指标,以街道(乡镇)作为基本评价单元,分别计算乌鲁木齐市2004、2008、2013年3年各单元格制造业的Gi*统计量Z得分(热度指数),根据自然断点法将Z得分分成5个等级,得到乌鲁木齐市不同年份制造业企业分布冷热点图(图1)。在ArcGIS中将乌鲁木齐市街道(乡镇)单元格转化为点数据,然后基于点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估计,生成不同年份制造业核密度空间分布图(图2)。显然,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
2004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集聚程度较高的单元有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北站东路街道、迎宾路街道、二工乡街道、三工街道、杭州路街道、南纬路街道和石油新村街道,沙依巴克区的西山街道和红庙子街道,水磨沟区的南湖北路街道、七道湾街道和苇湖梁街道等。2008年,近郊区的部分街道和乡镇也成为企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米东区的芦草沟乡、铁厂沟镇、卡子湾街道,头屯河区的乌昌路街道等。2013年,制造业企业的郊区化趋势更为显著,城市远郊区的铁厂沟镇形成了较大范围的新的制造业企业核心区。综上所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逐渐成为制造业企业“回避”或“逃离”的区域,城市东北和西北方向的近远郊区成为制造业企业集中的新的区域。
以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为城市中心,以105个空间单元的中心坐标到人民广场的距离为半径,计算各距离范围的企业数量,结果见图3。2004年制造业主要分布在距市中心3~30km范围内,并有两个明显波峰,在距市中心3~7km范围内企业数量超过150家,在距市中心11~16km范围内企业数量达到300家;2008年制造业总数较2004年增多,主要分布在距市中心7~30km内,有向外迁移的趋势,也存在两个明显的波峰,在距离市中心11~16km内企业数量达到400家,在距离市中心20~30km范围内企业数量接近300家;2013年制造业总数比2008年显著增多,主要集中在距市中心9~30km范围内,并且在距离市中心11~16km 和20~30 km范围内出现两个明显波峰,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00家和600家。总的来看,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多年来基本上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30km范围内,企业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2004~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逐渐从距离市中心11~16km向距离市中心20~30km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0~40km制造业数量也有增加的趋势。乌鲁木齐市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中心城区去工业化、制造业郊区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
2.3 制造业时空演化:分行业特征
基于矢量数据符号法和距离分析法对乌鲁木齐市各类型产业的数量分布进行研究(图4-圖7)。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分布范围有所扩大,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
2.3.1 都市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化
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图4)。2004年,都市型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3~16km范围内,并且在距离市中心5km和13km处企业数量最多,形成两个明显波峰;企业数量较多的街道有: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和二工乡街道,水磨沟区的七道湾街道、水磨沟街道和六道湾街道以及米东区的卡子湾街道。2008年,距离市中心3~9km范围内企业数量较2004年有所下降,企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9~16km范围内,其中距离市中心13km处企业数量最多,在距离市中心20~30km范围内企业数量有增加趋势,其中七道湾街道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企业数量增加明显,都市型产业逐渐向城市外围扩散。2013年,在距离市中心3~9km范围内企业数量已明显减少,企业大规模分布在9~30km范围内,同样在距离市中心13km处企业数量最多,并在25km处形成了新的都市型企业集聚地,米东区的铁厂沟镇、地磅街道,沙依巴克区的长胜东街道企业数量都有明显增加。都市型产业多年来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13km范围内,并逐年向城市外围扩散,2008年以后逐步形成了25km新圈层。
2.3.2 高新技术产业时空格局演化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数量都比较少,格局演化并不十分明显,主要呈向心集聚,也有一定向外蔓延的趋势(图5)。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3~20km范围内,其中在距离市中心5km和13km处企业数量最多,形成两个明显波峰,企业数量最多的街道为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7~11km和20~30km范围内,在距离市中心9km和25km处企业数量最多,新市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头屯河区的乌昌路街道、王家沟街道等企业数量增加明显。2013年,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7~30km内,在11km和25km处企业数量最多,新市区的长春中路街道企业数量增加最为明显。2004年~2013年,高新技术产业从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内圈层向外迁移了6km,从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外圈层向内集聚了5km,但并不十分显著,总体上都分布于中心城区。
2.3.3 机械设备产业时空格局演化
机械设备产业呈现明显的向外扩散趋势(图6)。2004年,机械设备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3~25km范围内,并在距离市中心5km和13km处形成两个明显波峰,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30km处也有少量企业分布;企业数量较多的街道有: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三工街道、迎宾路街道和水磨沟区的南湖北路街道等。2008年,机械设备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7~30km范围内,其中在13km处企业数量最多,且在25km处形成新的企业集聚,水磨沟区的七道湾街道,米东区的南路街道、古牧地镇和铁厂沟镇企业数量增加明显;与2004年相比,企业有向外迁移的趋势。2013年,机械设备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9~30km范围内,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在距离市中心13km和25km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并形成两个波峰;米东区的铁厂沟镇、地磅街道,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地窝堡乡,水磨沟区的七道湾乡和头屯河区的乌昌路该类型企业数量增加明显。从2004年到2013年,机械设备产业企业数量显著增加,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从距市中心较近的5km圈层向较远的13km圈层聚集,到2013年已经形成新的25km圈层聚集地。
2.3.4 基础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础型产业呈现出向外扩散与迁移的趋势(图7)。2004年,基础型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5~30km范围内,分布相对均匀,新市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街道和米东区的卡子湾街道该类型企业数量最多。2008年,基础型产业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7~30km范围内,在距离市中心13km处和25km处企业数量最多,水磨沟区的七道湾街道、米东区的铁厂沟镇和新市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增加了大量该类型企业,企业向城市的外围扩散。2013年,基础型产业主要分布在距离市中心9~40km范围内,并且在距离市中心25km处企业数量最多;与2008年相比,距离市中心13km处的企业数量减少,而距离市中心25km处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企业从内圈层向外圈层进行了迁移;在空间单元上表现为米东区的柏杨河乡、三道坝镇和长山子镇,乌鲁木齐县的萨尔达板乡和新市区的长春中路街道等该类型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从2004年到2008年,基础型产业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并呈现向外围扩散和转移的特征,扩散和转移的方向为城市的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
乌鲁木齐市机械设备制造业呈现出向城市近、远郊区迁移和扩散的趋势;都市型产业呈现出向内集聚与向外扩散的趋势;基础型产业呈现出向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米东新区化工工业园区内迁移和分布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演化特征并不明显,多年来一直分布于中心城区,也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
3 制造业企业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市场等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产业空间结构,从而使城市内部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30],企业区位决策需要权衡市场与政府干预下成本与效益的变化[31]。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就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市场经济机制
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更多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成本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第一,土地价格。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土地市场改革,使土地资源使用由“无偿”转为“有偿”。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城市不同地块的土地因区位差异体现出不同的价值,随着其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32],工业企业普遍占地面积较大,尤其是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城市中心城区高昂的地租迫使这些企业在利益驱使下开始向外迁移(图6、图7),而城市原有的工业用地被第三产业所代替。因此,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大量的制造业企业通过用地置换向城市外围地价相对较低的地段迁移。第二,区位通达度。区位通达度指某一位置或场所对外交往的方便程度,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和距离以及交通便利程度。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坚持“突出交通建设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河滩路等南北向主要干路的修建,更强化了城市向北部新区的突破[33]。乌鲁木齐市制造业集聚的几个热点区域交通便利(图1)。其中: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区内建有高铁综合交通枢纽和全疆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全疆最大的货物储运站,312国道、乌奎高速公路、北站公路与乌钢公路在区内形成了一纵三横的主干交通网,与全疆15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2个航空口岸)遥相呼应;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坐落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内,绕城而过的外环路与吐乌大等级公路、乌奎高速公路两条交通主动脉相互连接,构成通往北疆交通枢纽和沟通中、西亚的重要国际通道;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和良好的区位优势为制造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集聚经济。集聚经济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降低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并通过发挥其外部规模经济效益而不断增强[12]。高新技术产业多需要利用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力和市场因素等,不同类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可以使企业获取大量的相关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创新。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且集聚度最高。与曹玉红等[15]对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的研究结论一致,乌鲁木齐市的都市型产业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并且集聚度最低,这可能与都市型产业均为消费型企业,市场需求量大且大多聚集在原料地或接近市场有关。而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集聚程度高,并且集聚趋势明显则與该类型产业的郊区化趋势明显有关。
3.2 政府调控机制
政府宏观调控不仅对城市制造业快速发展及其企业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也直接影响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与过程。政府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随着城市职能的转变、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处于土地级差地租高、交通条件便利、接近市场的工业地段被高收益的商业、金融等第三产业所占据,原有的工业开始外迁[34]。第二,产业布局调整。随着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边缘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组团逐渐壮大,与城市中心连接成片,开发区与昌吉市相接,米泉和东山的紧密结合形成米东区[35]。乌鲁木齐进一步向北部的新市区、西北部的头屯河区、东北部的米东区疏解人口和城市功能,形成了北部新市区高新技术产业组团、西北部头屯河工业物流组团、东北部米东工业园。这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与扩散。第三,开发区设立与建设。地方政府通过“退城进园”,以及将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集中于开发区,从而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17,30],使开发区成为制造业企业的理想区位。国家级开发区、省(区)级开发区是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征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截止到2013年,乌鲁木齐市已形成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和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米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米东新区化工工业园区、头屯河工业园区、水磨沟工业园区等自治区级产业园区。这些开发区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优质的政府服务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着制造业企业入驻,对制造业企业由中心城区向郊区集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是导致制造业企业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动因。第四,城市功能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总体布局指导,对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以工业为指导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方针政策指导下,乌鲁木齐市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工业发展为主题,导致商业、贸易和服务业等行业被忽视和削弱,城市用地结构极不合理[36]。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乌鲁木齐市大力发展市区经济,城市内部用地类型增多,用地分异现象明显,土地资源更是得不到合理配置。为了改善这种不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乌鲁木齐市编制了《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年~2020年)用于指导新世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规划中对城市工业用地进行了调整:全市不再安排高耗水量、高耗能和重污染的工业,市中心区的工业用地要逐步转向边缘地带,工业用地新增289.6公顷,主要分布在两个开发区、头屯河区和红雁池二电厂;城市快速环路以内只能安排一类工业,以外的市中心区只能安排一、二类工业,市中心区以外视需要可安排三类工业。此外,为减轻城市环境污染,乌鲁木齐市出台了《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政策要求,推动了乌鲁木齐市基础型产业和机械设备产业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减少了中心城区的环境污染,使制造业空间结构更为合理。
4 结论
总体来看,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格局呈现出中心城区去工业化、制造业郊区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企业区位逐渐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在逐渐增强,并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分产业类型来看,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四大产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差异较为明显,表明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结构朝着更为优化的方向发展,未来乌鲁木齐市更应以开发区和高新区为依托,对制造业企业进行合理布局,使产业集群式发展。
城市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企业自身、周围发展环境、市场机制、政府引导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还不能对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迁移方向和距离进行判断,对机制方面的解读如果能深入企业内部进行访谈和调研将更为准确,这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钟鲁. 基于现金流量的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2] 王法辉,胡忆东. 芝加哥制造业发展过程及区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10,30(2):175-183.
[3] 郑国.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结构演化研究[J]. 人文地理,2006,21(5):84-88.
[4] 张晓平,孙磊.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J]. 地理学报,2012,67(10):1308-1316.
[5] 宁越敏,谢守红. 城市化和郊区化:转型期中国大都市空间变化的双重引擎[C]// 认识地理过程,关注人类家园——中国地理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北京:中国地理学会,2003:227.
[6] Drucker J.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cen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J]. Economic Geography,2011,87(4):421-452.
[7] Viladecans M 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City-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4,4(5):565-582.
[8] Rogerson C M, Rogerson J M. Intra-metropolitan industrial change in the Witwatersrand, 1980-1994[J].Urban Forum,1997,8(2):195-223.
[9] Scott A J. Locational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J]. Urban Studies,1982,19(2):111-141.
[10] Christerson B, Appelbaum R. Global and local subcontracting: space, ethnic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pparel Production[J]. World Development,1995,23(8):1363-1374.
[11] Leo P D, Robert T H, Brooke P. Evaluating offshore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in the apparel industry: The small firm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2007,5(3):47-63.
[12] 賀灿飞,梁进社,张华. 北京市外资制造企业的区位分析[J]. 地理学报,2005,60(1):122-130.
[13] 孙磊,张晓平. 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分解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2,31(4):491-497.
[14] 刘涛,曹广忠. 北京市制造业分布的圈层结构演变—基于第一、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的分析[J]. 地理研究,2010,29(4):716-726.
[15] 曹玉红,宋艳卿,朱胜清,等.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J]. 地理研究,2015,34(9):1708-1720.
[16] 王俊松.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2014,33(12):2312-2324.
[17] 吕卫国,陈雯.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2009,64(2):142-152.
[18] 蒋丽.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J]. 热带地理,2014,34(6):850-858.
[19] 郭杰,杨永春. 转型期成都城市制造业空间分布变动研究[C]//规划创新:201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0:1-11.
[20] 郭杰,杨永春,冷炳荣.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12,31(10):1872-1886.
[21] 贺灿飞. 中国制造业区位:区域差异与产业差异[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01-102.
[22] 孟斌,王劲峰,张文忠,等.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中国区域差异研究[J]. 地理科学,2005,25(4):11-18.
[23]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C]//Companion to econometrics.Oxford:Basil Blackwell,2000.
[24] 马晓冬,李全林,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2012,67(4):516-525.
[25] 程乾,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13,33(10):1166-1172.
[26] 董丞妍,譚亚玲,罗明良,等. 中国“癌症村”的聚集格局[J]. 地理研究,2014,33(11):2115-2124.
[27] 周蕾,杨山,王曙光. 城市内部不同所有制制造业区位时空演变研究——以无锡为例[J]. 人文地理,2016(4):102-111.
[28] 刘春霞,朱青,李月臣. 基于距离的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J]. 地理学报,2006,61(12):1247-1258.
[29] 李佳洺,张文忠,李业锦,等.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16,35(1):95-107.
[30] 袁丰,魏也华,陈雯,等.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J]. 地理学报,2010,65(2):153-163.
[31] 袁丰,魏也华,陈雯,等.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J]. 地理科学,2012,32(4):401-408.
[32] 姚康. 基于企业视角的兰州市制造业地理集中与集聚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0.
[33] 宋亚君. 干旱区绿洲背景下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及演化研究[D]. 乌鲁木齐: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11.
[34] 王宏光,杨永春,刘润,等. 城市工业用地置换研究进展[J]. 现代城市研究,2015(3):60-65.
[35] 张利,雷军,张小雷,等.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J]. 地理学报,2012,67(6):817-828.
[36] 周兆军,李晓东. 乌鲁木齐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分析[J]. 山西建筑,2009,35(32):18-20.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of Urumqis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economic census data of 2004,2008 and 2013, and using the locational Gini coefficient, hot spot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Results show: From 2004 to 2013, the overall agglomeration degree in Urumqi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shows that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dustry> basic industry> urban industr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of Urumqi spread from central area to the direction of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of the center gradually weakened, the scope of agglomeration constantly expand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mode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he single-core model to multi-core model. From 2004 to 2013, the scope of urba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has been expanded, and it tends to outward diffusion; the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always concentrated in center area, location change is not obvious; th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dustry and basic industry have obvious location change, they spread and transferred from center area to suburban district and the outer suburbs, they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Urumqi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mon function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Urum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