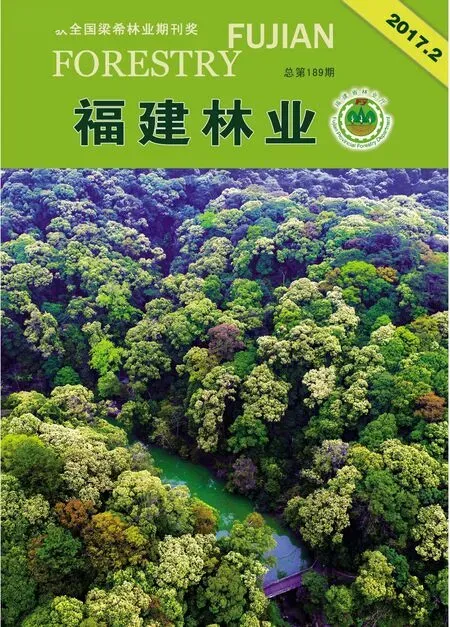海棠文化
文/苏祖荣 图/洪蓉
海棠文化
文/苏祖荣 图/洪蓉
记得读初中时,老师要我们背诵李清照的《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海棠依旧,绿肥红瘦,一个红字,使我记住海棠。
海棠别名梨花海棠、海红,属蔷薇科落叶植物。海棠种类很多,旧有海棠“四品”一说,一曰贴梗海棠,二曰垂丝海棠,三曰西府海棠,四曰木瓜海棠。海棠幽姿淑态,红艳倚霞,早有“国艳”之誉,贾耽在《花语》中称海棠为“花中神仙”,饮誉至今。花叶并艳的海棠与玉兰、牡丹、桂花、翠竹、芭蕉、梅花、兰花同列庭院名花八品。海棠宜孤植于庭院前后,或列植于人行道两侧;可对植门厅入口,或从植于草坪角隅;可植亭台周边,或植丛林边缘。海棠也可制作盆景,切枝可供插瓶作装饰之用。在颐和园、萃景园、御花园以及南方的园林,一丛丛一簇簇的海棠,风前摇曳,艳丽花姿,楚楚动人,海棠胜景无疑是造园家最得意的作品。
海棠花朵小,但重葩叠萼,一树千花,或深红浅红,或艳红粉红,且红中透白,白中泛红,花质细嫩,好似少女红唇。王象晋在《二如堂群芳谱》中赞海棠“其花甚丰,望之绰约如处女,非若他花冶容不正者可比,盖色之美者,惟海棠。”古人心中,海棠已然是一位亭亭玉立的青春美少女了。难怪石崇看见海棠,为海棠美色所震撼,不禁叹道:“汝若能香,当以金屋贮妆”。因海棠之红艳,而把海棠看作美人,已是一种共识。自此后,历代文人对有“国艳”之誉的海棠妩媚风韵的赞美,毫无顾忌。吴融的《海棠》诗:“雪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多逢醉五候”。崔德符的《海棠》诗:“混是华清出浴初,碧纱斜掩见红肤。便教桃李能言语,西子娇艳比得无?”刘兼的《海棠花》诗:“淡淡微红色不深,依依偏得似春心。轻烟虢国颦歌黛,露重长门敛泪襟。”陈与义的《春寒》诗:“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陆游在《海棠》的长诗中更直言:“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扁舟东下八千里,桃李真成仆奴尔。若使海棠根可移,扬州芍药应羞死。”无论是海棠的胭脂色,还是海棠红肤最风流;无论是海棠色比西子娇艳,还是芍药见到海棠要羞死。一句话,文人们借女色红妆来赞美海棠,从不惜笔墨。诗人面对的显然不再是海棠花,而是朝思暮想的梦中美人。海棠已是诗人心中无法抹去的女神。
春暖花开,这是海棠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人们喜爱海棠,亦把自身融进海棠的情感王国。宋代有一隐士叫徐佺,居然攀到自家的海棠树上,结巢为屋,若有客人拜访,引梯而上,在巢中接客品茗,人称为“徐老海棠巢”。诗人苏东坡痴迷海棠,沉醉海棠,往往从白天到夜晚呆看海棠还嫌不足。此时明月已经高挂,但面对海棠,诗人仍恋恋不舍。诗人怕夜深海棠睡去,于是点燃红烛,以便再看一眼红妆容颜。
周总理一生喜欢海棠,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那棵海棠,曾相依相伴周总理二十六年不平凡岁月,海棠的红色定然勾起周总理诸多难忘的往事和无尽的联想,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后来邓颖超大姐睹物思人,写下《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回忆周总理在西花厅的点点滴滴。是的,一年一度,“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写下《乡愁》名篇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晚年余韵未尽,又挥毫写就《乡愁四韵》,其中一韵便是海棠。两岸同根同源同宗同血脉,却被浅浅的海峡阻碍,在这里,海棠被诗人抹上一层乡愁,那样浓烈,那样凝重。在诗人沸血燃烧的灼痛中,人们似乎听到诗人对和平、对统一、对人民团圆的呼唤,一如海棠依旧,在春风吹拂神州的时候,暖暖开放,嫣然一笑,百媚千红。
(作者单位:福清市林业局)
责任编辑/谢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