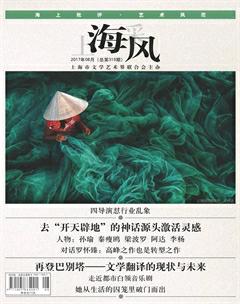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
王萌萌
当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袭黑衣、两鬓微斑的李杨导演,说这句话时有那么一瞬敛了脸上的微笑,双眸射出略有些凌厉的精光,随即又恢复笑容补充道,我认为自己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受邀参加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他住在毗邻淮海路的花园饭店,对闹中取静的宽敞花园和原法国俱乐部改建的巴洛克风格的裙楼很满意。适逢闷热潮湿的梅雨季,但他并不抱怨连续降雨使出行不便,稍有闲暇便想去看老房子。
采访的前一晚,笔者有幸与李杨共进晚餐,席上有重量级剧作家沙叶新,陪伴在侧的李杨自始至终恭敬有礼、照顾入微,并且顾及到席间每个人的感受,言行处处分寸得当令人舒服。若非如此接触,谁能想到这位国内影坛上颇为“另类”的导演,行事待人却如此随和低调。
为圆“导演梦”退学出国
生于1959年的李杨,父母都是陕西省话剧院的演员。看着大人们排戏,孩子自然会模仿,与小伙伴游戏的内容之一就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过家家般演戏。耳濡目染,他早早就立下做演员的志向。
文革期间,父亲因年轻时曾加入国民党而遭受批斗、被迫害致死。母亲虽然因为曾经参加抗战而幸免于难,却也因为不愿与父亲离婚而被降职降薪,家中生活一落千丈,身为长子的李杨13岁就承担起家庭责任,想办法去挣钱并照顾两个弟弟。眼看着身边的人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最熟悉甚至最亲近的人彼此背弃、施暴……令他年轻的心早早就看见人性的无常与丑陋,并因此产生了长久的思索。1977年恢复高考,对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深怀厌恶的他为了远离人群,报考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地质学专业,却因11分之差而落榜。1978年,他同时考上了陕西省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称国家话剧院)。不愿回伤心地面对关于父亲的惨痛回忆的他,选择了去北京学习和发展。
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几年,起初各个领域包括文化艺术界都百废待兴,并没有太多好戏可演。后来为了增加表演经验,也为了生存,他也和不少话剧演员一样去外面接一些影视表演的活。但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对导演的工作产生兴趣,并且受了第五代导演早期代表作诸如《一个与八个》《黄土地》等影片和一些外国经典电影的影响,逐渐将目标转移到做导演上。
1985年,26歲的李杨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两年之后,他居然退学了。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属于国家干部编制,罕有人会中途退学,他的举动在当时着实属惊人之举。如今谈起缘由,他说当年的女朋友要去德国留学,而他又想走出国门,去电影和艺术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学习体验。那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五年内不能出国,想到毕业后再等五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为了不虚耗时光,也为了爱情,他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定。
带着凑来的400美金来到德国,李杨最先进入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之后又转入慕尼黑大学,修戏剧文学专业。最终1995年在科隆影视传媒艺术学院电影导演系,获视听传媒学硕士学位。对于自己8年期间三次转变专业方向,李杨笑称自己“不安分”。但得益于德国高度人性化和相对自由的教育制度,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情况转换就读的专业和学校,大学之间彼此承认过去的学分,他因此能最终比较理想地完成导演专业的学习。
在德国留学期间,李杨为了生活和学费打过各种工,起初是餐厅跑堂、商场销售之类,语言过关之后就开始做演员,还曾经在对华广播的电台做过播音员。通过从事这些工作,使他对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德国人纪律性强、严谨务实、理性重逻辑等特质也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感觉到自己从前的认知崩塌又重建,看问题和思考的方式都改变了。
亲身见证柏林墙倒塌,亲眼看见长期处于物资匮乏中的东柏林人在柏林墙开放后因吃得太猛而噎住、一边干呕一边流泪的情景,使得他心中对人性、对生命生出更多悲悯和反思。
处女作《盲井》获奖无数,让王宝强脱颖而出
在德国考电影学院期间,李杨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云南泸沽湖的报道,他意识到那里有适合拍成纪录片的素材,便自费前往拍摄。完成了记录摩梭族走婚制的《妇女王国》之后,他又拍摄了记录哈尼族喜庆葬礼的《欢乐的绝唱》。忆起当时情景,他感慨说那次拍摄过程中,哈尼族“向死而生”的生死观对他触动很大。这两部拍摄于当时云南最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又引人深思的纪录片都出售给了德国电视台。此后他又为纪念抗战50周年创作了纪录片《痕》。
然而仅仅拍摄纪录片并不能令李杨满足,他的“导演梦”是拍摄自己的故事片,证明自己有做导演的能力。
在德国完成学业之后,他迫切地想要将所学得以施展,可当时国内电影业不景气,街头到处充斥着播放港台片甚至色情片的录像厅。电影拍摄都是由各大电影厂进行,个人连拍摄许可证都难以申请。他每年回国来考察,又总是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国内也有所谓“地下电影”,在部分小众影迷之中颇受欢迎。于是他决定自己攒钱拍一部真心想做的电影,先不考虑之后的放映发行问题。
为了积攒拍片的成本,李杨在德国花三年时间用各种方法赚钱。2000年,他先帮黄建新导演做了一回副导演,以此熟悉了国内拍摄影片的流程。2001年他正式搬回国内,深感国内的变化远超他的想象,一边调整适应,一边寻找合适的拍摄题材。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神木》触发了他的创作兴趣。小说原著讲述的是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骗人去矿上谋害发矿难财的故事。故事的人物简单、场景和矛盾冲突集中,而反应与表达的内容却令人极度震撼,他意识到这能改编并拍摄成一个绝佳的小成本电影。于是他先向刘庆邦买下了小说的电影版权,并试着自己写剧本。然而他发觉由于自己对社会底层和矿工生活不了解,导致在创作过程中最鲜活、最有质感和冲击力的部分不断丧失。他又请刘庆邦帮忙安排,前往矿区下生活。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从河北到内蒙古再到宁夏,回到陕西,之后又转道河南,每到一站就下车去小煤窑探访。最后,总算写出了理想的剧本,其中每一个戏剧化的故事,都是由真实的案例在背后支撑。
说起这部处女作《盲井》,笔者还记得第一次看是大学期间在宿舍里放的盗版DVD。彼时同宿舍的室友也都在看片或者看剧,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感动得流泪,而笔者则自始至终沉默着,时刻感觉眼睛被刺痛着、心被拉扯着,看完之后心情沉重久久无法释怀。那时只觉得,故事片竟然还能这么拍,镜头丝毫不修饰、不回避,直击最肮脏、最混乱、最丑陋之处,似乎隔着屏幕都能闻见空气中弥漫的煤粉味,那么粗粝又那么有力量,淳朴天真的男孩与穷凶极恶却又伪装成好人的骗子之间的对比与互动,以及影片最后男孩离开时不再懵懂和清透的眼神,叫人难受至极却又无法言说。
而李杨说,艺术创作一定要找到与内容最适合的表现方式,因此这部电影他选择用“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由于成本的限制和拍摄手法的需要,剧组需要驻扎在一个条件艰苦又危险的小煤矿里。有一回,剧组在井下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上来两个小时之后煤洞就塌方了。拍摄至中途,剧组发生变故,制片主任携款潜逃并且煽动了部分演职人员退出。李杨身兼数职,带领留下的人在艰难的境况中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盲井》是王宝强首部作为主演的电影,此前他只是一名在北影厂门口等待做群众演员的北漂少年。最初在选演员时,副导演曾经带来不少接受过表演训练的城市孩子给李杨看,李杨觉得这些孩子既没有农村孩子的淳朴,又因为刻意训练,而有了表演的“模式”。他请副导演找回一百多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不给他们试镜,而是与他们聊天,观察他们最自然的状态,最后选中了形象最接近角色需求、又因做过群众演员对镜头没有陌生感的王宝强。他说我从来不教王宝强表演,因为不需要他表演,他只要理解了角色和剧情,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可以。当拍摄遭遇困境、团队人心惶惶之时,李杨曾经对王宝强说,我不能保证你坚持下去一定能得到什么,但作为演员这是你的责任。王宝强坚持到了最后,他在片中毫无表演痕迹的本色出演,让元凤鸣这个角色活灵活现深入人心,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盲井》获得了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第5届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影评人、最受观众欢迎等五项大奖;第2届美国纽约崔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2003年荷兰海岸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和文學大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困境中的坚守与不得已的妥协
“盲和瞎不一样,瞎是生理上的疾病,而盲是一种视而不见,一种道德上的失明。”李杨曾经这样解释他的“盲”系列作品。他的镜头始终对焦在社会底层,法律意识的严重缺失、人如草芥的生存状态、赤裸裸的毫无道德底线的金钱交易等,都是他关注和表现的重点。
李杨拍摄的第二部电影《盲山》,讲述的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关中农村,两年里受尽虐待不断挣扎逃跑最终被公安机关解救的故事。与此前的《盲井》不同,《盲山》没有文学作品作为改编基础,剧本要靠李杨独立完成。2006年年初,他专程到成都金堂、中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采访被解救的被拐妇女的生存状态。对每个被拐妇女来说,回忆那段噩梦般的经历都很痛苦,就像把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一样。可李杨为了创作,不得不进行这种残忍的采访,甚至还需要诱发对方讲出具体细节,因为不了解细节就无法创作剧本,那段时间他内心充满负罪感。向来头沾了枕头就能睡着的他,每晚都需要泡澡放松甚至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比喻自己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相机看着拍摄对象被敌人打伤、打残,但从职业角度他不能去救人,而是要拍摄。有可能他放下机器时拍摄对象已经死了,但这本身就是两难的境况。而经过这些采访,他也坚定了要完成这部电影的信念,觉得自己身上有了一种责任,不论承受多少委屈和艰难,都要把这些故事讲述给世人看。
将拍摄地选择家乡关中乡下,一是为了语言沟通方便,也因为当地原本就有买女人的现象。除了女主角和几位主要的配角之外,男主角和绝大多数演员都是当地的农民。影片中有个角色叫郑小兰,在女主角白雪梅宁死不从的时候,她抱了孩子来劝慰,说你看我也是被卖到这里的,还不是这样了。先把身体保住才是,不然怎么逃?这个演郑小兰的女人,现实生活中真是四五年前从四川一个县城被骗嫁到那个村里的,才2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李杨是拍摄时才知道她的情况,见她天天来剧组看,就叫她演戏。她的丈夫不同意,打她。她就告诉丈夫说你再打我,我就跟剧组走。丈夫不敢再打,后来李杨叫她的丈夫也来串个角色,连她抱的孩子也给一份钱。在拍摄地的村子里,人们视买卖妇女为正常之事,配合拍摄丝毫没有心理障碍,而专业演员全部向农民靠拢,使影片的镜头呈现出最符合真实的效果。
为了拍摄这部《盲山》,李杨抵押了房子,但他觉得为了拍好电影这么做是值得的,真正令他难受的是迫于现实压力而妥协。《盲山》于2007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夺得罗马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可为了能在国内公映,让国内观众看到这部影片。李杨不得不另外制作了国内公映版。国外版的结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黄德贵知道白父要带她逃跑,跟白父起了争执,为了救父亲,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黄德贵,然后画面黑屏。国内公映版的结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亲走了,他觉得这个结尾不是不可以,但国外版的处理方式更符合他个人的想法。
“盲”系列的第三部,也就是收官之作《盲道》,于2016年完成,经过一年多的送审、修改之后,今年将会全国上映。这部由李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讲述的是流浪街头的留守儿童和落魄的街头音乐家之间互相救赎的故事。为了创作剧本,李杨采访了许多流浪的孩子,请他们吃饭,引导他们讲自己流浪的经历。此次拍摄期间依然困境重重,投资人中途撤资,使得李杨不得不“砸锅卖铁”,在拍摄后期,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候,幸好得到了几位主创和好友的鼎力相助才完成拍摄。然而一年多的反复审查和修改,使得不少他认为重要的镜头被剪掉,在他看来使得影片的表现力减弱很多,但他只好“表示理解”。整个采访过程中,每当说起那些不得已的妥协,都是他脸上神情最为无奈和难受之时。
“剑客”本色
从2003年至今,十四年时间拍摄三部影片,李杨在当今国内影坛上或许看似有些低产,但是从影片的题材、质量和社会影响来看,他绝对称得上是立意高、水准高、责任感与使命感高的导演。或许有人会不解,曾经在德国进行了十多年电影方面的学习,熟谙各种技巧、手段的导演,作品竟然如此写实与朴素?然而精心地打磨一部作品、扎实地讲好一个故事,已经成了如今国内电影导演稀缺的品质。当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大热之际,李杨和他的作品或许能给业内人士带来一些思考。
最讨厌刻意拔高的李杨却不愿意被人稱为什么“文艺片大师”,他说电影从来不分“文艺”和“商业”,只分“小众”与“大众”,而每部电影都具有商品的属性。他说接下来他将会转换方向,创作拍摄一些商业性强的电影,赚钱之后就又能去做自己最想拍的电影了。在过去十年之间,除了筹备和拍摄第三部影片《盲道》之外,他还做了不少编剧和影视后期的工作,例如参与《山楂树之恋》《智取威虎山》的编剧,或许这些都是他为执导商业大片做的预热,但他说自己对于底层和弱势的关注永不改变。
前不久,李杨在微博上的一次转发引起一场风波,遭到转发文章中提到的某位当红女星粉丝疯狂的嘲讽和攻击。他回应说,自己的转发不针对任何演员进行批评和评论。演员的演技好坏自有公论,而中国影视界弄虚作假的现象只会伤害中国电影和电影人。谈起这件事,他只觉得可笑和可悲。国内影视界目前肤浅、低俗、粗制滥造、唯利是图的种种不良现象,才令他心痛和心忧。他想对有志于做导演的年轻人说,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加强自身的修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然后坚守内心的追求,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
自嘲在日常生活很无趣的他,业余时间爱阅读、逛博物馆、听音乐会,旅行一定要去远离喧嚣、接近自然的地方。他说自然的广阔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也能指引人抵达内心的平静与美好。
“其实有时候,批评不是坏事,是为了能让在乎的事物变得更好,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嘛。”采访进入尾声的时候,李杨语气郑重地这样说,又补充道:“我是个有正义感的人,看见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就要说出来,就想去改变,这个恐怕一辈子都改不了。”
“所以你自称剑客?”笔者问,他笑着点头。
“对恶的无视和纵容就是帮凶?”笔者又问,他又点头,但这次没笑。
此前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他多次说起过三个词,分别是“常识”“真实”和“意义”。从1987年退学出国学电影到如今完成了“盲”系列三部曲,收获了不少成绩也经历了太多坎坷磨砺的他,眼下追求的是更平和、更自在的心境。说起过往的悲欣得失,他语气超然,有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味。
最后他说:“我个人对物质要求很低,能吃饱穿暖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生活,做值得的事,这样不一定能舒服,也许要受苦,但心里是安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