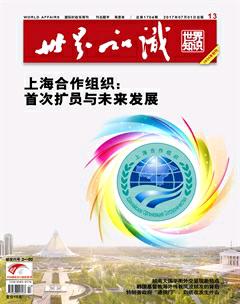穆斯林平行社区:文明冲突还是经济分化
储殷
在欧洲国家同恐怖主义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同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右翼思潮,甚至一些传统的中左翼政党也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右倾化。捍卫“欧洲价值”与欧洲文明的“独特性”,正在成为欧洲主流社会的共识。而这个共识所对应的,除了移民与难民问题之外,更为现实的则是一个难以融入、拒绝融入的“异端”——穆斯林平行社区。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概念对应下,一大批出生于欧洲、成长于欧洲的人被区隔成为某种“内部的外部人”。
当移民群体在经济与文化上长期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形成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移民街区时,“平行社区”现象就随之出现。调查显示,在欧洲,近一半移民及三分之一的移民后代居住在这种聚居区,其中穆斯林移民占比最高。对于宣传“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穆斯林聚居区以及这些区域中林立的清真寺是最好的注脚。但是,移民聚居并不仅仅是来自北非或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穆斯林的习惯,来自东欧、南欧的俄罗斯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以及来自亚洲的越南人、印度人,都呈现出聚族而居的趋向,华人同样如此。对于大多数从事底层劳动的外来移民来说,只有在同族聚居区才能找到廉价的安身之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唐人街与巴黎、马赛、安特卫普、伦敦、柏林的穆斯林聚居区没有质的不同。
欧洲的穆斯林聚居区多形成于二战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十年间,大致上因外来劳工、家庭团聚、难民(含非法移民)而形成。正是经济原因让这些区域成为主流社会之外的“平行社区”。一方面,这些区域租金便宜,也更容易获得各种低廉的黑市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成为收入低下的移民群体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带有强烈移民文化色彩的聚居区。这种穆斯林平行社区,尽管被一些有心人以“文化隔离”的原因来解释,但其实不过是经济弱势造成的贫民区。另一方面,这些区域能够为语言不通、素质较差、缺乏劳动技能的低端劳动者提供廉价而难得的工作机会,比如卫生状况不合规定的移民餐馆、隐蔽于社区内的黑工厂以及各种非法却普遍存在的生意(偷窃、卖淫、盗版、走私等)。相当多在土耳其街谋生的穆斯林二代与许多在唐人街混街头的华裔二代一样,完全不需要走出街道去谋生,也很难走出街道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而欧洲的产业空心化,使大多从事重工业、制造业的穆斯林移民群体面临严重的失业困境。
另一个文明冲突论者不愿正视的事实是,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和新华人移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移民的中国富裕阶层、留学人员等)由于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其社会流动,并没有形成聚族而居的平行社区。同时,与全世界所有居住在贫民区和棚户区的家庭一样,这些居住于“平行社区”的家庭一旦经济收入有所改善,往往会选择搬离。留下来的空间往往为新的贫困者所填补。
尽管作为平行社会的穆斯林社区长期存在,但直到上世纪末其才真正作为重大社会问题而凸显。近20年来,随着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移民逐渐被认为是不正当的竞争者、社会福利体系的侵占者。社会大众心态的这种变化为欧洲中右翼的转型与复兴提供了条件,也被右翼政治力量及时把握。右翼的崛起,迫使歐洲各国政府无论左右都逐渐修正了传统上对移民“不提要求、也不关心”的倾向,而采取更为严格的“同化”与“融合”的政策。“让穆斯林以一个欧洲人的正常状态生活”,这恰恰强化了穆斯林的“非正常”和“非欧洲”符号。日益增加的压力恰恰强化了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移民子女的撕裂感。青年穆斯林群体在深受压迫的同时,出现了反抗性的宗教认同,突出表现为回归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全球穆斯林面临的各种不同问题被简单归结在“压迫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中,而欧洲的穆斯林群体也由此完成了与西方社会彻底的分离。
对于一些主流群体而言,穆斯林问题不仅仅是安全问题、就业竞争、福利削减,而是异质文化在欧洲的对决,没有融合的可能,唯有零和的结局。然而所谓的穆斯林问题,实际上是欧洲穆斯林群体面对一系列经济、文化、政治困境的直接结果。唯有认清文明冲突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倒因为果”,欧洲社会才有可能找到治理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