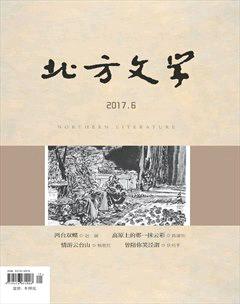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构建
刘媛媛
摘要:女性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座不可忽视的丰碑,大量触目惊心的反传统的母亲形象,赋予了母亲角色以新的理解。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使我们看到,母亲不仅是慈爱的圣洁的奉献者,同时也是可悲的父权制的牺牲品,甚至是可憎的“同谋者”。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女性作家开始觉醒。她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母亲形象。通过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来反映女性意识中的母亲形象由圣化到俗化的过程。
关键词:女性文学;母亲形象;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的概念最早来源自于西方的女权运动,它与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主义等多种释义,一样都泛指主张性别平等。女权主义思想是人类在追求自由、平等历程中必然产生的一个产物,是女性对自我认识的觉醒与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两次博兴与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时期反封建和个性主义的宏伟壮阔的革命乐章,妇女解放的呼声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声部;新时期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时代强音,主权意识的张扬也不过是点缀其间的低吟而已。
一、传统语境中的母亲形象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的男性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就是男子被看作是传宗接代的继承者,妇女则是成就男子社会成就的辅助者,在人格上她们没有自主权,对于自身存在的女性意识更是认识的少之又少。
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来源于此。但是对母亲的尊重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母亲的价值判评上,而且也形成了“贤妻良母”这样的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范畴,母亲身上的道德完美性得到强化。人们将母亲的牺牲、奉献、隐忍精神推崇到极致,常被看作是“义”的化身,但这种“义”带有一种愚性。这些母亲多是一种丧失主体性的存在,她们是忘我的、非理性的,忽略个性与个体的自我价值,超越本能欲望冲动完美而神圣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她们是被看作依附于男性,她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理想,成为成就男人们社会地位的一道辅助工具。
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不仅可以三妻四妾,甚至眠花宿柳也无任何道德压力,却严格规定女性的决对从一而终、守节明志。反之,就会认为不贞。传统社会对女性有种种限制。社会压力,自身的认知也使得很多女性甘愿守节。宋代的程朱理学尤其是推崇妇女的贞操节烈。“饿死是小,失节事大”[2]扼杀了无数女性的青春与幸福。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没有选择自己婚姻的自由,她们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只能服从父母和丈夫,做一个十足的附庸品。
从古至今,母亲受到无数的赞扬。在一般意义上说,母性是女人具备的最基本的特征。其具体内容大抵包括女人的善良品格、对长辈的孝道、对家庭的勤劳、相夫教子、贤惠与贞洁等层面。
母亲这一字眼在一定意义上占据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却只是一个女人人生意义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历来作家们大都只关注到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特定的称谓,而把母亲与崇高、博爱、温柔、贤良等光辉的赞誉相关联。有依据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将母亲塑造成不同的侧面。如鲁迅、柔石、萧红等革命作家为表现妇女所受的封建神权、夫权和男权社会的压迫,塑造了一系列苦难愚昧不幸但善良、慈爱的母亲形象;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更是集中了所有母亲的温柔慈爱的品格,也受尽了天下苦楚的母亲形象。在封建社会的教义中人们要求把女性塑造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形象。母亲是圣母的化身,家庭,丈夫,孩子是他生活的全部,她不能有自己追求自由的权利。
和历代的女性文学家相比,现代女作家无疑是幸运的,她们在一个反叛传统的伟大时代,五四运动推动的人们对自我的觉醒。作家们第一次争得了在创作中言说女性婚恋自由的话语权。因此在这个时候,出现许多不同的新女性形象。在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现代女作家首先把话语的批判锋芒对准造成几千年妇女痛苦不幸的罪恶渊源——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
二、觉醒的一代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質疑
五四以来,随着先进思想的传播、女式学堂的不断兴起,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女性。她们不认同传统的相夫教子、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的道德伦理观念。她们的价值取向在于追求美丽爱情、张扬独特个性。一些新觉醒的人开始选择了积极自强、自求进步。一些孀居的年轻女性,在失去家庭丈夫的依靠,也开始逃离了家族的束缚限制后,勇敢的走向更加广旷的的空间,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提到母亲,人们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儿女躲避风雨的温暖港湾。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母亲形象。比如,在以冰心为首的一批女作家眼里,母爱是真正的皈依,是可靠的真善美。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母亲光辉美好的形象幻灭了。她说“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一说法却也是大胆新奇,也是对传统母亲形象观念的大颠覆。但人只有了解了人生的真相,我们才能重新站在世俗的现实人生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诚然,张爱玲把母性的荒凉与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她推翻了传统的母亲身上的桎梏,解放了母亲作为人的天性。而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传统文化对于母亲人格的束缚于罹难,以全新,大胆的笔触对封建思想作出了回击,这对于母亲文学的发展而言,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母亲走下神坛,在现实生活中被完全世俗化。她们虽不乏对儿女的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纵观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她们一方面是慈爱母亲的化身,是子女们感情与心理上寻找庇佑的对象,另一方面却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冲击和社会的影响,成为父权制度的直接承载者。而母亲这一独特形象,在此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能为儿女所接受,觉醒的儿女开始对被压迫的母亲形象大胆提出质疑与批判。她们要想自身走出母亲的生活模式,并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唯一的方式就是和叛逆之子组成新的家庭,这种以建立在爱情上的新家庭,也是她们对抗封建家庭攻击的一个政治堡垒。对于一份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五四青年们誓死捍卫,于是就有了《隔绝》中的女主人公的竭力高喊:“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女性作家由此开始了对母亲的生活状态的思考与质疑,这种追问与质疑的目的,无疑是对母性生活自由与独立人格的热切期待,她们渴望母亲能够在家庭与社会中重新享有平等的生存环境和话语权利。这与传统社会对母亲真实的定位在本质上并不冲突。可以说,在与现存秩序的不断抗争过程中,她们发现母亲不但是封建父权专制的牺牲品,也是封建父权的间接帮凶。于是,她们在塑造母亲、歌颂母爱的同时,也重新跳出传统,发现了母亲的不完美之处,开始对母亲的复杂角色属性进行了重新分析,定义,批判和质疑。首先她们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对母亲的“女奴”地位进行了观照,毫无遮掩的揭露了母亲在其日常生存与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也即是母亲所受的旧伦理的制约与其自身主体人格的缺失与束缚。在众多作家笔下,母亲勤劳隐忍,且时刻坚守自己所背负的男权思想。母爱从一开始就携带着母亲的权威,同时也把这样的痛苦直接施加在女儿的身上,主导女儿的婚姻同时也造就了女儿人生的不幸。母亲再一次成为了封建父权专制的同谋者。作者针对于母亲的这一定位,表达出了自己满心的怀疑和不满。
凌叔华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表达了对忍让痴心的母亲形象的深刻反思与审视。但她笔下的人物正像鲁迅所说的,她的作品描写的是“世态的一角”。她的作品告诉我们,一切除了叛逆、弑父、追寻母亲之外,这个时代的女性生活还有如此多隐秘不被人熟知的的、封建腐朽的的、可悲可鄙的方面。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撕掉了母亲身上被男人们所强行挂上的装饰品。用她犀利苍凉的笔触写出了女人生命的挣扎和遭受的迫害。黄七巧是现代文学中母亲形象的内心欲望与精神世界最为张扬也最为深刻的一个。她本性并非是恶, 然而她终究由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逃不出女性命运的藩篱,转而变成了害人者,这无疑体现了对母性乃至人性裂变的深刻抛示,也体现了这类母亲深深的生命痛楚。
女性出走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虽然并不鲜见,但其身份往往定位于“新女性”而较少缺少母亲身份的出走者。同时,五四启蒙文学中的女性出走所反抗的对象也往往是传统旧家庭。在此背景下,《寒夜》中的主人公曾树生具有“新女性”与“母亲”的双从身份,她所克服的对象也包含了新旧两种不同的家庭秩序,这样一个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的很远的任务体现了女性的不断觉醒。她既是一个言行反悖于传统的受气小媳妇的儿媳形象,又是一个心灵深处充满反抗风暴,却丝毫不弱于其他异态母亲形象的人物。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敢于追求个性解放和社会理想,曾希望依靠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因此,她像当年的众多新女性一样,勇敢的逃离家庭,转而从事了教育专业,成为一名职业新女性。创办乡村化和家庭化的学堂成为了她和汪文宣的共同理想。她不但找到了事业上的同事,也找到了生活中的如意伴侣。在家庭中,她为了追求真爱而不选择形式,依然和汪文宣同居,面对婆婆的无理指责,她昂然回击并我行我素。她认同的是自由平等的新式家庭关系,而不是汪母所遵从的封建家庭伦理道德。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与汪文宣解除婚姻关系,从这一点而言,她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个带有叛逆色彩的母亲形象。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阳货[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N].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