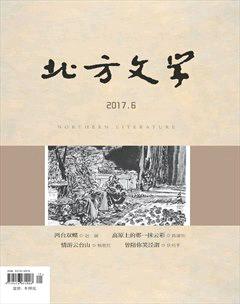浅谈意象
任世珍
摘要:我们在谈论古典诗歌时,经常会提到“意象”。它是人们借助于具体外物、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作者的情思。人们在欣赏古典诗歌时,习惯于把诗歌中出现的名物,例如梅花、兰花、月亮、芳草、西风等等都看作意象。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本文就来分析不恰当的原因。
关键词:意象;表意之象;名物之象
“意象”是一种“表意之象”,将意象从诗歌中剥离出来,代之以符号化的事物名称,将诗歌意象混同于诗中名物甚至拿一个名词来对应一个意象,是不妥当的。
一、名物之象尚不足以承担意象表意的功能
名词有具体和抽象之分,用作名物之词的,大多是具体名词,它在形成概念的同时,亦常能在人们心中引发表象,例如我们在提及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山川河流时,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相应的图像来,但这种表象并不等同于意象。它只是直观经验的积累。而意象是作者诗性生命体验的产物,它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长久而深沉的积淀形成的,内中包孕着诗人对生活的各种活生生的感受。即使转形为诗歌文本,显现为语言文字符号,这些符号所提供的信息也都指向了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意。这正是意象之为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之象(表象)的重要原因。
譬如:我们都熟悉唐代诗人王维在其《使至塞上》诗中的一句名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试问这里包含了几个意象?恐怕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四个意象,这其实就是将表象混同于意象的结果。这些意象单个拆开来看,只能指称名物,是很难把握其内在的情意体验的。而只有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画面,我们才能体会到那种空阔、荒凉、寂静、壮美的氛围。而也只有将它们组合起来,才能让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借此传达出来。这样看来,单一的表象通常是很难构成意象的,意象须由表象之间的的张力而引发,即通过意象组合在一起所生发出来的互补、互衬、互渗、互动的功效来传达,这也是诗中名物不能等同于意象的缘由。
那么我们平时习惯将各类名物从具体诗作中抽取出来,以形成系列性的考察,如专题研究的杨柳意象系列、桃花意象系列等,究竟是否恰当?应该说,按照上面对“表意之象”的理解,意象只能是特定的“这一个”,它在诗歌语境的特定文本中生成,承载着表达诗人特定情意体验的职能,一旦离开了文本的具体语境,孤立的名物便不复成其为意象了。即便排成系列。也只能算作名物的“類象”。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举了这么个例子:“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在给诗歌意象和名物之象作区划时,还会遇到一种情况,便是怎样看待那些因历史承传而在自身内部积淀着某些特定意蕴的名物,有如人们常提及的“南浦”、“东篱”之类的词语。众所周知,“南浦”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但由于大诗人屈原在《九歌·河伯》篇里写下“送美人兮南浦”的名句,被后人袭用来表现送别场景和惜别之意,这个词语便有了比较固定的感情色彩,不同于普通的地名了。同样,“东篱”也仅泛指屋东的篱笆,而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的诗作后,遂亦取得了与清高人格相联系的韵味,不再是普通的篱笆。这类名物就好比文章里常用的典故、成语,一般都有自身的特殊蕴涵,就它们而言,能不能撇开文本,直接归入“意象”的范畴呢?笔者认为,还是不能。诚然,这类词语在其历史承传的过程中,确实积淀了某种意蕴,有其情感生命的痕迹在,但在抽离了具体作品的语境后,其感情色彩必然趋于固态化和定型化,并不能构成特定的“这一个”。只有当它们返回作品,再度与具体语境结合,直接参与诗人情意体验的艺术创造,才有可能重新被激活而转化为诗歌意象的有机构成。
二、构成意象的材料不仅仅是“物象”
诗歌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除了看到名物之象尚不足以承担意象表意的功能外,还有一层因素,就是不人为意象的构成材料仅限于名物之象。名物之外的许多成分,也有可能实现诗歌意象构建的职能,故意象更不能与名物之象画等号了。
一首诗,哪怕是抒情诗,少不了物象的描绘,尤其是我们民族的古典诗歌,喜欢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来表现情怀,于是诗中物象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诗歌并不能一味摹写物态,写物之余,它还要抒述情怀,情感的直接表白有时候是必不可少的。情思的引发往往来自于具体事件,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完全符合艺术的规律,这样一来,在抒情的同时必须适当结合其所引发的事件,诗篇也就有了叙事的成分。更有甚者,诗人的情思里不光有情感活动,亦有思想活动,思想活动若脱离情感而自行表露,又形成了诗中的理念。以此观之,情、理、事、物都应该算作诗歌作品构成的原材料,决不仅限于物象这一端。
先看“事象”。在抒情诗里,情感的抒发需要事由,抒情诗里的叙事往往是为了交代事由。若只能抽象交代,那只能算诗中的“事语”,还构不成“事象”;但有时交代得比较具体,叙述中夹杂描绘甚至还有情意,这就有可能构成“事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本只是述说送别的情由,而说得有情志、有气氛,于是产生了“意象”。更为特殊的,是那种将抒情和纪事交织起来加以表现的诗歌作品,它惯常以纪事为线索,串合情感的抒述、情与事打成一片。叙事中的意象成分便大为增加。如杜甫的名作《羌村三首》之一,抒写诗人于安史之乱中经飘零在外而返回家乡时的情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用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诗篇来组织诗篇,而情感的抒发便也自然地融于其中了。
再说“情象”。“情”是抒情诗的主宰,但“情”又深藏于诗人内心,似乎叫人不可捉摸的东西,那么,该怎样来抒情呢?情景关系的创立,便是为了解答这一难题,“景”以显“情”,成为抒情的正道。不过,我们过去常将这个“景”看得太狭隘了,仅限于具体物象甚至自然景物,这样一来,那些直抒胸臆、罕举物象的诗篇,又当如何来解释呢?实质上,情感活动不只限于借自然景物作表达,它自身便能构成意象,并通过这一“情象”的建构来作自我传递。《古诗十九首》写游子思乡,除首联以月光起兴以及五、六句直言思归点题外,其余各联也都是通过“不寐”起床、“揽衣”徘徊等一系列动作、神情的描绘来加以表达。我们平时也正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神情、姿态来了解其内在心理活动的。因此,“情象”的建立便有了根据,它不同于由状物或叙事所构建的象,而是自成一类的诗歌意象。
最后,还要提一下“理象”。诗中理念能不能构成理象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诗可用来直接表达思想,只要这思想确属诗人诗性生命体验的有机组成,在表达上就有可能做到具体可感,而诗中理语也就自然转化成“理趣”和“理象”了。这亦便是谈论意象艺术不应丢弃“理象”,要将“理象”与“物象”“事象”“情象”相提并论、共同研讨的原因。
由上边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意象不可以等同于诗中名物,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意象是“表意之象”,它只能是特定的一个,不能离开文本单独谈论。另一个原因是构成意象的材料不仅仅是“物象”,还有“事象”“情象”“理象”。
参考文献:
[1]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
[2]《易·系辞上》[M]中华书局,1980.
[3]《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