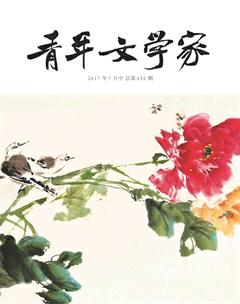浅析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摘 要:哈贝马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详细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哈贝马斯用交往行为这一理论对社会交往进行理解,提出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进行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无数私人领域的集合,是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并非两种对立领域的中间地带,而是两种范畴的交集。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交往行为
作者简介:满肖阳(1989-),男,蒙古族,云南昆明人,哲学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2
“公共”与“私人”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希腊城邦里,公共生活在广场上进行。公共领域可以建立在对谈之上,对谈可以是讨论,也可以是诉讼。公共领域同样可以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实践可以是战争可以是竞技活动。私人领域则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家室的正义与友爱是基于家室中的两种不平等的交往 生活关系的:父亲同子女间的和丈夫和妻子间的。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不能产生那种可以推广的公共性的交往关系。[1]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私人”的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通过“个人”概念(与私人和私人性相通)的使用,构建出了个人的善的知识。在友爱上他强调私人交往,在正义方面他强调公民间的公共性的交往。在他公民的交往是在家庭之外发生的。在家室中至多只具有类比意义上的政治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只有在家室之外的政治社会中才能形成。[2]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希腊的私人领域是局限在家庭之中。但我们从希腊的政治制度对应的经济基础角度看,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公民无需从事劳动。但是公民能否参与公众生活还是取决于领主的权威。领主的权威越大,公民就越容易参加公共交往活动中去。同时,对动产和劳动力的支配不只是家庭财富,而是能否进入公共领域的评判标准。可以说古希腊的私人领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家庭,但是家庭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重要参考。应该说,在古希腊人看来,私人领域包括的是人类生存的必须范围,公共领域则是为个性提供表现空间。
中世纪的欧洲,“公”与“私”通过罗马法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公共财产就是大家共有的,超出商业用途,不受私人权利约束的财产。例如山川河流,公共的道路等。但是,这种约定并没有约束力,并未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共识。封建领主的所有权范围极大,即包括管辖权又包括主权。可以说,封建社会里并不存在古典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分离。在中世纪欧洲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共领域。君主把世俗的领主和精神领袖、骑士、教士以及城市代表都笼络到自己周围,组织起一个本身即是“国家”的团体,而不是代表国家的团体。那么,他们就可以代表国家,甚至是民众。国家的一切都属于他们所有,他们这种代表就表现的是所有权。中世纪欧洲的公共领域参与标准其实是权力的大小。通过繁杂的礼仪、举止、生活习惯、修辞方式以及权力象征物来将甄别参与公共领域的人。这种公共领域说到底是一种贵族交往空间。直到启蒙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资本主義时代远距离商品交换的蓬勃发展,信息的远距离交换成为常态。无论是商人,还是官员,甚至是普通人都更看重书写的报纸,保密的报告或是私人的信件。市场的不断扩张,信息交流机制也随之不断扩大。为了规避风险,政治不断的干预贸易,家乡社区的社区活动也就逐步附加了国家主权性质。随后“民族”形成,现代国家逐步建立,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等级特权为封建领主特权所取代,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这就为另一个公共领域腾出了空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公共权力领域。[3]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前提。市民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市民社会意识。这种特殊的市民社会意识来源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的利益逐渐地扩张,演变为超越地域限制的私人利益交往。这种私人交往的同样需要一定的前提。所有参与市民社会的个人共同认同的交往规则,共同的社会阶级意识,共同的利益诉求等,都是市民社会交往的前提。这种交往前提逐步演变为市民阶级共同遵守的交往规则,最终实现市民社会内的规则的制定。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认同的交往规则演变为共同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阶级意识演变为对“民族”的认同;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民间组织。随着现代国家主权的形成——通过对所管辖的领土、人民、权力等领域进行法理明确的过程——现代民族也随之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市民社会的市民主权也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随之形成。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会而成公共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劳动领域中的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4]哈贝马斯定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个人是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主体,私人与公共权力机关是矛盾对立的。私人通过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与公共权力对立。这种对立体现在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的规则上,也就是规则的制定应当从公共权力出发,还是从私人利益出发。可以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统治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体。
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基础。私人领域包含市民社会,也就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以及家庭与其私生活。通过公共教育形成的基本文化和民族意识并不能覆盖公共交往的方方面面,资产阶级逐渐开始追求关于体面生活的教养。这种教养是通过文学阅读、聚会和讨论逐渐形成。本该形成于家庭交往之中的部分逐步被抽离出来,失去了这一部分的交往领域,也随之变化为狭义的私人活动领域。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领域(国家)之间的部分,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并非两种对立领域的中间地带,而是两种范畴的交集。
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中,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众多私人形成的集合,但这些私人(也就是市民阶级)本身没有统治权,却要求这种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这种要求可以说是很明显的私人。可以说公共交往实质上是私人交往世界以外的众多私人的交往。“私人”的古典意义——即切身所需——同社会劳动和依附关系似乎一起被赶除了私人领域的内在空间,即被从家园中赶了出来。商品交换打破了家庭经济的界限,就此而言,家庭小天地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区别了开来:国家和社会的两极化过程在社会内部又重演了一遍。个人将商品与所有者与一家之主、物主与“人”的角色完全结合起来。私人领域在更高内在层面上扩张构成了上述双重角色在“个人”这个共同名义下趋同的基础。[5]有的学者将之形容为“从魔瓶中释放的巨怪,他竟膨胀到这种程度,使得它的母体不仅相形见绌,而且被挤到了边缘。”
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是一对相互区分的概念,两者的范围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两者在概念上对立,同时又在范畴上相互重叠。想彻底地将两者区分开是很困难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无论公共交往还是私人交往,都是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他所理解的交往行为则是一种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遵循主体间有效性,以对话的形式,力求达到两个及以上主体相互之间理解的社会化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系统,社会是由人通过理解和交往活动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在这种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也就是社会,当中交往行为就表现为公共交往和私人交往。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J].廖申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