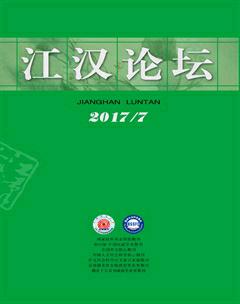逻辑、历史与实践:法治与民主的三层关系


摘要: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可以从逻辑、历史与实践三个层面来看。在逻辑上,法治与民主是不同序列的概念,二者互不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在历史上,民主先于法治产生,这是因为法治比民主需要更多的条件。在实践上,民主与法治可以有多种组合,或者法治优先,或者民主优先,但并非每种组合都是等值的。科学合理的组合是,先进行一定的法治培育,再进行相应的民主建设,从而使二者相互协调、稳步推进。
关键词:法治;民主;逻辑;历史;实践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7-0044-06
法治与民主,是现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经常混用或连用二者,但实际上二者有根本区别。法治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讨论此问题,在理论上有助于厘清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上有助于推动法治和民主建设。本文试图从逻辑、历史和实践三个层面讨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一、互不为必要和充分条件:法治与民主的逻辑关系
法治一般指法大于权的制度设计。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教育人民,并让他们自由地投票”①,这一界定是民主的本意(即多数人的意志)在现代政治选举中的应用,它使得现代选举成为民主共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民主或者是不可分离的孪生关系(即有其一必有其二),或者一者是另一者的构件或要素。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混为一谈。比如,美国学者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明明讨论的是法治的奇迹,讲述美国宪法制定的关键历程,却被认为是民主的奇迹。而彼时,美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民主选举。美国宪法的制定,是精英协商、合作的结果,与平民、大众几乎没有关系②。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将民主与法治并列,认为二者互为条件,不可分离③。
科恩认为,既然“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因此,要弄清民主的性质就有必要把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与其它种类的管理体制区别开”④。科恩认为法治与民主是不同的两种社会管理体制。当代欧美法治民主国家,法治与民主共存,因而,人们似乎可以据此将二者视作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孪生关系。但是,不要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国家都是成熟民主国家(也是成熟法治国家)。成熟意味着事物有其发展阶段。达尔就说:“把民主看作是一次性发明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就像蒸汽机的发明。”⑤我们能否以成熟状态作为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呢?恐怕不能。因为成熟状态的事物可能复合了诸多其他因素,因而不能作为一般标准。比如,民主是有阶段的,每个阶段的特征也是不同的。对于有待民主转型的国家,尚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民主,因而首先需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民主,并以之为前提,再向成熟民主前进。若以成熟民主为标准,就会犯倒果为因的错误,将目标设置为起点。比如,达尔认为,民主兼有程序性和实质性⑥,其所言民主当为成熟民主。因此,我们应该对民主作一个基本的区分,将之区分为底线民主和成熟民主,前者就是最低限度的民主,即熊彼特所言的选举民主⑦;后者复合了法治与民主,当今的美国、英国、德国就是典范。不过,与底线民主相比,底线法治的条件要多得多⑧。讨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不是不可以从成熟层面来讨论,但首先应从底线层面来讨论。
民主与法治是不同角度或序列的概念⑨。我們可以列表来显示二者的差异。为了充分比较,也将专制和人治列入考察。
根据表1可知,在逻辑上,民主与法治不是同一角度/序列的概念。凡是矛盾的概念A与非A,都必须属于同一问题。若两个概念不属于同一问题,则不可能是矛盾的,所以,民主与法治不可能是矛盾的。这意味着,法治与人治是矛盾关系,民主与专制是反对关系(因为民主与专制不是二分的)。在逻辑上,不同序列的概念可以相互组合,不会导致矛盾。所以,基于权力来源角度的专制与民主,跟基于权力运行的法治与人治,可以构成四种组合:专制+法治;专制+人治;民主+法治;民主+人治。如果贵族制也引入,则有更多的组合。
民主与法治互不构成必要条件,也互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是二者基本的逻辑关系。
第一,民主不是法治的必要条件。没有或缺乏民主,法治也可以存在。典型案例是1832年前的英国,有法治而无民主。此期的政治博弈及其发展,是在英国的精英集团(或权势集团)之间展开的,大众并未参与,并无底线民主。又如,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也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治,但并无选举民主。再如,新加坡在威权体制下也建立了法治。所以,民主不是法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法治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民主也可以和人治并存。典型例子是雅典民主及当代的不少民粹民主。处死苏格拉底,就是直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法律。有人指出,雅典时代在法治上乏善可陈,“始终没有制定过完整的成文法典,没有推理缜密的司法判决,也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法学论著”;“没有产生出一个职业的法官、法学家和律师”;“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雅典可谓政绩平平,乏善可陈”⑩。民粹民主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多数人意志为直接的决策标准,包括审判标准。民粹民主的存在足以证明,法治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至于这种民主是否巩固,又当别论。
第三,民主不是法治的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民主是法治的充分条件,那么,有民主就必有法治,从而民粹就不可能存在。雅典民粹民主的存在就验证了民主不是法治的充分条件。
第四,法治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法治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有法治就必有民主,从而专制+法治这种形态就不可能存在。1832年前英国的专制+法治就验证了法治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充分条件,都是必然性条件,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以否定其必然性。所以,综上所述,法治与民主是不同角度或序列的概念,二者互不为必要条件,也互不为充分条件。这种关系表现在时间上,既非法治必然在民主之先,也非民主必然在法治之先。明白此点,有助于将民主与法治视作不同的独立变量或者一般意义的独立因素。一些论者在谈论民主时,实际上兼杂了法治;谈论法治时,兼杂了民主,就是没有明确认识到二者其实是不同角度的概念。
二、民主先于法治产生:二者的历史关系概述
讨论法治与民主的历史关系,既可以丰富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也可以验证上述逻辑讨论。
虽然民主与法治互不为必要条件,但在历史上,民主先于法治产生。最早的民主产生于古希腊。雅典民主虽然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它完全满足底线民主的条件。底线民主的特征是选举民主。那它有无其他必要的附加条件呢?若有,设之为x,则底线民主的条件就不再仅是选举民主,而是“选举民主+x”,其特征就不再仅是选举民主。所以,底线民主不能有其他必要的附加条件。也就是说,民族、地域、历史、文化、非选举的其他制度都不是必要条件,都可以不考虑。再看雅典民主具有哪些特征:(1)选举,并且是直接选举,如选举执政官。(2)处理公共事务,并且是直接民主决事,而不是代议决事(案例:审判苏格拉底)。这意味着,雅典民主的内涵大于选举民主,所以,雅典民主满足底线民主,准确说是超过底线民主的。无论雅典民主是满足还是超过底线民主,都表明民主是先于法治的。当然,底线民主满足民主的基本条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稳定、巩固的。要实现民主的稳定与巩固,则需要更多条件。
但是,雅典民主只是民粹民主和直接民主,而不是法治民主,因为它不满足法治的基本条件。雅典民主之后,民主沉寂了两千年。邓恩讲民主的历程,其中,从古希腊一下子跳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此间跨越了2000年。之后,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而英国,也是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才具有了底线民主。
英国法学家戴雪在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中第一次使用了“法治”(rule of law)这个概念。当然,法治这种思想要先于此。尽管亚里士多德谈到了法治思想,古代也有一些按照法律来处理公共事务的事例,但是,即便是底线法治也是最近几百年的事。罗马法时代算不上底线法治,因为它并不具有法律至上、人人平等等法治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没有法律至上,没有人人平等,法律只是君王的统治工具,这种统治只能成为以法治理(rule by law),而不是依法治理(rule of law)。底线法治的雏形,始于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有何独特之处?它“不是对一个暴君的压迫和勒索的应急措施”,而是一种制度制约。同时,它明确表达了拒绝不受控制的、不负责任的王室权力,并主张即使是国家最高权力,也必须受到某些基本规则的制约。王在法下的观念开始(但未完全)形成。1295年召集议会(parliament,雷宾南译为巴力门,以别于一般的议会);1689年,权力草案又限制御用特权(royal prerogative)。这几百年间,英国建立了底线法治,并走向成熟。宾汉姆认为,《1628年权利请愿书》“是《大宪章》和人身保护令状的直系后裔,对法治的贡献同等重要”。因而,如果说存在法治的“成年”时刻,那就是国王承认《权利请愿书》的1628年。但是,此期并无底线民主。此期的政治博弈及其发展是在英国的精英集团(或权势集团)之间展开的,大众并未参与。而民主对法治的介入,乃是底线民主形成后的事(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标志)。
在历史上,民主先于法治出現,虽不具有必然性,但也不是完全偶然的。法治的条件比民主复杂,这是它更晚出的重要原因。不过,并不能说,复杂的事物一定晚出,因为即便具备了民主的条件,统治者也可以不推进民主。换一种表达,底线民主只有一个必要条件:众意至上(这与选举民主是底线民主不矛盾,选举只是众意至上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处死苏格拉底就是众意至上的实践。雅典民主是古代世界唯一实现过的民主,即便其稳定性值得考量。法治对民主构成规范,形成现代民主,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并最先在美国得以实现。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自我升级版,而是“民主+法治”的合成物且不断相互促进、升级的结果。而即便是底线法治的条件,也远比民主复杂、多样。法律至上、普遍性、无内在矛盾、稳定性、事先可知晓、司法独立、严格程序、可预期、裁量权边界可控,都是底线法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底线法治比底线民主晚出。而这种晚出恰好表明,尽管民主与法治相互配合,可能有更好的效果,但民主可以不依赖法治;同时,法治也可以不依赖民主。
在法治的诸多条件中,还有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隐蔽条件使它比民主晚出,此即智力条件(或知识条件)。民主并不需要特定的知识条件。科恩认为,民主需要智力条件,即“公民理性能力有可能运用于处理一般问题的那些条件”,如推理能力。但此说并不妥当。科恩说的或许适用于良性民主或成熟民主。况且,没有任何手段能保证公民具有理性能力,而对何为理性能力的判断,不同利益、立场、背景、知识、文化、传统中的人可能不同,甚至相反。比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有人认为希拉里应该当选,有人则认为特朗普才是最佳人选。如果要把智力条件作为民主的条件,那么,就需要对公民进行智力条件限制,并延伸出智力水平测试等一系列措施,而这在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这意味着,一定教育程度以下的公民不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民主允许用脚来投票,这意味着,不能设置智力条件限制。从底线民主看,一群文盲也可以搞民主,多数人的意见完全可以成为决策根据。亨廷顿所言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便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所以,选举对选民也无智力要求。但是,法治需要智力条件,因为法治以无内在矛盾的严密、合理、科学的规则系统为必要条件。福山认为,古代宗教社会就有法治因素,但古代无法建立底线法治,因为彼时人类的知识积累较少,无法制定法治所需的科学的规则系统,因而缺乏法治的必要条件,而这正是雅典有民主而无法治的重要原因。黄仁宇认为,英国从1689年开始实行数字化,整个社会变得规范有序,这佐证了科学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只有科学发展了,才能实现数字化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也才能实现法治。近代以后,科学飞速发展是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知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古代,人类不可能搞法治。所以,基于智力条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及民主历史地先于法治的原因。
三、法治可以规范民主:二者的实践关系
法治与民主既互不为必要条件,也互不为充分条件,这一逻辑关系是二者的实然关系,即客观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民主与法治没有必然、唯一的先后关系。表现在实践层面,这一关系又具有几种具体情况:(1)先民主再法治;(2)先法治再民主;(3)同时实行民主与法治。由于逻辑本身不做价值判断,所以,这三种具体的逻辑关系在逻辑上都无优先性,即没有谁比谁更好。但是,逻辑上无优先性的,不等于价值上无优先性。价值,体现于社会实践领域。
那么,在实践中,这三者中哪种关系更优?特别是,对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民主与法治应该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在实践上,民主与法治的应然关系问题,即价值判断问题。有时,人们会混淆实然关系和应然关系。比如,如果认为应该先民主再法治(应然关系),就说民主是法治的必要条件(实然关系),那么,这种说法就不严谨,它混淆了实然关系和应然关系。
就实然关系和应然关系来看,应然关系不能违背实然关系,即前者的选项不能超出后者的选项。若后者有多个选项,如何遴选最优的选项作为应然关系,就是很重要的课题。由此可知,一方面,说民主是法治的必要条件(或者反之)是不严谨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二者在实践中的顺序无所谓先后,则可能导致重大的实践错误。
本文认为,在实践层面,法治建设应该优先于民主建设,因为民主需要法治来规范。这是基于法治与民主的基本特点及二者的关系来考察的。
法治是意志的表达,民主也是对意志的表达,这是二者的共同平台。只不过,法治所表达的意志外延更大,它可以是大众的意志,也可以是小众如统治者的意志,而民主则是大众意志的表达。既然二者都是对意志的表达,那么,用一种意志来规范或改变另一种意志,就是可能的。法治规范民主的总机制可以概括为:法治实现出来的功能即规范性程序是对(没有法治化的)民意的规范。这个总机制可以分解为诸多方面。
第一,法治和民主对意志有不同的表达和规定方式,民主可能是对元素意志的表达,法治必然是对集合意志的表达和规定,所以,法治可以以其集合意志规范民主的元素意志。虽然二者都是对意志的表达和规定,但是,民主作为“多数人的意志”,不限于但可能表达和规定特定的意志,而法治却只能表达和规定一般的意志。这里的“特定”和“一般”,可能有歧义。为了避免歧义,可以借助逻辑语言来表达。“特定”对应于“元素”,“一般”对应于“集合”。没有形成法治的民主,或者没有法治化的民主,它只是表达元素意志,而法治却表达集合意志。比如,雅典时期,雅典城邦通过投票的方式对苏格拉底的民主审判,表达的就是元素意志。因为这一民主审判只是针对苏格拉底,其审判结论可以表达为:“蛊惑青年的苏格拉底该处以死刑。”(命题A)其审判结论不是:“凡是蛊惑青年的人都该处以死刑。”(命题B)命题B表达的就是集合意志。法治有诸多必要条件,不满足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不是法治。之所以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不是法治的,不仅因为其结论表达的是元素意志,还因为它不满足法治的其他一些必要条件。比如,蛊惑青年是否该判处死刑,这一规定必须是预先给出的,而不能临时规定。
是表达元素意志还是集合意志,是民主与法治非常重要的区别。法治只能表达集合意志。宾汉姆指出,1215年的《大宪章》作为现代法治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宪章》不是应急措施,而是一种制度制约。所谓应急措施,就是就事论事,只解决当时面临的那件事(元素),而不考虑其他同类事件(集合)。而制度制约就是把一类事件(集合)作为它的处理对象。法学理论所言之法律要有普遍性,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这其实就是说法律要表达集合意志。
但是,这不是说民主只能表达元素意志,而是说民主经常表达元素意志。只有法治才能使元素意志变为集合意志。当民主表达元素意志时,可以说它是纯粹的民主,也可以说它是民粹民主。纯粹未必都是优点。许多好的事物都是复合的。现代民主作为民主的成熟形态(相对于底线民主)至少是民主与法治的复合,而现代法治作为法治的成熟形态(相对于底线法治)也是民主与法治的复合。在现代,民主属于授权,法治属于治权,民主为法治提供合法性基础,此即政权民授。但要注意,并非从来如此。古代,合法性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神意,如君权神授。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分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合法性来源不同。专制的法治的合法性来源是君权,并最终还原为神权;民主的法治的合法性来源是民权。在现代,由于民主为法治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得民主与法治看起来合而为一或孪生,谈民主不能离开法治,谈法治不能离开民主,因而可以称为民主法治社会。但这是复合的结果。民主要使它从对元素意志的表达上升为对集合意志的表达,并不需要借助民主之外的东西,而只需要借助它自身。当民主把处理对象从元素意志修改为集合意志时,民主就可以嬗变为法治的民主。比如,当民主不再是对蛊惑青年的苏格拉底(或其他某个人)进行讨论和投票,而是对蛊惑青年这种一般行为该如何处理进行讨论和投票时,民主就摆脱了纯粹和初级的形态,进入成熟形态。
同时还需辨析,不能误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从对元素意志的规定转变为对集合意志的规定,专制也能。《大宪章》对集合意志的规定就发生在专制时期。而这也证明了民主和专制都可以导向法治。因为,民主(和专制)跟法治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它们不是矛盾的,因而可以结合。
上述对民主与法治的逻辑辨析非常有意义。它區分了民主与法治的基本不同,而法治与民主的其他不同以及法治对民主的制约功能和机制,都是以这种不同为基础的。
第二,法律无内在矛盾,民意经常有矛盾,所以,法治以其无内在矛盾规范民意的矛盾。法律不能规定A,又规定非A。当然,法律可以修改,可以推翻先前的立法,但这样做,仍然是有规则可循的。如果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公认的解决原则是后法优于前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这一规则也是法治可预期的重要原因。但是,民意很容易此一时彼一时,充满矛盾,并且无法在事前以公开、明确的方式展现这种矛盾,也无有效规则去化解这种矛盾。
第三,法治具有稳定性,民意不具有稳定性,所以,法治以其稳定性规范民意的不稳定性。稳定性是法治的重要优点之一,法学家们都非常强调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的稳定性包括两个方面,法律的稳定性(立法)和法律执行的稳定性(司法),且如何执行本身又是被法律规定了的。但是,民意(准确说,没有法治化的民意)并不具有稳定性。典型的案例是,在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中,对苏格拉底的同一行为,前后两次民主审判(也就是民意审判)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轮投票中,以280票比220票判处苏格拉底有罪。但苏格拉底不服,认为自己对城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苏格拉底的辩护激怒了部分陪审员,使得在第二轮投票中,以360票比114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法律本身作为人的意志(不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意志)的表达,虽然它也是可以修改的,但其修改需要经过复杂而严格的程序,其稳定性显然远远高于民意。
第四,法律的内容可事先知晓,民意的方向很难事先知晓,所以,法治以其可知晓规范民意的不可知晓。同理,法治的可知晓分为法律和执行两方面。由于法律通常是明文规定的,因而它很容易知晓。即便有些自然法或习惯法,也是长久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人们早已知晓。但是,民意(准确说,没有法治化的民意)很难知晓。比如,在苏格拉底审判中,苏格拉底根本不知道民意究竟要干什么,因为民意既没有事先表达,也不稳定。
第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意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所以,法治以其人人平等规范民意的非人人平等。人人平等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层面,对于属于同一类型的事件(即属于同一集合的元素事件),法律应该予以相同的规定;同时,在司法层面,对归属为同一类型的事件的同类处理,在执行时,应该同等对待。但是,民意面前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这种不平等,也可以从苏格拉底审判中分析出来。由于苏格拉底审判进行了两轮投票,我们可以把被第一次审判的苏格拉底视作苏格拉底(甲),被第二次审判的视作苏格拉底(乙)。第一次审判,因为甲没有辩护,所以判得轻;第二次审判,因为乙辩护了,反而判得重。这意味着,影响民意的因素太多,所以民意面前很难做到人人平等。但是,法治完全主张辩护,法官不会因为辩护而加重惩罚。
第六,法治审判有专业的第三方,即司法独立;但民意审判中没有专业的第三方,所以,法治以第三方即司法独立规范民意之无第三方。司法独立其实有两层含义:独立性、专业性。在古代,法律比较简单。但即便如此,普通民众仍然并不通晓法律(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民众要打官司,也得找“讼棍”)。而在现代,不要说普通民众无法通晓法律,即便是律师、法官和法学家,都只懂部分法律。所以,无论古今,法律都是具有专业性的,且法律的专业性越来越强。独立性使司法机关和法官能够超越当事人的利益纠纷,作出比较公正的审判;专业性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尽可能依法审判,少误判。但是,民意审判缺乏独立性,因为部分民众很可能与当事人利益纠纷相关,很容易使民意根据自己的立场、情绪和利益来判断,因而这会影响审判的公正性。同时,缺乏专业性,也很容易使民意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看法、立场和情绪来审判。
第七,法治有严格程序,但民主并无严格程序,所以,法治以其严格程序规范民意之无程序。有人说,民主强调程序。这个看法是不当的。因为这种观点是把法治视作民主的一个构件或要素。没有法治化的民主可以说没有程序,要说它有什么程序,则只有一个——投票。比如,有10个人,其中9个人讨厌另外那个人,于是,他们就用投票的方式,将那个人扔进河里。这也是符合民主的——这种民主就是民粹民主,也是原始民主。苏格拉底就是死于这种民主。真正看重程序的,是法治。正因为民主不讲程序,法治讲程序,法治才对民主构成有效规范。法治的程序性是它规范民主的最重要手段和功能。虽然这一手段和功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法治的其他特征和条件,但它却是法治规范民主的最重要表现。同时,法治的程序性也是法治可预期的重要原因。
第八,法治可预期,而民意不可预期,所以,法治以其可预期规范民意之不可预期。这里的可预期跟前面的可知晓不同。可知晓是就法律的内容而言,可预期是就一个行为在特定法律体系中的后果而言。同理,法治的可预期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法治可预期,意味着行为者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中,能够大致准确地评估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因而能够提早做出行为决策和计划。这一点在经济活动中特别重要。无论什么制度,如果它不能有效激励经济,都不是好的制度。法治是促进经济的最重要因素。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回答“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单一促进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深思熟虑地回答道:“法治”。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也说:“通常,法治被认为是政治的或者法律事务……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在经济学上,法治也具有了重要意义……不仅认为法治自身是有益的,而且它体现和鼓励了公平社会,因为它也是其他‘有益事物——特别是增长——的促进因素。” 但是,民意(准确说,没有法治化的民意)是不可预期的。典型案例仍然是苏格拉底审判中的民意。苏格拉底似乎认为,第一轮投票后,他的辩护有理有据,可以改变民意,判他无罪。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辩护反而激怒了某些陪审员,导致了对他更不利的审判——死刑。
第九,法治的裁量权边界可控,民意的边界不可控,所以,法治以其裁量权边界可控规范民意边界之不可控。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社会生活,法官必须拥有一定的裁量权。同时,“遵守法治是一个程度问题。完全遵守是不可能的(某些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存在某些受到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比不存在更好”。法治的裁量权边界之所以可控,是因为法律稳定、明确、无矛盾,其内容预先可知。民意的边界不可控,还可以用逻辑来描述。设有两种不兼容方案A与非A,民主投票既可能选择A,也可能选择非A,因此,其边界不可控。但是,在法治中,裁量权不可能有如此之大。比如,如果法律规定,“贪污10万元判刑3年至10年”,即便嫌疑人态度不好,最多也就判10年;态度好,最少也要判3年。而在苏格拉底审判中,民意几乎没有边界,苏格拉底从第一轮审判中被判有罪到第二轮审判中被判死刑,这个边界可以说是无穷大,也就是没有边界。
其实,法治还有一些优点有助于规制民主,但相对次要。比如法律至上也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条件,但此处并没有将之作为法治规范民主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民主社会,民意也是至上的。并且,民意至上是法律至上的合法性根据,法律至上是民意至上的确定(或凝固)。所以,法律至上与民意至上并不矛盾。法治要规范的不是民意的至上性,而是这种至上性的表现,即尽可能避免这种至上性以临时、具体、矛盾、不稳定、不可知、不可预期、不可控等方式表现出来。
基于以上几点比较可以得知,虽然法治和民主都是对民意的表达和规范,但是,如果没有法治,民意就经常只能针对元素意志(或元素事件)、不稳定、很难知晓、充满矛盾、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也不独立和专业,进而无法预期。要规范这些不足,必要的手段就是法治。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绘制“法治规范民主的机制的逻辑结构图”(见图1)。
综上所论,民意如水,法治如沟渠;民意如车,法治如道路和规则。水需要沿沟渠流淌才不会构成危害;车需要沿道路按规则行驶才不会混乱。所以,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应该先进行一定程度的法治培育,为民主设计好规则,然后进行与法治程度相匹配的民主建设;同时继续进行法治建设,再进行民主建设,从而使法治与民主相匹配,并且循环递进,相互促进。至于什么算不超出法治范围和相应的民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判定。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如何处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逻辑、历史与实践三个方面对法治与民主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完整清晰地认识并在实践中更为科学地规划二者的关系,制定更加合理的国家治理方略。
注释:
①⑦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8、395—396页。
② 参考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关于民主与法治关系,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CNKI篇名栏输入“民主+法治”,有1100多篇,仅2016年就有近100篇论文,且有不少著名学者参与了这个话题。有人认为民主与法治不可分。譬如,俞可平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参见俞可平:《再说民主》,《领导文萃》2009年第12期。李德顺先生新近的研究也持类似观点,参见李德顺:《论民主与法治不可分——“法治中国”的几个基本理念之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法治与民主是两回事,强调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应该法治化。较新的研究可以参见马一德:《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葛洪义:《法治:政治民主的底线与高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关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将逐渐深入。清理、辨明二者的关系,对于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有裨益。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清理民主与法治的逻辑关系,论证了二者并不具有相互依赖性;基于此关系,再考察二者的历史关系和实践关系,从而使三层关系成为有机整体。而关于法治与民主的实践关系,本来二者是相互规范的,但本文侧重于法治如何规范民主。关于民主如何规范法治,另付专文讨论。
④ 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158页。
⑤ 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⑥ 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⑧ 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⑨ 关于概念的角度和序列,可以通过模拟来理解。设问:“这间屋子里有些什么人?”答:“有男人、医生、老人、女人、教师、儿童、青年、律师。”如果屋里真的有这些人,那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但它是混乱的(正确与否与混乱与否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正确的不等于不混乱)。因为它将不同角度或序列的回答混杂在一起。男人、女人,属于性别角度或性别序列;医生、教师、律师,属于职业角度或职业序列;老人、儿童、青年,属于年龄角度或年龄序列。回答之所以混乱,也跟问题相关,因为提问的角度本身就是不准确的,“什么”这个疑问词所包括的角度太宽泛。
⑩ 程汉大:《雅典宪政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汤姆·宾汉姆:《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19、25—29、57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2页。
戴雪:《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再版序文第13页,译者导言第3页。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Francis Fukuyama, Transitions to the Rule of Law,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0, 21(1), pp.33-34.
黃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其实,无论在古今还是中外,关于民意没有稳定性、很难知晓、不可预期的类似案例非常多,只不过,苏格拉底审判非常著名,故这里主要以之为案例。
拉兹(Joseph Raz):《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93页。
作者简介:刘广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