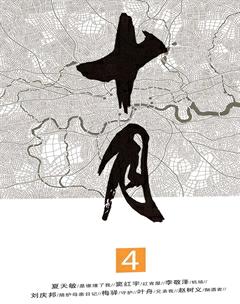写作是多年前午后散淡的光
孟昭旺
小时候,我是个敏感的孩子。那时我住在董村,我们村很穷,没工厂,没副业,所谓养殖大户和致富能手,只能从报纸和收音机里了解到。我觉得,我们董村是最像农村的村子,直到现在,村里依然靠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广播信息,大到迎接上级检查、民主选举,小到谁家丢了鸡鸭、叫孩子吃饭的琐事,都要到广播里喊一喊。村中央有个铁皮小卖部,就在我们小学门口,小时候,我总在那里买铅笔、小刀、橡皮,也买玩具、斗兽棋、贴画还有印有卡通人物的纸片。现在,小卖部还在,只是卖东西的人换成了老店主的儿子。串乡的商贩,每天清晨会沿街叫卖,从前是吆喝、摇着拨浪鼓或敲着铜锣,现在换成了扩音喇叭,从巷子一头到另一头,一遍一遍地喊。我们董村偏僻闭塞,通往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离我们村还有三里地。我对那条公路印象深刻,原因是,从我上高中开始,直到参加工作后的前几年,总共十几年的时间,每次回家,都要在三里地外的路口下车。父亲会准时在路口等我,我下了汽车,骑上自行车,带着父亲回家。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讲,那条路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光阴和世事。
我们董村人是最像农民的农民。他们勤劳、善良、质朴,也因循守旧、胆小怕事,还有那么点儿势利眼和小聪明。在董村,他们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着,耕种、劳作、通婚、生育,自有一套成熟的模式。这套模式来源于“老辈子”——小时候我曾经频繁听到这个词“老辈子怎样怎样”,在董村人的意识里,“老辈子”代表了规矩和传统,也代表了尊严和正义。
我父亲是个优秀的木匠,他真的很优秀,就像我在一篇小说里提到的,假如他不当木匠,而是去画画或者拉小提琴,他一定也会非常出色。父亲当过兵,空军炊事班班长,跟他一批的战友很多都留在部队,后来成了很牛×的领导干部。父亲没能留下,因为他没文化,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坚持让我和姐姐读书的原因。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并不笨,她总是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走亲戚该带什么东西、吊孝时怎么磕头、过年上供有哪些忌讳,她都记得门儿清。即便如今上了年纪,她也会在自己的药瓶上画上太阳和月亮,代表白天服用和晚上服用。还有我的姐姐,她对我很好,小时候总替我抄歌词、替我攒邮票和电话卡,她让我感到踏实安稳,后来姐姐去了天津,在那里定居,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我的乡亲们,董村的会计、赤脚医生、牲口把式、小学老师,还有打谷场、麦秸垛、电线杆、烟囱、池塘、水缸、枣树……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不外乎想说,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对我的写作,对我性格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小说比作一个人的话,我想,我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个人的骨骼和血肉。
最后,我想说说多年前,午后和阳光。大约在十岁以前吧,许多个夏天的中午,因为担心我和村里的伙伴儿们下水游泳,母亲勒令我在家睡午觉。天气炎热,我躺在炕上,母親摇着蒲扇,哄我睡觉。年少时多梦,梦境离奇,彩色的石头、滔天的洪水、会飞的蛇、长着翅膀的姑娘,都曾在我的梦里出现。有时会被笑醒,有时则会被吓醒。
当我醒来,通常已是午后,身边空无一人,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儿,大概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我锁在家里。直到现在,我仍时常回想起那样的场景:我一个人躺在偌大的土炕上,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枕头上,也落在我身上,世界悄无声息,安静极了。在阳光照耀下,我能看见空气中飞翔的尘埃,它们闪烁着光芒,在空中飞舞,像精灵一样。我躺在那片阳光中,所有情绪都被无限放大。时隔多年,我很感激那许多个午后,也感激那许多个午后带给我的恐惧、好奇、平静、躁动、孤独、狂欢、欢乐、忧伤……总之,它是温暖的,带有忧伤的底色,某种程度上,它是我写作的灵魂,也是我写作的缘起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