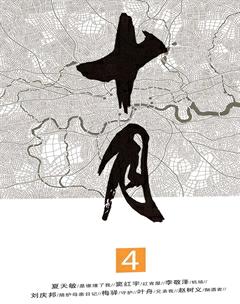年年有父
王棵
一
农历新年前,这地方家家户户都要做同样的事:贴春联,掸尘,洗蚊帐;馒头和年糕蒸得越多越好,最好装满几口大缸;还要架起油锅,炸些肉丸、鱼丸、虾丸、长生果、兰花豆,用它们款待新年期间前来拜访的亲戚;年后该走的亲戚,是要預先走访一遍的,送些年货过去,顺便敲定年后的拜访时间……这些事最好在腊月二十到二十九之间做完。二十之前太早,二十九又太晚。过了二十九,就只剩三十这一天了。这一天,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腊月二十九以前的天明跟大人们一样忙,但大人们忙的是手和脚,天明忙的是眼睛和心思。天明的眼睛盯牢了父亲,心思被父亲的动作牵上牵下。
天明是在监控父亲。他担心父亲偷偷把那件事给做了。这样,他就不能像去年那样,去做那件事了。
去年这个时候,天明做了那件他觊觎了好几年的事:
他把家里的春联写了。
大门、房门、灶房、树上、猪圈、羊圈,加起来二十几副春联,都由九岁的天明写了。
天明觊觎这件事有三年了,从他上小学一年级在描红簿上用毛笔描出第一个字开始。去年,天明终于遂了心愿。这得感谢从南京来的小晚。小晚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脑子虽然有点儿欠缺,却有一鸣惊人的抱负,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大惊小怪。那天夜里,小晚从外面走进天明家里。天明正趴在煤油灯下写语文作业,小晚蛰到他身后,发出一声高喊,“哎呀,陈秀志,你快过来看,你家这个小孩到底是个什么小孩啊?”
“怎么了?怎么了?”天明的母亲陈秀志慌里慌张地跑进来。
“你看看,看看。”小晚说,“你家这个小孩的字,吓死人了。”
“怎么回事?你乱说什么‘吓死人?”陈秀志紧张起来。
“好看。”小晚说,“哪有小孩写字这么好看的?没有。我走南闯北,从来没有见过。天明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经小晚这么一说,天明像被烈酒呛了一口似的,满脸通红,但同时他激动得小心脏直往上蹿,幸亏他的手捂得及时,没让它从嗓子眼里钻出来。终于有一个人如此猛烈地夸赞他写的字了,虽然,这个人,这个女人,不识字。
最终,激动战胜了羞涩,天明摆正了脸,直视光影里的小晚,像看一个难看的仙女。他就这样看着缺了一颗牙、瘦得八十斤不到、颧骨尖尖的小晚将他的练习本举起来,在他的母亲陈秀志眼前挥动。陈秀志当然也像小晚一样,是不识字的,她要识字才怪了。理所当然,在此之前,她要懂得天明的字写得好看与否,那更是怪了。现在,小晚的表扬令她的虚荣感取代了理智。于是,她把头伸过来,与小晚的瘦脑袋紧贴在一起。她二人瞪大眼睛望着天明作业本上的字。然后,陈秀志就把自己的头从煤油灯的光辉里挪走了,挪到那些光辉与黑暗的交集之中。
在那里,陈秀志用一种故做淡漠的语气说,“小晚,南京到底是大地方呀,把你的眼力弄得这么好。”
“全南京没有比我眼力更好的人。走遍江苏全省,都找不到比我眼力更好的人。”小晚把南京等同于整个江苏,生活在南京就觉得走遍了江苏全省,看来脑子欠缺得不是一点半点。
小晚接着又说,“我活到四十多岁,从来没见过谁家小孩的字有你家小孩写得好。哎呀!我今年四十几岁?四十一还是四十二?四十三?”
如果是别的时候,女人身、男人心的陈秀志对这样的提问一定会抱以尖刻的讽刺:你个小晚,还是像在这边做姑娘时一样没脑子呀,南京人到底怎么了,竟然把你这个痴货给娶过去了,你多少岁你自己都不晓得,别人怎么好意思晓得?但现在陈秀志自然懂得去羞辱一个说好话的女人是不妥当的。
于是陈秀志说,“小晚,你不须要晓得自己多少岁,你只须回到南京的时候跟南京那里的人说一说,你娘家这边有个小孩字写得好得不得了,那就行了。说不定你这一说呀,旁人就记住了,我们家天明长大以后可以去南京,靠写字吃饭。”
“那是。那是。”
小晚走了。
天明的脸还在烧。他在想,天底下还有比他不怕害臊的小孩吗?这是两个不识字的女人啊,其中一个还疑似智商有问题,所以,刚才这顿表扬是毫不足信的,但他竟然无视这一点,坚决地让自己兴奋得不行。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天明会放任这种无视了:他对自己的写字水平足够自信。
至少,天明写得比父亲王卫丰好。别的不说,就说王卫丰写的春联有错别字,就能证明天明写得要好一些。
不是这个道理吗?
比如:前年堂屋大门上的“瑞雪兆丰年”被王卫丰写成“端雪兆丰年”;
东厢房门楣上的“五福临门”,“临”字的左偏旁,多出了一个点;
后门上那句“百年天地回元气”,“元”字,写成了“无”。
不独王卫丰爱写错别字,是王家园里许多人家的春联上都有错别字,所以王卫丰写的字在王家园里即便不算好,也不能算差,以王卫丰的人生哲学,做人不掉队,就不足以警觉,所以,他是向来不会去在意自己在春联上写了错别字的。
可是,天明一看到自家春联上的错别字,就浑身上下难受。亲戚、邻人来串门,眼睛不小心往那上面一瞟,天明就警觉地认为他们看到了那错别字,觉得人家肯定会因此看低了他们家。
天明不想被别人看低了自己家,因为,他从来都力争做王家园同辈小孩中口碑最好的小孩,他认定父亲的错别字是他去往好口碑的道路上的障碍,他务须把它清除。在争强好胜这件事上,天明遗传母亲陈秀志。
还有一个令天明恐惧的担忧,天明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王卫丰的错误字低头不见抬头见,会使他对父亲这个称呼失去应有的敬意。当然,这样的担忧,在王家园里,也就天明这种早慧的小孩会有。从这点来看,一个小孩的早慧,对一个父亲来说,不见得全是好事。
二
小晚走后,天明突然就在心里面想:为什么他不趁着刚被小晚大大夸赞了一通的这个夜晚、这个好时机,向母亲提出由他来写今年的春联呢?
于是,天明瞪着从黑暗里走到煤油灯的光晕里的陈秀志,突然说:“姆妈,今年春联哪?个写?”
这是一个曲折的提问。每年的春联都是王卫丰写,所以,天明这个问题问得实在莫名其妙。但知子莫若母,陈秀志的目光在天明脸上略略触碰了一下,便立即从天明的曲折里提炼出了天明的准确用意所在。
“你写啊。”陈秀志说,“今年的春联,天明,可以由你來写。”
以前春联都由王卫丰写,现在就不能改成不由王卫丰写吗?以前王家园的地还属于集体呢,从去年起,分到个人了,不是家家户户缸里、柜里、桶里的存粮更多了吗?这是另一个让陈秀志答应天明来写春联的心理依据。
天明把头深埋到煤油灯的光照不到的桌面以下去。他怕自己过于喜形于色,遭母亲取笑。更重要的是,他担心自己高兴过了头,使母亲突然想到他还是个不该被委以重任的孩子,然后收回她刚刚说过的话。再有,春联在这个家里约定俗成是王卫丰的事。突然要变成天明的事,陈秀志是要去做王卫丰的工作的。
陈秀志怎么去做工作的,天明就不知道了。反正,腊月二十七那天,天明真的被允许挥起毛笔在红纸上写春联了。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为了表示对春联这件事有独到的审美,天明专挑王家园里的人家没写过的写、挑没人敢写的写。稍微念过几本书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它们中,有的根本就不是春联,是诗,或者是挽联。
挽联不要紧,只要够特别。跟别人家不一样、能引人注目,这是第一要义。
反正陈秀志不识字,也不知道天明写的是什么。反正,爱写错别字的王卫丰也不见得一定知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样的“春联”是天明在语文课本上学到的那个叫陶渊明的东晋名士所作的一首《挽歌》,天明大可以在写春联这件事上大展生平所学。
春联由天明写完,由王卫丰贴。天明个子太小,贴门联这件事,只好有劳王卫丰了。王卫丰的面色怎一个阴沉了得。贴春联的时候,他把门板敲得“哐哐”响,明确表达他对让天明来写春联这事的反对态度。事实上,自从腊月二十六那天,他去乡上的集市买回春联纸、裁好纸,直到把纸和砚、墨在桌上摆好的这长达一天多的时间里,王卫丰几乎没说过一句整话,中间吃早饭的时候,他还狠狠用脚踢了那只兢兢业业为他家捉了五年老鼠的老猫。
陈秀志和天明都清楚,王卫丰是反对天明来写春联的。就仿佛这件事有打破了这个家庭延续了多年的规矩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个家庭里一般时候王卫丰都说了不算。说了算的是陈秀志。陈秀志想叫谁写就谁写。
小晚傻归傻,见识是有的。他们这些人连汽车都没怎么坐过呢,既然从遥远而著名的南京来的小晚都说了,天明的字写得好,那肯定是真好,不让天明露一手,她这个当妈的也太不懂得在王家园里表现自己了对不对?
天明写得好,就证明她教子有方啊,这是她表现自己的好时机。
三
门联贴好了,王卫丰脚步用力踩着地,跑到灶房里不出来了,一个劲地在灶台后抽水烟。而天明这边却完全是另一种心境,他背起手,站到自家房子前面,站到离房子足有十米远的距离,把目光的焦距调好,一个字一个字地端详过去,欣赏自己此生第一次的重量级劳动成果,那些春联。没有错别字,像他这么聪明的小孩,要想写春联,不可能有错别字。而且,他比王卫丰写得好太多了!天明审视完后,心里面响起一个如此笃定的声音。
可是,令天明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春联写完的当天晚上,常来天明家串门的郭金蓝装模作样地站在天明家的房前,同样装模作样地好生端详了一番天明写的春联后,又更加装模作样地大声对王卫丰说,“王卫丰,你呀,你写的字就是好看。”
“好看吗?”王卫丰掩饰不住心里的悲愤,冷冷地问,“你说说,都哪里好看了?”
听话听音,郭金蓝立即感觉到了不对劲。往常,素爱跟王卫丰插科打诨的她在赞美王卫丰时,王卫丰首先要回以笑脸的。今天,不但没有笑脸,还来了句如此生硬的反问。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郭金蓝到底不是个傻子,她一下子想道:也许发生了她所不知道的事。她试探地问王卫丰,“今天给自家写了一天春联,写累了吧?我很想今天请你去帮我家写春联,要是你今天写累了,明天帮我去写也行。”
“不累,我闲得腿都要木掉了,今年我轻松了,不用亲自写春联了。”王卫丰说,“你要是看得起我,想让我像往年那样,给你家写春联,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家去写。”
说着,王卫丰看了一眼天明,古怪地笑了一下。又看了一眼陈秀志,更加古怪地笑了一下。
郭金蓝一下子就知道不是王卫丰写的了。他看天明和陈秀志,说明这是他们两个人中的某个人写的。陈秀志哪里可能会写字?只能是天明了。
天明写的?竟然是天明写的?郭金蓝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地上去了。
天杀的,接着下来,这个女人竟然说了一句再没有原则不过的话,“怪不得呢,我说你们家今年的春联怎么看着不对劲呢?原来是天明写的,那上面,王卫丰你快看看,那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错字?那个,就是那个,是错字,对吧?唉,小孩子哪有不犯错的,难免的,难免的……小孩子做事,哪有大人牢靠……天明他一个孩子家的,他写春联,哪有你王卫丰写得好哟……王卫丰,陈秀志,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子去写春联呢?”
天明听到郭金蓝这样一说,恨不得跳起来上去扇她两个耳刮子,把她那个一年到头很少回来的男人扇回来,然后那男人替代天明再扇她两巴掌,把她打到河里面去。错别字?你一个不识字的女人竟然能看出错别字?小孩子一定没大人写得好?就不能写春联?这是什么歪理?呸!拍王卫丰马屁也没有这么拍的。
而王卫丰无疑对郭金蓝的话很受用,阴沉了一天的脸舒展了,他立刻开始像往日一样,跟郭金蓝插科打诨,十来分钟后,他在守活寡的郭金蓝的再次力邀下,迈着四方步,去郭金蓝家写春联去了。郭金蓝的男人在徐州当煤矿工人,一年到头难得回一趟家。所以,郭金蓝是王家园里最爱拍男人马屁的女人,拍拍马屁,男人们高兴了,多跟她说几句有男人气的话,这样,她守活寡的人生缺憾就得以弥补一星半点。郭金蓝是个无论生活怎么不完整,都有能力驾驭一部分世界的女人,王家园的人讨厌郭金蓝对自己残缺生活的经营,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的精明。嘘,不要说郭金蓝了,留点儿口德。
总之,去年,天明家的春联由于是天明写的,尔后,这一年里的一天又一天,不管刮风下雨,天明常会房前房后地走过来走过去,眺望这些春联,与记忆中那些年里王卫丰写的春联做比,最终,他一次又一次地确信,他写得就是比王卫丰好。
可是,天明几乎没有听到别人正面确证他心里的这种论断。是什么原因呢?噢,想来应该是这样吧,“王家园的女人几乎没有识字的,男人识字的倒挺多,但懂字好、字差的,不算多,敢于说天明的字强过他老子王卫丰的男人,就几乎没有了。”
反正,天明是这样想的。
四
不说去年的事了,还是回到眼前吧。现在,又是腊月二十七了,再不把春联写好、贴上,实在是不妥当的了。
王卫丰拖到腊月二十七才去街上买红纸,似乎,他故意这样的。这表明,去年的春联非他所写这件事,一直让他介怀到今天。
天明的心事却是另一种。他是这样想的:既然去年,他们家已迈出了春联由他去写的这家庭改革的第一步,今年会沿着改革的既定路线走下去吗?春联还会由他写吗?
会吗?天明满心期待。
王卫丰却一步到位地将天明的期待或幻想扼杀。
红纸买回来,王卫丰快手快脚地将桌子挪到堂屋正中,看都不看谁一眼,冷峻地裁纸、磨墨,之后,他拿来他参照了多年的折了许多角的春联簿,“哗啦”翻了几下,定好了要写的那几则春联对子,两腿撑开,半蹲半立,挥起毛笔就大写特写起来了。原先他写完家里所需的春联,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但这一次,他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写完了所有的春联。他在抢时间哦。仿佛,稍微写得慢那么一丁点儿,他手里的毛笔就要给人抢走似的。写毕,他同样冷峻地去调糨糊,再搬了凳子爬高爬低地去贴春联。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等去亲戚家预约完年后走访时间的陈秀志回来,屋前屋后、树上树下、猪圈羊圈鸡舍鸭舍外,已经红得稀里?哗啦了。
在王卫丰写和贴的那段时间里,天明原本盯在王卫丰身上许久的目光一点点地折断,幻想一点儿一点儿地破灭,心跌落到脚后跟。今年,他终究没有得到写春联的机会,终究没有。这一年里,天明摩拳擦掌,暗中等了一年,等着这旧历新年的到来,好再次在写春联这件事上大展身手。为了比去年表现得更好,在村办小学,每一堂对老师来说也就开个课做做样子、对别的学生来说根本不重要的描红课,天明极尽认真。他深信,自己的毛笔字,比去年又长进很多了。可是,这一切,都被王卫丰的独断专行扼杀了。
天明还惊恐地感觉到,因为王卫丰这一次的独断专行,那种他所排斥的对“父亲”这个词的敬意眼下少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
让天明意外的是,贴完了春联,王卫丰居然还在堂屋正中墙上,用力地贴上了一幅领袖头像。在家里张贴领袖头像的习惯,从去年包产到户开始,就被每家每户废弃了,因为这种不约而同的废弃,街上的所有的杂货铺,包括供销社,今年初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领袖头像的售卖。那这张领袖头像王卫丰是从哪里买到的呢?
天明仔细凑近墙上的领袖头像看,后来他认定,这是王卫丰专门请人画的。
五
王卫丰轻松明快地将高兴写在脸上。晚上,他温柔地推开陈秀志,把本该由陈秀志干的炸肉丸、长生果、兰花豆的事独揽。并且,他似乎不知道天明不开心似的,第一锅的肉丸炸好,他竟然笑着大声喊天明过来,要天明来尝尝他炸的肉丸的味道。
“不好吃。难吃死了。”天明假装吃了一口,立即把准备好的难听话说了出来。
他不好直接对父亲说,你写字难看,错别字信手拈来,你在春联上写了错别字,因为他还是知道,这种话是很伤人的。他更不好说,因为你写字难看却还不懂得藏拙,已令他难以对你产生应有的敬意。好,他可以不对王卫丰说这个,但他还不能说你王卫丰炸的肉丸难吃吗?难吃死了,太难吃了,就是难吃。
“哪里难吃了?”王卫丰笑眯眯地问,“我觉得很好吃的嘛。”
他将天明啃了一小口的大半个肉丸扔进嘴里,向天明做鬼脸。
“老大的人,在孩子面前没正经。”陈秀志嗔了一句。
“我要是正经,能生出天明嗎?”王卫丰说罢,“嘎嘎”笑了起来,再次做了一个鬼脸。
看来,他今天是高兴得不行了,得意得不?行了。
天明听得懂王卫丰话里的不正经。这让他甚至第一次对王卫丰产生了一点点的厌恶。
“别理他。”陈秀志说,“他是个痴货,天明,走,我们娘儿两个出去踩蚊帐去。”
天明赶在陈秀志的前头就往外走。
陈秀志叱了王卫丰一句,“你看你,把孩子惹恼了。”她跟着天明走了出去。
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常规状态:王卫丰扮演被嘲笑、被讽刺乃至被辱骂的角色,而陈秀志和天明占尽嘴上的便宜。不仅如此,在这个家里,王卫丰一年到头也几乎得不到一件可以由他说了算的事。
天明提着一大一小两双干净雨靴,陈秀志抱着一只大而沉的木盆,木盆里盛着蚊帐,他们一前一后往井边走。然后,陈秀志从井里吊上来两桶水,将蚊帐在木盆里泡好,一边催天明穿上雨靴,准备站到木盆里踩蚊帐。天明的脑子却全不在这里,他下意识地总会将思绪落到王卫丰刚刚写过的春联上。天明在脑子里搜寻着必然会出现的错别字。显然,王卫丰今年写的时候注意了一点儿,错别字少多了,但仍然有一个。那简直是天明不能忍受的一个错字:
国“太”民安——
天了啦,王卫丰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太”了,他简直“太”上瘾了。
“姆妈,跟你说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了。”天明穿好雨靴,站到木盆里,把水和蚊帐踩得“咯吱吱”响,凛凛地说,“他写的春联上有错别字,每年,他写的春联上,都有错别字。”
出乎预料,陈秀志一愣,像没听到天明说话似的,低下头去,没有搭天明的腔。
“他写的春联有错别字,姆妈,你听见了吗?”
“是吗?”陈秀志看了天明一眼,淡淡地这么回应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天明怎么都想不明白陈秀志为什么要装聋作哑?越想不明白他越想拿话去掏她心里的话,于是天明大声嚷嚷起来,“他在春联上写错别字,姆妈,你不怕人家看到笑话我们家吗?”
陈秀志仓皇瞪了天明一眼,大声喝道,“别说话。踩你的蚊帐。”
天明吓得不敢再说下去了。不明白陈秀志为什么要叱他。他说的是事实不是吗?一个说出事实的小孩不该被呵斥。天明忽然就对陈秀志刚才的呵斥很反感。
踩好蚊帐,娘儿两个一人拽着蚊帐的一头,合力将它拧干,陈秀志一个人抱着它走到房前,将它用竹竿顶起来晾好,然后她兀自进屋里去了,也不叫天明一声。天明简直就纳闷。
“你不要说他写得难看。”晚上,趁着王卫丰应邀去给郭金蓝家写春联的时候,陈秀志拉长了脸叮嘱天明,“天明,你不能说他写得难看……不能这样说的,懂吗?”
天明一夜没睡好,梦里面,陈秀志的话响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明感觉到自己身子很重。一些莫可名状的惶惑、郁闷、烦躁,加重了他身体的重量。
六
腊月三十到了。王卫丰早早起床,忙活起来了。
陈秀志和天明倒完全地闲了,没有一件可去做的事了。
如果说一年中王卫丰还有哪一天明显是说了算的话,那就只有腊月三十这一天了。这一天,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这件事得在做完所有杂事之后才去做,而这件事必须由王卫丰去做。只能由王卫丰去做。
祭祖。
谁都知道,再也没有比祭祖更重要的事了。
这件事必须在做完了一系列的杂事之后,让神思变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件事必须由王卫丰来做。只能由王卫丰去做。除了王卫丰,没有别人有资格做。
平日里吃饭用的饭桌,现在被当成了供桌,上面摆满了荤素八道菜,四样水果,四样点心,丰盛到不能再丰盛。仿佛,一年攒下来的最好的东西,现在全拿出来了,供上。祖祖辈辈曾经去世的先人那么多,多到不仅天明不知道有多少人,连王卫丰和陈秀志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怎么丰盛都不为过。
怎么虔诚,也不为过。祖先们都会在这一天回来,默默地挤坐在供桌的四面八方,吃着敬供给他们的这些美食,免不了会边吃边议论在他们面前做供事的他们的子孙,否则他们的这顿饭多么无趣啊。他们一定会说的,一定会议论的,议论面前的他们的后人。虽然王卫丰、陈秀志、天明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还是希望他们说出来的话,是赞美,不是怨言,不是摇头叹息。
王卫丰把铁锅在供桌之前架好,细致、耐心地在铁锅里摊好草纸、纸钱、锡箔、冥香,然后他先跪下来,向供桌周围无所不在的祖先们磕头,他磕得缓慢、扎实。庄重地磕。三磕三拜。上体笔直,然后,匍匐在地。末了,王卫丰动作缓慢有力地站起来,瞪大眼向陈秀志和天明看去。陈秀志立即会意,将天明拉进来,先叫天明磕头,她再磕。一年到头,她只有今天如此看王卫丰的眼色行事,唯有在今天,她会如此听从王卫丰的指挥。
都磕完了头。一切仪式毕。王卫丰默默地走到一边,走的过程中不看陈秀志和天明一眼,然后,他远远地隔着供桌,及供桌四面的长条凳,他就这样一个人在墙角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拿起水烟,尽量不发出声音地抽起来,目光盯着某处,定定地,很长时间不挪开。仿佛,他声音大了,目光动一下,会打扰到供桌上正在聚餐、用他们的方式交谈着的先人们。那样,是极其失礼的。
天明偎着陈秀志,远远离着供桌和供桌边的椅子,也远离着王卫丰,在另一个墙角边的凳子上坐下,时而看看供桌,时而看看王卫丰,如同王卫丰突然也变成了先人。天明的心里逐渐堆积起一种畏惧,不,是敬畏。这敬畏是针对那些他看不见的先人的,也是针对王卫丰的。
千真万确,就在这一天,一年中也就只有这一天,天明心里面丢失的对王卫丰的敬意会像退掉的潮水一样涌回来,堆积在他心里,堆积到该有的那么多。只有这一天,王卫丰突然在天明眼里有了气场,这气场将平日里堆积在天明心里的对他的挑剔意识驱逐得一干二净。天明也明确感到,母亲在这一天对父亲的感觉,是跟他一样的。
天明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受:王卫丰把这一天,当成自己的節日了。
要这么去想的话,在这之前的某一天,腊月二十七,抑或二十六、二十五,王卫丰就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节日做准备了。而写春联,是他在自己的节日到来前所做的一个重要的预备动作。
哦。那是王卫丰在自己的节日来临前的一个预备动作。既然是自己节日来临前的预备动作,由别人做,总是不甘心的吧。哪怕,这个别人,是他最疼爱的他儿子天明。天明想,这就是王卫丰不想让他写春联的原因吗?
天明好像有点儿理解王卫丰了。
可是,在除夕夜即将到来之前,天明一个人去河边走了走,这期间他脑子里总是跑不脱王卫丰摊草纸、纸钱、锡箔、冥香和跪下的样子,这时候想来,天明总觉得,王卫丰每年这一天做这事时的这些样子,多少有表演的成分,而今年,他的表演似乎有点儿过了。天明忽然就觉得,王卫丰是想抓住做这事的机会,来增添或挽回他在这个家庭、他在儿子心里的权威。
想到这里,天明对王卫丰的敬意迅速就褪去了,褪到和一年中的其他时候一样的少。它褪得这样的迅速,都让天明感到惊恐和无助了。
七
长长的除夕夜来到了。天明和王卫丰、陈秀志默默地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这年头岁尾的流逝。中间有一阵子,天明困得不行,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打架,终究迷糊了起来。恍惚间,天明看到陈秀志把王卫丰拉进了厢房。天明下意识地醒了过来。然后,天明趴在桌上,听到了厢房里陈秀志在小声数落王卫丰。
陈秀志说,“我知道你,你把写春联这件事看得顶顶重要。孩子要求他来写,你觉得如果满足了他,就等于你自己承认了自己写得不好。”
王卫丰齆声齆气地说,“我是写得不好,但我写得不好,也是他父。王家园里做父的,都写得不好,也没见哪个做父的让孩子去写。”仿佛要强化自己的意思,王卫丰又重复了一句,“我是写得不好,但我写得不好,也是他父。”
果然,天明在河边揣测的王卫丰的心理,没有冤枉王卫丰。
这时天明听见陈秀志轻声笑了,“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你是在担心,如果你答应了孩子来写春联,等于在孩子面前承认了你自己字写得不好。你怕你这么一承认,你在孩子心里就变小了。你觉得做父的,在孩子心里就应该大大的。”
王卫丰不说话了,大概在抽水烟。
最后还是陈秀志的声音:“可是你也看出来了,你不让孩子写,更加有可能让你在孩子心里变小。”
过了好长时间,王卫丰说,“明年,还有以后,都让孩子写吧。”
陈秀志说,“你心里面也答应了?”
王卫丰说,“嗯。”
陈秀志说,“那你还要向孩子道个歉。”
接下来就没有声音了。
天明瞪大眼睛躺在堂屋里。厢房里面王卫丰长时间没有给予陈秀志“道歉”的建议予以应答,令天明感到惊惶。不知道怎么回事,天明现在突然特别怕王卫丰最后会说,“好的,我找个时间,给孩子道个歉。”假使王卫丰真的来跟天明道歉了,天明不把头低到脚后跟才怪,尽管,天明并不觉得他之前要求写春联,有什么错。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不代表他能欣然接受父亲的道歉。
这样的怕,进而还让天明感到内疚不已。他想,白天他居然在河边那样去想王卫丰,那真是不该,不该啊。
仿佛是为了阻止王卫丰随时会出现的道歉声的到来,仿佛是为了迅速驱走心里的内疚,天明抓紧时间发出了一声大叫——就是那种被梦里什么事情吓到了似的,一个无助的小孩才会发出的惊声尖叫。
王卫丰和陈秀志听到天明在这边叫,飞快地从厢房里跑出来。
“天明,你怎么了?”陈秀志紧张地问。
“天明,你做什么不好的梦了吗?”王卫丰的声音同样紧张。
天明不容置疑地扑到王卫丰怀里,紧紧地搂住王卫丰宽阔的腰杆。
王卫丰身子一紧,然后,他看了陈秀志一眼,咧嘴轻笑的同时,腰杆慢慢地放松了。
“天明,你不要怕。没有什么好怕的。”王卫丰把两只手在天明瘦小的后背交叉起来,用力地勒了天明一下。
天明在王卫丰怀里用力点头,“嗯,嗯。”
八
然而,大年初一起床之后,天明站在自家房前,看着正门上那个横批:国太民安——那个不受欢迎的“太”字,他被无法排遣的悔意裹卷了。除了悔意,还有对自己的厌弃。天明想,为什么,凭什么,他昨天晚上不敢接受王卫丰的道歉?更何况,王卫丰根本就不曾答应过,要向天明道歉。
天明一个人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太”字,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前把它撕掉。
如果天明在大年初一的这天,撕掉门联,这简直太大逆不道了,但是,只有这种大逆不道之举,王卫丰和陈秀志才能意识到,天明须要让自己取代王卫丰写门联,对天明来说,是一桩多么重要的事。这种重要性,不会因为任何事而改变。
天明最终还是打消了那个可怕的念头。甚或说,那个念头不是天明自己的,它是别人的,留意到天明不开心,就好心好意地过来跟天明来说一声“新年好”的。来了一下,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了,跟天明毫无关系了。
所以,当王卫丰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出现在他眼前的天明,是一个面部表情平静的小孩。王卫丰大概还惦记着昨天夜里天明紧紧搂住他腰杆的那种感觉,还沉浸在那种感觉带来的感动中。他跑到天明身边,蹲下来,抬起头,向天明温柔地笑了。
天明想了想,向王卫丰同样温柔地笑了一笑,慢慢转过身,进去屋了。
王卫丰不会知道,天明的这一笑,代表天明心中的一个决策。那就是,他決定此后尽可能省俭地跟王卫丰说话,既要省简说话的量,又要省简情绪。这是天明能想到的对父亲保持足够敬重,又能让自己不太失落的唯一办法了。这样的决策其实是很艰难的,令天明感到难过,但却也能让天明觉得自己驾驭了一部分的世界。
小晚是个弱智,却能把自己嫁到人人向往的省会南京去,郭金蓝是个生活残缺的女人,却也有办法让自己比王家园里生活完整的那些个女人受男人欢迎,既然天明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小孩,当然也应该有能力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同王卫丰相处。虽然这说起来有点儿悲哀,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小孩心中隐秘的快乐呢?
——张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