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社邑文書校讀札記三則
趙大旺
提要: 本文是討論敦煌社邑文書的三則札記,第一則對“”字釋讀,結合魏晉以來的碑刻資料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證明該字應當爲“三”的俗字。第二則對P.2717作研究,該文書涉及關於喪葬用車的具體規定,提供了敦煌社邑的另一種形態。第三則是對 Дx.6053V 定名的討論,該件當爲“行人轉帖”,而非前賢認爲的“渠人轉帖”。
關鍵詞:敦煌文書 社邑 俗字 喪葬互助 文書定名
敦煌文獻中有大量的社邑文書,對於今天我們了解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民間結社有重要的價值,歷來受到學界的重視。對社邑文獻的整理研究已取得了較多的成績,其中唐耕耦、陸宏基、寧可、郝春文,以及日本的山本達郎等先生分别對社邑文獻有系統的整理釋録,*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一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下簡稱《釋録一》。同書第二輯、第三輯、第五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下分别簡稱《釋録二》、《釋録三》、《釋録五》。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簡稱《社邑》。〔日〕山本達郎、土肥義和、石田勇作編《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資料》第四卷《社組織及相關文獻: 導言與録文(A)》,東京,東洋文庫,1989年,下簡稱《山邑》。寧可、郝春文先生的《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至今仍是學者從事敦煌社邑研究重要的資料來源。筆者參照已出版的敦煌文獻圖版,研讀以上諸家録文,偶有所獲,對前人成果有所補充或訂正,因此草成札記三則,以求教於方家。
S.2041《巳年至大中年間儒風坊西巷村鄰等社條》中,社人名單有“張履”、“張安”,諸家録文均作“張履屯”、“張安屯”。(圖版見《英藏》3,頁193上。録文見《釋録一》,頁270;《社邑》,頁4;《山邑》,頁2)
S.2103《酉年十二月南沙灌進渠用水百姓李進評等乞給公驗牒》,其中有“劉子”,諸家均録作“劉屯子”,郝春文先生在《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一書中直描其形而未釋録,後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中録作“屯”。*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1。(圖版見《英藏》4,頁2下。録文見《社邑》,頁364;《山補》,*〔日〕 山本達郎、土肥義和、石田勇作編《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資料補編: 導言與録文(A)》,東京,東洋文庫,1989年,下簡稱《山補》。頁68、69;《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300)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該字的釋讀影響了對社邑文書的校録與研究。另外,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其他社會經濟類文書中,也常常有該字作爲人名的用例,兹列數條如下:
S.11453K《唐瀚海軍抄牒狀文事目録》有:“虞候狀,定曹仁充虞候判官。”其中該字孫繼民先生録作“毛(屯?)”。*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19。(圖版見《英藏》13,頁280下)
Дx.2163《大中六年十一月百姓杜福勝授田牒狀》有“北張安”、“西至畫子”。(圖版見《俄藏》9,頁56下)
吐魯番阿斯塔那339號墓出土的60TAM339: 50-1/1《高昌武城堛作額名籍》有“張富”,整理者照描其形。*《吐魯番出土文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16。

二 P.2717“結社契”校録研究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書P.2717P2,首尾俱殘,現存四行,據其内容應當爲結社契約。前人整理社邑文書者,均未收録該件,故筆者將本件録出,並進行初步的研究。
《法藏》將本件定題爲“同結兄弟契”,*《法藏》(17),頁348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定題爲“社會文書四行”,*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52。兹據《法藏》(17)所載圖版,及IDP彩圖,對本件録文於下:
(前缺)
1. 内有同活兄弟叔侄遷化者,要輞〔一〕者亦乃一般,助
2. 輞壹片〔二〕。若家内無傷折者,不許亂沾;若有傷折者,
3. 不諫(揀)〔三〕大小,便與隨例。今則立此言約,已後隨例而行。

校記:
〔三〕 “諫”,據文義校作“揀”。
〔四〕 “歌”,據文義校作“哥”。
〔五〕 “僧”,底卷僅存上部殘筆,據字形補。
根據録文可知,本件是關於喪葬互助的規定,據内容,前面殘缺部分應當還有其他的互助項目,但已缺失,僅存關於用車的規定。本件無紀年,其中“李苟奴”又見於以下兩件文書:
1. 北大D.193《羯羊賬》有“丁酉年李苟奴羯羊兩口”,*《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61下。並有“王鄉官”、“韓衙推”等官名,年代當在公元877年或937年。
2. S.7060V《諸色破曆》有“李苟奴母麥一漢升”,*《英藏》(12),頁51。根據該件紀年及斛斗計量單位,當爲吐蕃時期文書。
若以上兩個“李苟奴”爲同一人,此人應生活在吐蕃末期,歸義軍初期。但目前還不能確定本文涉及的三個“李苟奴”是否爲同一人,因此暫難對P.2717P2進行斷代。
在敦煌的喪葬活動中,出殯一般用到兩輛車,一爲“輀車”,置放靈柩;一爲“魂車”,安置亡靈真儀及銘旌等。*參見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風情》,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346—347。此外還需要牛來拉車。如敦煌寫本《搜神記一卷》有:“母患命終,家中富貴,所造棺椁墳墓,並自手作,不役奴僕之力,葬送亦不用車牛人力,惟夫婦二人,身自負上母棺,已(以)力擎於車上推之,遣妻牽挽而向墓所。”*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866。而車、牛的使用卻又價格不菲。如關於唐五代時期車牛的雇傭價格,陸贄在《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狀》中説:“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王素點校《陸贄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56。可見車牛雇價不菲。這種計里給價的方式與敦煌不同,據唐耕耦先生研究,敦煌地區使用車牛具是計日給價,使用一天所需要付出的價格是“麥五斗”。*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頁456。又,S.4525《付什物曆》有:“布兩疋,紫錦壹疋,付車社。又付纈縛壹條,又車社大紅錦壹疋,又大紅錦壹疋,又付車社轝屋紫繡禮巾六條。”S.4525V還有“付車社銀角,其角付戒果”、“付車社陰家官健郭山昌花氈壹領”等。*《英藏》(6),頁125下、126上。這些都應該是喪葬活動中支付車牛的開支,從其交付的色物數目來看,普通百姓是斷然負擔不起的。
正因爲如此,在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中,常常有關於喪葬用車的互助。郝春文根據敦煌文書中的社條對此有過簡要的論述。*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279。目前所見實用性社條中出現喪葬用車互助的有P.3989、S.6537V兩件,文樣也有S.5520、S.6537V兩件出現喪葬用車的互助,但都是籠統地規定。如P.3989《景福三年敦煌義族社約》:“若有凶禍之時,便取主人指撝(揮),不間(問)車轝,便雖(須)營辦。”S.6537V《社條》也有:“諸家若有凶禍,皆須匍匐向之。要車齊心成車,要轝赤(亦)須遞轝。”*《法藏》(30),頁320上。《英藏》(11),頁94。具體如何“成車”?少有材料涉及,而用於通知社人參與營葬活動的身亡轉帖中,目前也未見到關於“用車”的具體要求。惟有P.2717P2具體規定每人“助輞一片”,但由於文書殘缺,無法得知除了“輞”以外,還是否有其他用車方面的資助。“輞”的價格,在S.7060《辰年都司諸色破歷》中有所反映,該卷第三行有:“張定千一片,用麥八斗。”*《英藏》(12),頁50。可見“輞”也並非尋常易得之物。此外,晚唐五代時期,已經有了專門從事喪葬服務的行業,如會昌元年(841)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如有違犯,先罪供造行人賈售之罪。”*《唐會要》卷三八《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817。《五代會要》有“兩市葬作行人白望、李温等四十七人”,*《五代會要》卷九《喪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42。《两京新記》也記載:“此坊多假賃輀車送喪之具。”*辛德勇輯校《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66。關於唐五代時期喪葬行業,參見崔世平《唐五代時期的凶肆與喪葬行業組織考論》,見權家玉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562—580。前文所引S.4525《付什物曆》中有向“車社”支付絲織品的記載,這裏的“車社”應該也是從事喪葬用車的租賃服務的,也就是説,在喪葬活動中,也可以通過租賃的方式獲得輀車、魂車。但P.2717P2結社契中的成員應當經濟條件較差,無力支付租車費用,因此社内成員各自拿出一些部件,組裝成車,勉强使用。從中可以看出,敦煌百姓雖然以結社爲手段來支持喪葬活動,但也是量力而爲,王梵志詩説“富者辦棺木,貧窮席裏角”,*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56。對於棺椁如此,對於用車也當是如此。
本件結社契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立契者題名排在首位的李苟奴身份爲“大哥”,而非如其他社邑文書那樣署“三官”職務,但從其署名位置及自稱“大哥”來看,其身份當爲社内領袖。這一點表明,敦煌的結社並非都如大多數社邑文書所反映的那樣制度嚴格、組織嚴密,也有一些是通過簡單的訂立契約而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結合與中國古代早已存在的“結義”更爲相似,如史籍中常見的“約爲兄弟”,*如劉邦與項羽曾“約爲兄弟”,《漢書》卷三一《項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815。又如公孫瓚,“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45。參看岳德虎《我國古代“異姓兄弟結拜”之考論》,《内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謝元魯《論中國古代社會的虚擬血緣關係》,《史學月刊》2007年第5期;梁滿倉《先秦至南北朝異姓結拜及其對人際關係的協調》,《河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這一風氣隋唐時期仍然較盛,如隋代《韋略墓誌》記載墓主:“弱冠,與州里鄭子春、子信諸從兄弟契。”*韓理洲輯校編年《全隋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42。《魏昇墓誌》也有:“但義兄弟等哀慕崩號,戀同五孝。”*《全隋文補遺》,頁207。唐代王思禮與張光晟結爲兄弟,李抱真與王武俊結爲兄弟,等。*《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573;卷一四三《朱滔傳》,頁3898。從唐後期開始,異姓之間以兄弟相稱的風氣演變爲有一定規範的儀式,如訂立書面的“金蘭”文契。*《論中國古代社會的虚擬血緣關係》,頁7。與明立社條,推選三官的社邑相比,這種結合組織較爲鬆散,成員也較少,在敦煌文書中,類似這樣的結社還有一些,如P.3691V有“四人合爲一社”,P.3372V有“弟兄氾再昌、安醜子二人同心合意”,S.2894V有“淨土寺學士郎辛延晟、曹願長二人等同心一會”,S.6300有“乾元寺隨願共鄉司判官李福紹結爲弟兄”,*《法藏》(26),頁324下;《法藏》(24),頁17上;《英藏》(4),頁253下;《英藏》(10),頁250下。等。本件文書尾部殘缺,從殘存的題名來看,成員也在四人以上,關於傳統“結義”與敦煌“結社”之間的關係,有待結合其他資料進一步探討,本文不再展開。
三 Дx.6053V定名芻議
Дx.6053V抄有兩件轉帖,*《俄藏敦煌文獻》(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34下。各四行,應爲抄件,而非實用文書,從筆迹來看,兩件轉帖應爲同一人所抄。本節討論的是第一件轉帖,目前對其録文研究的僅郝春文先生,郝先生將其命名爲《渠人轉帖抄》,認爲“從其所存内容看係渠人轉帖抄”。*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432。兹據圖版,參照郝先生録文,將該文書重新録文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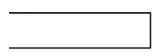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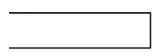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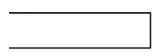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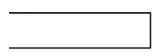
本件轉帖由於殘缺過甚,包含的信息較少,不明發帖事由,無發帖者身份,且無法判定其大致年代。末尾署名“保住”,從字迹看,應當是抄寫者署名,而非原轉帖的發帖者。該轉帖中僅有一處與渠人轉帖相近,即轉帖中“官有處分”一語,常見於渠人轉帖中。但“官有處分”這樣的表述並非僅見於渠人轉帖,行人轉帖中也有,如S.4504V《年次未詳(十世紀前期)十一月五日行人轉帖》有:“全不來,官有處分。”同件《年次未詳(十世紀前期)七月三日行人轉帖(寫録)》也有:“全不來,官有處分。”*《英藏》(6),頁114下,115上。這些均爲行人轉帖,可見,僅憑“官有處分”一語,不能判定本件轉帖屬於渠人轉帖。
該轉帖還有一個重要信息未被注意,即轉帖規定的集合地點: 南門。以東、西、南、北四門爲集合地點,常常見於歸義軍時期的行人轉帖。如P.3070V《唐乾寧三年(896)閏二月二日行人轉帖》有:“限今月十三日,南門取齊。”*《法藏》(21),頁223上。又如前引S.4504V《年次未詳十一月五日行人轉帖》有:“限今月卅日卯時於南門外取齊。”此外,行人轉帖的集合地點還有“北門外”(P.2877V)、“東門外”(S.4504V、P.4017)、“西門外”(P.2342)等。*《法藏》(19),頁245下;《英藏》(6),頁115上;《法藏》(30),頁355下;《法藏》(12),頁160下。而目前發現的渠人轉帖中並未見到如此表述集合地點的。從這個角度來説,上録Дx.6053V應該是行人轉帖,而非渠人轉帖。
轉帖僅規定於“南門”集合,具體是哪兒,對轉帖的通知對象來説,應該是不言自明的。沙州設有子城、羅城,子城爲内城,如隋漢王諒作鎮晉陽,“於宫城之内更築子城,安置靈塔,别造精舍,名爲内城寺”。*釋道宣《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73。郭湖生認爲,在唐代地方政府,“子城爲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監獄皆設其間”。*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國城市史專題之一》,《東方學報》第57册,1985年,頁683。吐蕃時期的S.1438V《沙州某官狀》提到:“右件賊,今月十一日四更,驀大城,入子城,煞卻監使,判咄等數人。”*《英藏》(3),頁19下;録文見《釋録五》,頁320。表明吐蕃時期官府駐地在子城内,因此,子城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敦煌文書中提到南門,多爲子城南門,如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沙州城内有一殿:“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門。”*《法藏》(1),頁48;録文見《釋録一》,頁7。這裏的“城南門”即是“子城”的南門。上引S.1438V《沙州某官狀》還有:“及至子城南門下,其節兒等已縱火燒舍,伏劍自裁。”這裏的“南門”也是“子城”的南門。歸義軍時期,行人需要定期輪番到各城門上值,一般每番三天,如P.2877V、S.4504V、P.4017等行人轉帖均説明轉帖事由是“次著上直(值)三日”,要求行人攜帶武器在北門、南門、東門集合。
綜上,筆者認爲,上録Дx.6053V應爲通知行人到南門上值的行人轉帖,而非渠人轉帖。
附記: 本文在撰寫、修改的過程中得到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劉進寶、馮培紅和古籍所張涌泉等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一并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