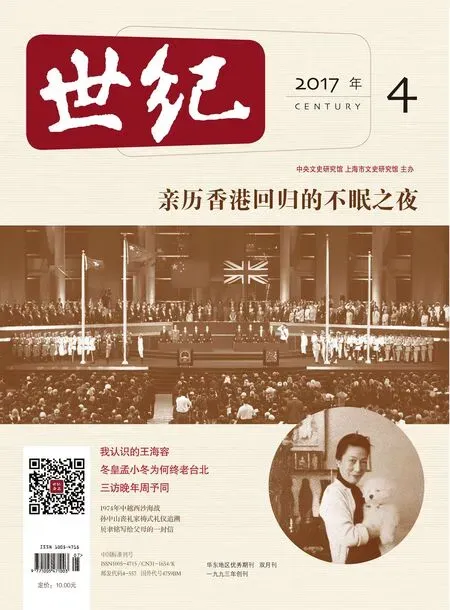高语罕致信林伯渠主动请缨杀敌
黄家猛 史艳蓉
高语罕致信林伯渠主动请缨杀敌
黄家猛 史艳蓉
作为朱德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和参与南昌起义的策划者,革命先驱高语罕越来越受到中共党史学界的重视。随着史料的发掘和对陈独秀评价的日趋客观,与陈独秀关系甚密的高语罕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其生平及思想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笔者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封高语罕的亲笔信函,信中体现的大无畏革命气概让人赞叹。这封亲笔信函保存在编号为“汉15815号”的《高语罕致林祖涵函》的原始档案中,为毛笔书写原件。信函内容很短,现将其内容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伯渠同志转军事委员会诸同志钧鉴:
我愿随中央独立第一师出发,努力杀贼(不要名义)只以中央委员资格参赞一切,因为我与该校学生多少有点渊源,或许有可以效死之处,请即决定示告为荷。匆上即颂党祺。
高语罕
五月十七日
这封信是高语罕1927年5月17日写给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的。
信函背景介绍:高语罕自德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12月,高语罕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埔四杰”。1926年1月16日,高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定为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并与汪兆铭(汪精卫)、邵力子起草宣言,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一起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27年3月,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出席大会。
高语罕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时,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高语罕在1927年3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的社论,出版《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的公民》,抨击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制造惨案的行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高语罕与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其次是武汉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期北伐,期望彻底打倒奉张军阀。1927年4月18日,第二期北伐正式开始。
值此北伐战事正酣、武汉兵力空虚之际,发生了夏斗寅叛乱事件。夏斗寅时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该师本来是武汉国民政府用来戒备四川军阀侵犯首都武汉的部队,但是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夏斗寅同四川军阀杨森相勾结,密谋实行军事叛变。5月初,杨森带领三万川军,由川东出发,入侵鄂西,进犯宜昌。5月7日,驻扎鄂西的夏斗寅秘密行动,响应杨森,还派船帮助杨森运输部队,同时捏造战报,说杨森兵多人众,自己兵力不济,无奈后撤,将军事重地宜昌拱手让给杨森,将所部擅自向武汉方向移动。5月9日,杨森进驻宜昌,派兵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并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夏斗寅则率军乘船东下,经沙市、石首、监利,13日在嘉鱼登陆,随即发出反共通电。在通电中,夏将董用威(董必武)、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焘、李汉俊等视为“宵小之徒”,污蔑“所谓提高党权者,不过提高若辈宵小之权力;所谓权力属于党者,亦是以所有权力属之于若辈宵小之手”。宣扬自己“只有率我将士为民请命,班师东下,扑灭诸獠,去此害马,重建新政,继续北伐,以竣初功”。很快叛军占领了咸宁的汀泗桥,直扑武昌。这时,武汉因为大军北伐,兵力空虚,叛军既有蒋介石为后盾,又有杨森军相配合,并约有何键、刘佐龙等部为内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企图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17日,叛军迫近离武昌近四十里的纸坊镇。武汉国民政府的首都武汉陷于危险之中。
在形势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武汉国民政府无法从前线抽出军队,只得将在汉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改编为军队,开往前线迎敌。其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杨树松为副师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即为黄埔军校,高语罕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之后,兴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高语罕亦为该校政治教官。
值此危机存亡之秋,高语罕主动请缨随学生军赴前线杀敌,于是向林伯渠写了这封信,希望其将信转递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从这封信上的其他文字来看,林伯渠应该是很重视高语罕的这一请求,他将高语罕的信转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终批准了高语罕的请求。在信的结尾处有这样批示:“照准,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前往。”下面有□□(□□似为程潜)和汪兆铭的亲笔签名。随后,林伯渠将此意见书面通知高语罕,旁边有“已作函交高同志,存”等批注。
这封信函的意义:第一,体现了高语罕的崇高人格。夏斗寅和蒋介石勾结发动叛乱时,武汉国民政府军队正在全力北伐,首都武汉兵力异常空虚,而与此同时,四川军阀杨森率部沿襄河两岸协同东征,于学忠、张联升在鄂西北配合行动。武汉国民政府处于敌人的三面围攻的危急形势之中。当叛军逼进武昌近郊纸坊镇时,武汉城内顿时人心惶惶,很多有钱人纷纷外逃,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些人受蒋介石收买,趁机散发一些谣言,有人甚至对夏斗寅表示同情。在此情况下,高语罕等主张坚决同敌人作斗争,彻底消灭叛军,高语罕更是主动请缨杀敌,而且强调“不要名义”,这充分体现了高语罕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

第二,高语罕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作为该校的政治教官,当革命形势面临危急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为学校的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高语罕明白,课堂的政治说教固然重要,但革命危急时刻的表现更能体现政治教育的成果及意义。更何况这是一个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绝佳的机会,虽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有军事训练,甚至包括实弹射击的学习科目,但毕竟不是实战,这次军事行动是检验平时学习训练水平的很好机会,因此作为政治教官的高语罕自然很想看看实际的效果。高语罕对学生军的战斗力没有把握,才提出“与该校学生多少有点渊源”,到时可能有“效死之处”,对即将到来战斗中出现的情况做了准备。
因为史料的原因我们无法知晓高语罕在这场战斗中的具体表现,但他的这封请缨奔赴前线的亲笔信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的革命活动,特别是高语罕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资料的不足。
(黄家猛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史艳蓉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