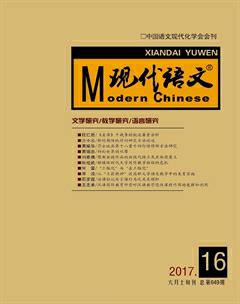从“文术多门”到“以诗为专门之学”
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术”与师承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江西诗派及其后学的实践基础上,元好问提出“以诗为专门之学”,从理论上廓清了对诗歌进行艺术探索合理性的偏见,为之后诗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文术 师承 “以诗为专门之学”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1]的文学理论著作,以其强大的理论体系和全面的理论建构,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刘勰在书中对于文学本体、创作、流变、批评等问题提出的观点,对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可谓“采掇片言,莫非宝也”。
针对齐梁文坛“弥近弥淡”[2]的现状,刘勰在《风骨》篇中指出:“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3]认为讹滥文风的出现,师授未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没有明确的师授传承和法式学习,在准的无依、正式不确的情况下“各适所好”“多略汉篇,师范宋集”[4],“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5]造成“文体解散”“将遂讹滥”的文坛局面。
一、“文心”与“文术”:执术驭篇
针对齐梁文坛之弊,刘勰首先提及的是对“文术”的重视。这是文学研究视角内转的必然趋势,也是刘勰个人的卓越见解和重大贡献。《总术》篇写道: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6]
在此,刘勰详细论述了“术”与“心”的关系:术可学而“心”不可期,宜研术以待“情会”,在对为文之“术”进行认真揣摩领会的前提下,再加以灵感的刺激。若不由文术,徒慕灵感,其上者,则难免会陷入后人所说的“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7]的地步;其下者,则茫然混沌,不知所终。引而申之,这即是“学”与“才”之关系。《体性》篇中,刘勰在承认才、性等先天因素对作家风格、成就影响的同时,着重论述后天学习、所处环境对作家的重要性:“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8]同样主张从可把握、可感知的“学”入手。对“文术”“学”“习”的重视,可以说刘勰实际已道出了重功力、讲法度的先声。
其次,是对师法前人的强调。积极向古人借鉴学习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途经。从《文心雕龙》对前人的总结来看,师法前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文学发展的早期,对前代文学创作风貌的总体学习。二是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在对文学风格作出辨析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作家作师法对象。《通变》篇提及:“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9]这是对前代文学成果的总体风貌学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文学自身发展尚处于早期的自发阶段,整体风貌相对比较单一。“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10],刘勰在对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为概括总结时,也佐证了早期相对比较单一的文学风貌。二是文学理论的不成熟,理论上还不能对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作出准确明晰的判断。在建安文人的诗文评点中,反复出现了“气”的概念:“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祯,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11]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整体风貌下,“高妙”“齐气”“逸气”“异气”是对不同作家之间不同风格的描述,这就与同时代的人物品评注重感性把握相似,诗文评呈现出的是以整体风格的感性概括为主的特点,而并未对不同作家之间的不同风格作出清晰把握。因此,在具体法式准则指导缺席的情况下,对师法对象进行选择时,“随其嗜欲”“准的无依”。钟嵘谓时人:“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古今独步。”[12]在求新、爱奇、尚丽的整体时代风气下,师法“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13],文学创作自然会流向新奇、纤细的一路,结果只能是“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14]。
刘勰提出“文术”“师授”的重要性,针对当时文坛的痼疾,他给出的策略是“原道、明圣、总经”,即取法儒家经典。刘勰认为,“儒家经典实际上具有两方面的文学功能,一方面是可以作为‘文之奥府,具有深刻的思想理念和丰富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可为作者师法;另一方面,经典本身的文学性也极强,具有‘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表达效果,其文学经验亦足资为学文者师法。”[15]“秉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16],从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六个方面学习为文之道。而紧随其后的钟嵘,在《诗品》中则“深从六艺溯流别”“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17]。钟嵘通过深入研究五言詩人的渊源流派,意图廓清诗坛创作和批评的混乱局面,为五言诗的创作确立了具体的学习典范。在师法对象方面比刘勰的更进一步。
二、“文术”与师承:“以诗为专门之学”
此后,赓续“文术、师承”传统的应首推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不论是示人门径,还是提携后进,黄庭坚都有着非凡建树,但在同时代的天才诗人苏轼面前,诗歌艺术成就上的珠玉在侧,导致其与苏轼迥异的理论成果也遭到一些非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黄庭坚提出的广积学问和师法前人。目为才学者有之,鄙为剽窃者有之,虽然有在其理论指导下后学创作的失当之处,但来自苏轼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诗歌创作实践的进行,后学逐渐意识到黄可学而苏不可学,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才真正意义上为诗人所服膺,逐步占据了后世诗论的主导位置。而在这个过程中,“以诗为专门之学”的提出是其关键一环。
“以诗为专门之学”首见蔡绦所著《西清诗话》,《野客丛书》《苕溪渔隐丛话》均有引:“唐人以诗为专门之学,虽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误。”[18]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亦提及:“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赋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9]严羽将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视为有唐一代诗歌繁荣的主要因素,并认为宋诗不如唐诗。这个问题因见仁见智而可以悬置不论的话,那他和蔡绦认为唐人将诗歌创作看成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则范式和技巧,则是深中肯綮的。蔡绦更是指明,“善用故事”是作为“专门之学”的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或者具体技巧,也是强调诗歌的艺术成就在技法上的体现。
将“以诗为专门之学”从对前人成就的褒扬转化为明确的诗歌主张和对时人的殷切期盼,是在元好问手里完成的。元好问在为友人杨鹏的诗集《陶然集》所作的序言中提到:“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以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20]在他看来,后学的诗歌创作欲向古人学习,以期达到古人之境(当然,这个境界是很难企及的),必须要从“追琢功夫”入手,苦吟力学,“死生于诗”。他钦叹杨鹏“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积之之多”[21],认为这是诗艺精进的不二法门。并针对时人对于杨鹏“追逐功夫太过”的批评作出了解释:去圣久远,非追琢功夫,无以追配古人。明确提出了对诗歌进行雕琢加工的艺术要求。此外,还援引杜甫“佳句法如何”[22]“新诗改罢自长吟”[23],薛能“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24]等人的观点,以及唐庚的事例,进一步说明对诗歌进行有意精炼雕琢的必要性。
另外,元好问还在《通真子墓碣铭》《张仲经诗集序》《中州集·李讲议汾》中先后提及“以诗为专门之学”。“以诗为专门之学”的提出,可以说是诗歌创作论认识上的关键转捩,几乎是在理论上承认了对诗歌艺术技巧探索的合理性。意境这一诗歌最高美学范畴于唐代得以提出并得到充分论述后,江西诗派就试图将其具体化为纯艺术技法问题,努力淡化其中才性、灵感、天分等不可知因素。元好问在江西诗派对诗歌炼字、用典、声律、化用等诸多具体技巧进行大量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从认识上一举扭转了前人对诗歌,乃至文学创作的偏见和误解。例如,扬雄《法言·吾子》篇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25]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言:“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视来世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26]裴子野《雕虫论》说:“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27]虽然诸多偏见不乏作者的激愤和论述谋略,但作为一种文本的事实存在,还是给人口实、混淆视听之嫌。
元好问作为文坛盟主时提出的一系列诗歌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基于北方政权中原本位意识而提出的复古理论,既开启了元代“宗唐得古”的先河,又影响了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潮,“荡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外”[28],要求诗歌表达真情实感的“元气”说,实际就是后来“性灵”说的先导。同样,“以诗为专门之学”的提出,也引导着金诗坛逐渐将目光聚焦到詩歌艺术技法的探索和传授上来,与南宋诗坛本土的江西后学一起,共同将江西诗派的核心理论——重功力、讲技法——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主导理论。虽然元好问诗论的出发点是复古,但要达到他所谓技进于道,不烦绳削而自合,以追配古人的境界,指明是从字句的琢磨入手,苦吟多学的门径策略。不论是从策略上,还是诗歌理想境界上,都十分接近地江西诗派。尽管元好问一再强调:“北人不识江西唾”[29]“未作江西社里人”[30]。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中,个人学养功力、诗艺技法的进步有赖于师友之间的切磋与传授,宋代之后诗社活动的兴起即是明证。因此,对师授的重视也是“以诗为专门之学”中应有之义。
三、“以诗为专门之学”与我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点:诗法的理论研究价值
在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提出后,后学就不断对其进行纠正、补充和完善。曾季貍《艇斋诗话》提到:“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说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31]如果说“换骨”“中的”之说还谨守江西门径,在练字、炼句等具体艺术技巧上着力的话,那么“活法”“饱参”的提出,则表现出对江西诗论的突破与补充。吕本中倡言“活法”“悟入”,“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32]从法度入手而渐趋精纯化境,不拘字句。韩驹言“饱参”,悟入诗法正法眼,则可达不思而得的境界,信手拈来,皆浑然天成。二人都是从诗境和法度的关系着眼,试图将苏轼关于诗歌创作境界的理论纳入到江西诗法中来,直欲融合苏黄,以此来突破江西诗派在诗境上的樊篱与困境。和元好问同一时代的严羽,则以“别材”“别趣”“妙悟”“意兴”等对诗歌意境的着力探索,来荡涤江西后学的弊病:“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33]但其将读书、穷理看成诗人自我修养的必备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34]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严仪卿有‘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非教人废学也。”[35]《师友诗传录》中说:“夫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为读书者言之,非为不读书者言之。”[36]。相比之下,元好问“以诗为专门之学”的提出,则在诗法与诗境的平衡中,实现了对江西诗学的批判继承:将境界宗唐、门径法宋正式确立为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的古代诗学主导模式。
在诗境上,努力学习唐人浑融圆贯的诗歌意境,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意在言外,旨冥句中”,正是元好问所提倡的诗境:“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也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强调将诗人的诗艺表现技巧完美地融入诗歌创作中,风韵天然而无斧凿痕,不烦绳索而自合。在门径上,则取法江西诗派及其后学所指明的策略道路:多读书,广积学问;重视法度、技巧的传授与学习,从古人的诗歌创作中汲取艺术经验。以广博的学识为底蕴根基,辅以师授法度技艺,苦吟力学,达到浑然天成、韵味无穷的诗歌境界。这实际上是给出了一条完备的诗歌艺术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创作理论指导体系。这也跟《庄子》里提到的“庖丁解牛”“痀偻承蜩”有相通之处,虽然庄子重点在于说明进行艺术创作时的“虚静”状态,但其客观意义上也反映了欲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离不开长期的技艺实践和练习。
之后的诗学理论,则是沿着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不断丰富完善,然不外境界、门径两途,不能出其范围。主境界者则滋味、神韵,重门径者则格调、肌理,但二者并非是冰炭殊途不可调和。无论是元初月泉吟社对练字练句和格律技法的重视,还是元中期京师诗坛在师法对象上对介于唐诗宋调之间李商隐的选择,抑或有明以降诗坛屡屡兴起的复古潮流,以及“神韵”“格调”“肌理”等诸多诗歌理论的产生,其诗歌风貌气度或各有其形,然贯穿在其中的主线精神:对技法、功力的重视,确是一脉相承的。进一步来说,主境界者又何尝抛弃过对法式、技巧的重视和探索呢?
清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的集大成时期,康熙诗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家莫过于朱彝尊和王士禛。朱彝尊论诗尊宋调,重学问;王士禛崇唐音,主性情。然朱彝尊并非不谈性情,王士禛也不是不讲学问,只是理论重心不同而已。作为清代诗坛艺术理论贡献最大的“神韵”说,虽然王士禛的理论重点在于追步严羽而独标神韵的诗歌艺术境界,注重自然入神、意味无穷的诗境建构,但其在对待具体的技巧法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在王士禛弟子郎廷槐和刘大勤分别编著的《师友诗传录》《师友诗传录续录》中,详细记录了王士禛在与诗友、学生的切磋问答中,对于学问涵养、诗歌技法的见解和重视。诸如“五古句法宜宗何人?从何人入手简易?”“七言长短句,波澜卷舒,何以得合法?”“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若何?”“律诗起句,易涉于平,宜用何法?”“诗中典故,何以活用?”[37]等问题,在对具体诗歌技法的阐释中,将一颗为后学指明诗艺进步详细门径的良苦用心擦拭得分明。
重术者不讳情,主情者不废术,然术与情皆有法可循。这正是元好问之后诗论发展到成熟阶段对法度技艺与性情诗境的理性认识,而对于这种诗歌理论的发展而言,元好问的开创之功是毋庸讳言的。至于这种精神的有时而晦,即是矫枉过正,标榜“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性灵”说对诗坛的颠覆,其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的弊病,前人之述备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庶几近矣。
综上所述,从“文术多门”提出对文术、师授的重视后,在江西诗派进行大量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元好问“以诗为专门之学”的理论澄清,使得这种有赖于师友传承的重功力、讲技法的诗歌理论最终成为我国古代独具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主导。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2]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20页。
[3]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14页。
[4]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20页。
[5]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55页。
[6]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56页。
[7]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页。
[8]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08页。
[9]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20页。
[1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20页。
[11]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14页。
[12]钟嵘:《诗品》,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3]钟嵘:《诗品》,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4]钟嵘:《诗品》,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5]郭鹏:《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谋略》,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6]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1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18]王楙:《野客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页。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1頁。
[19]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20]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2页。
[21]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页。
[22]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4页。
[23]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5页。
[24]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1页。
[25]扬雄:《法言》,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26]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4页。
[27]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73页。
[28]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2页。
[29]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30]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31]曾季貍:《艇斋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6页。
[32]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1年版。
[33]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34]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35]沈德潜:《说诗啐语》,《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啐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3页。
[36]王士禛等:《清诗话》,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5页。
[37]王士禛等:《清诗话》,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3页,134页,138页,150页,153页。
(姚晨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