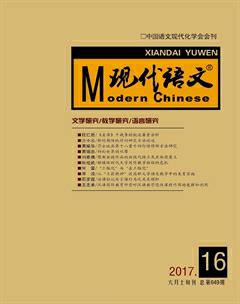十七年抗日小说的英雄叙事研究
摘 要: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英雄形象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红色英雄”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独特的英雄叙事特色,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包含着复杂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十七年 抗日小说 英雄叙事 文化精神
一、引言
十七年时期是充满理想主义和红色激情的时代,十七年文学是大力张扬、崇尚、讴歌英雄的文学,不同文学题材塑造的“红色英雄”形象成为十七年文学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英雄形象作为“红色英雄”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独特的英雄叙事特色,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包含着复杂的文化精神。
二、英雄叙事特色
(一)英雄的起源
弗莱认为在传奇英雄神话中,英雄出世一般和洪水密切相连,并构成周而复始现象的常见象征。可以这样理解:洪水对英雄而言是出生非同寻常的隐喻,也是人生灾难和苦难的开始,是英雄成长和升华的必经之路,故洪水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没有灾难和苦难的烘托,就没有英雄后来的耀眼光环。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英雄的出身和起源同样离不开苦难和灾难。但是它和英雄神话中的自然界天灾水患不同,而是来自人间社会属于人祸的阶级、民族压迫。在苦难中磨砺与成长,寻得光明之途,成为英雄形象成长道路上必经的“门槛”和“路障”,有深重苦难与灾难,英雄就仇恨的对象和动力,就有对其进行阶级、革命身份的确认,也就有英雄形象身上纯净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
十七年抗日小说的英雄形象出身来源在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的显现。一般情况下,英雄的阶级身份和血缘身份一致,二者关系“纯净”和“明朗”,是正统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出身。而这种单纯的身份确认似乎注定了英雄家庭的残缺不全,即英雄早年往往是“无父”“无母”或“无父无母”的文本现象。“无父”现象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母子与《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母子,无父无母的“孤儿”形象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与《烈火金刚》中的丁尚武,这形成了传奇英雄的血缘父亲“缺席”与“不在场”的独特景观。进一步交代血缘之父缺席的根源往往涉及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革命主题,这样,英雄出身的孤独和苦难的根源不言而喻就和革命联系起来,英雄的革命行动便有了顺理成章的依据。另一方面,残缺的家庭和不幸的人生经历为英雄寻求“精神之父”和“革命之父”提供了契机。血缘父亲或母亲的“缺席”位置正由抽象的革命的“精神父亲”将其填补,对英雄的革命之路起到精神引导的“引路人”形象往往是小说中的政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形象李正,文本中的这类形象往往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符码。英雄们在“精神之父”和“革命之父”教育引领下,阶级意识苏醒,逐渐由狭隘的家族复仇观念升华到民族、国家、阶级复仇的思想高度,完成对其革命性与阶级性身份的验证与确认。
有时,革命英雄的出身来源是复杂的,并非纯正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身份与血缘身份的“错位”是抗日小说中较罕见的文学现象。不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英雄总要经历身份蜕变,果断斩断与家族的血缘伦理关系,从而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这种背叛阶级身份的文学形象多是来自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女性,如《烈火金钢》中的何志贤和《平原枪声》中的苏建梅。在《烈火金钢》中,当丁尚武发现自己搭救的革命同志林丽就是他的杀父仇人的孙女时,一心找何家复仇的丁尚武就立时要置她于死地。林丽自辩说:“……我恨这个地主家庭,我和何家的关系已經一刀两断了。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这是地主阶级的血债,……我是一个革命战士。你救了我的命不错,但这是同志的义务,是战友的责任。”[1]“同志”者,“志同道合”也,通常人们将它们自然而然地捆绑在一起成为“革命同志”,这不仅是一种称谓,也是对被称呼者的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可和确认。何志贤只有与何家割断血缘伦理关系改名换姓为革命战士“林丽”,并站在她的地主兼汉奸双重身份的父兄对立面,她才获得对其革命身份的合法性确证与认同,才会受到革命者的保护而免遭她的革命同志丁尚武欲为家族复仇而施加给她的厄运和灾难。正是这种“革命战士”身份取代了她天生无法选择的阶级和血缘身份,“同志”这一称谓才成为她生命的“护身符”。非但如此,丁尚武对林丽的救助反而成了“同志的义务”和“战友的责任”,可略见“同志”之严肃意义与丰富内涵:在它的管辖下,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只有共同的阶级敌人与革命对象,可消除同志间的个人恩怨。
(二)英雄的形塑
弗莱发现:传奇中的英雄总是“与春天、黎明、秩序、富饶、青春及充沛活力联系起来。”[2]英雄代表光明、希望和一切正面价值应该是人类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渴望和期许。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脸谱艺术对人物性格、身份具有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正如《说唱脸谱》总结的“……蓝脸的多尔礅盗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脸谱的夸张性、装饰性,具有强烈的寓褒贬、别善恶的文化功能,符合读者深层的民族心理与审美习惯。
十七年抗日小说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同样具有鲜明的道德化倾向。它包括对英雄革命肉身的赞美和英雄内在革命精神方面,对英雄革命肉身的塑造从年龄和形体方面进行书写。就生理年龄而言,传奇英雄多处于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一般在十八九岁至三十岁之间。如《烈火金刚》中的肖飞二十岁,《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二十八岁。还有一种英雄类型是儿童形象,如《敌后武工队》中勇敢的郭小秃,《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机灵的韩小燕,他们均是十二三岁的“人小鬼大”的少年英雄。这些年轻的青春英雄们充满生命的巨大能量和蓬勃活力,在革命战争中焕发出光彩,带给人们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烈火金钢》中齐英就称赞那些能打善战的民兵们:“个个年轻力壮,精神饱满,真赛过小老虎一般。”这样年轻的英雄们的革命肉身富有雕塑般的美感:或者英俊健美,或者强悍粗犷,都散发出男性的魅力。马英“气宇轩昂”,武工队员赵庆田和贾正的肉身形塑具有“神话”色彩:“他俩那种勇武威严的劲头,真像那为群众守家、被群众喜爱、贴在两扇门上的两尊神像——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什么样的鬼怪妖魔碰见也得牙颤腿抖、浑身哆嗦。”[3]这样潇洒、英俊、健美的男子汉形象加之他们崇高、伟大的思想和革命行为,使得女英雄对他们也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意,吸引着革命异性的目光。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女性和革命男性共同构成了富有朝气的英雄群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在胜利与挫折的交错中不断成长,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当然,这些传奇英雄形象如刘洪、杨晓冬、肖飞、史更新等此时已不同于传统民间中的侠义英雄,他们与梁山好汉、岳家将们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有时他们身上也流露出传统文化中“侠”和“义”影子。他们是在现代的革命战争中,经历血与火的洗礼而成长起来的,因而带有更多的“革命性”,在他们身上所凸现出来的,是革命战士的崇高觉悟和高尚品质,在他们的人生信念中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
总之,通过传奇英雄们革命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形塑完成对其“革命”“阶级”等政治身份的认同,它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高大、完美、伟岸的英雄肉身总是倾向革命的,这与其英雄行为相得益彰,完成了对革命英雄谱系的传奇书写和对其阶级身份、革命身份的自我塑造。这些健康、健美、年轻的革命身体也不禁让人们反思:“当身体不再有任何疾病时,社会意义也就可以直接书写在人们的身体上,因而这种新的身体是一种直接表达意义的身体,它必须而且只能接受积极意义,只能作为一个博大得多的想象性社会主体的外延和细节。”[4]
(三)英雄的爱情
爱情是人类文学世界中永不凋零的花朵,也是人类文学表现中亘古不变的主题。特别是文学中的“英雄”与“美人”故事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英雄美人”的文学创作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表现为一种“革命+恋爱”的文学思潮,在抗战时期的30、40年代,这一文学传统仍然得以延续,如《新儿女英雄传》和《吕梁英雄传》在小说的结尾最终完成革命与爱情双重的大团圆。因为英雄故事里单单有革命情怀还不够,那是表现英雄阳刚之美的,爱情故事则使英雄具有了侠骨柔情,属于阴柔之美,刚柔相济,阴阳互补方是完美世界。这样传奇英雄革命行动中点缀的零星的爱情故事为紧张跌宕的传奇故事涂上一抹稍许浪漫的玫瑰色,形成一种新的“英雄美人”模式。
按照爱情关系的多寡,英雄的爱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的爱情线索和爱情关系,如《铁道游击队》中刘洪与芳林嫂;《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与汪霞;《烈火金钢》中的肖飞与志茹等。爱情的描写往往是针对主要传奇英雄而言的,非主要的传奇英雄的私人情感则语焉不详,成为“空白”与“缺失”,体现出创作者对这类叙事的“节制”与“克制”。另一类型的爱情关系稍复杂些,它有多对的爱情关系,近似“三角恋爱”的爱情模式,如《平原枪声》中既有马英与苏建梅、云秀的“两女一男”的恋爱模式,同时还有作为“内线”的革命者郑敬之与秦方芝之间单一的爱情模式;《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高自萍与银环隐含了这种“三角恋爱”中的“两男一女”模式。在忠于“革命”与忠于“爱情”的公私选择中,多数传奇男英雄们义无反顾地表现出“革命优先”的原则,将私人生活的感情问题让位于“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将爱情置于一边,但他们总能在最后结成革命伉俪,完成革命和爱情的“大团圆”。与这种美好圆满情形相反的是出卖革命的叛徒对革命女英雄的爱情追求往往徒劳,成为梦幻泡影,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自萍和《敌后武工队》中的马鸣即是例证。“世俗幸福的获得者终归还是革命者。此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世俗幸福的态度,是既有排斥,又做了‘定向控制和‘定向分配。”“革命文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告了革命者对优质情爱资源的最终占有,并赋予这些优质爱情以神圣的革命意义。”[5]
英雄的爱情表明十七年文学包括抗日小说在内的爱情选择不是传统观念中双方在贫富、家庭、财富、地位等方面的“门当户对”而是革命前提下政治思想方面的“门当户对”。当然,在文本中表现和关注的焦点仍是英雄们的革命业绩和外在的革命神性光环,关于英雄的感情叙事只是零散地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而这种爱情叙事也显然是“革命化”的。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完全纯粹的“爱情话语”,它与革命话语一起成为小说最后“胜利大团圆”模式的一部分。“革命”主题成为这类小说文本的叙事重心,占据主导地位,爱情表现则成为它的陪衬和点缀,处于不起眼的位置。这样的爱情故事很显然是作为革命话语的附属而存在的,这也是讲述历史的年代文学规范的结果。相较之下,发表于建国前的《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爱情叙事则显得相对复杂和世俗化。而爱情叙事叙述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革命事业高于个人生活,革命工作大于私人情感,爱情的圆满与革命的胜利相伴,偶然出现的爱情的夭折也与革命的艰巨性和残酷性相关,引起的是对敌人的更加仇恨和對革命的更加坚定,最终以革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为落幕,实现结为生死与共的革命夫妻的理想结局,达成爱情和革命的双重和谐。
三、英雄叙事的文化精神
(一)传统文化精神
陈思和认为十七年文学的“革命英雄传奇”的英雄人物塑造借鉴了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方法,“在人物性格配置方面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6]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抗日小说《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丁尚武、肖飞、孙丁邦、孙振邦是如此,《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王强、林忠、鲁汉、小波也同样如此。此外,飞行侦查员肖飞又带有《水浒》中浪子燕青的精神气质,手持大刀英勇杀敌的丁尚武和《平原枪声》中带有侠义之风的王二虎则具有“黑旋风”李逵、牛皋二人的鲁莽与豪爽;在《敌后武工队》里,叙述人甚至直接将武工队员赵庆田和贾正比为勇武威严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可以看出,抗日小说对古典传统小说和民间文艺资源的吸收利用,使得英雄人物的塑造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很容易让读者阅读时唤起了他们的“阅读记忆”,从而与古典小说的阅读经验发生联系。“在传统传奇小说文本的运作与现代革命演义的运作之间便可以达成一种秘密的会合与交换。现代革命演义是通过非政治运作使得小说情节故事在读者阅读中获得合法性的。”[7]
(二)政治文化精神
十七年抗日小说的英雄叙事包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精神,无论是传奇英雄们,还是作为英雄敌手的对立人物,政治道德化是衡量他们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标尺,“革命性”与“反革命性”是二者之间鲜明的“楚河汉界”,英雄人物形象的“神祗属性”和敌人的“魔怪属性”从“革命”的“神性”与“反革命”的“魔性”方面隐含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讲述历史年代的政治文化特征。
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英雄们多处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他们代表着新生、理想和希望,他们朝气健壮、英勇善战,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信念,关于他们的传奇英雄叙事使小说文本充满明朗乐观的感情基调,就现实意义而言,新生政权的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新的政治乌托邦理想的实现等需要调动人们的革命干劲和建设激情,青年作为革命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尤其需要引导和教育,使其明白革命历史的来龙去脉,了解革命先辈英雄的伟大壮举和崇高的革命思想,并希望他们以英雄为楷模榜样,获取精神动力。李英儒曾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图,“青年们没经历过战争”,所以,革命历史小说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给青年同志们精神上一点鼓舞”[8]这正是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所在,正如毛泽东在《冬云》诗中对英雄的赞美:“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只有完美无缺的英雄才是人们的学习效仿对象,英雄身上那种对于革命不利甚至相抵触的“世俗性质”需要剔除,这种过于政治道德化的英雄人物塑造方法也导致一定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使得英雄的高大形象走向革命的“神性”光环,“世俗性”的一面被剔除殆尽。
(三)人类英雄文化精神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十七年抗日小说的红色英雄也是人类英雄文化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英雄崇拜是沉淀在人類心灵深处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与情怀,关于英雄的神话寄予了人类对超越自身的美好期望。人类在不断观照自身中发现了人的缺陷和弱点,这种认知让人类深感沮丧,因此文学世界中英雄形象的创造就成为必然。被形塑的英雄形象包含着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美好祈愿,成为判断人类行为的价值标准,引领人类不断前行。他们身上往往具有完善的道德和无穷的力量,通过移情作用,人们感受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志,从而弥补自身的缺憾。
英雄形象的塑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英雄形象;即使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推崇的英雄也是形象各异。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英雄。特别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剧烈动荡的节点,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和崇拜显得格外急迫。悉尼·胡可说:“谁救了我们,谁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们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们。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锐危机,必须有所行动,而且必须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9]因此,十七年文学世界中伟岸、高大的英雄叙事既是外在世界中历史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人性召唤的一种理想结果,是历史中的传统文化、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与人类英雄文化精神综合因素造就形成的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十七年抗日小说的英雄叙事亦是如此。
注释:
[1]刘流:《烈火金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2]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3]冯志:《敌后武工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2页。
[4]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5]余宗岱:《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2,73页。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7]程光炜:《<林海雪原>的现代传奇与写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8]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7,528页。
[9]王清彬等译,[美]悉尼·胡可:《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