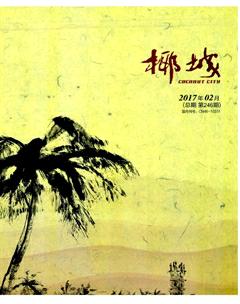海口那些老地方(散文诗组章)
陈波来
中山路
如果有一层若有若无的薄雾,铺抻在这条老街,相信是来自民国的。
虽远,但总能触手可及。
比如你看到的百年骑楼,从民国一直周折到眼下。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看见的:
比如回乡的银两秤出来的传说,春潮与爱,与望穿秋眼的落寞……
比如我相信每一扇花格子窗后面,必有一个香艳而诡异的身影,它因为没有说完故事而日日附身于姿色撩人的女子——
从骑楼甬道的暗影里迎面走来。
水巷口
巷口原先是紧靠码头的,不像现在,靠海的地方都被盛大的楼盘占据。
原先,一条巷子都在担水。靠岸的船要补水。
渔夫或水手趁机下了船。银钱在他们的口袋里水耗子一般弹跳着。
他们疲沓的身心,早被无边的海摇晃成了一条空巷子,要用岸上的烟火和脂粉填补。
每次到水巷口,我惶惑于眼前,这又一栋翻新的骑楼:
到底是那时的水房,还是别有滋味与故事的所在。
长堤路
机动渔船,一艘艘泊在对岸。有楼层的船尾高高翘起,闪烁的信号彩灯,飞舞的条带,斜刺向天的天线……仿佛彼岸,消匿于一片凌乱的船尾。
它们带来海上的凌乱。
渔船越来越高大,惟这泊船的河口越来越狭窄。河床抬升。
以前放倒一块木板,就可以在船与岸之间搭一条路,并且随便可以找到称为岸的地方。
现在,堤岸已成市街,城市吆喝着车流与楼盘,逼迫,挤压。
机动渔船,因此一艘艘泊在对岸。
惟渔歌低微而凌乱。
老街口
老街口越来越接近于车水马龙的行车道。
一辆违章驶入的土豪金的小车,轻易地撕裂街口恪守的古老姿态。花墙、有雕饰的立柱以及在各种方言里曲折延伸的廊道,很快变得斑驳杂色。
仅仅,隔一段石板路;一个拐弯;
一个张望的瞬间。
但,走进老街口,就觉得还有那么多眼睛,在窗后与墙上看着。
一片斑驳杂色中,一个人做出旧貌新颜的样子。
一个人在突然飞驰而过的救护车的呜呜声里,吹了几声——
只有自己听见的口哨。
得胜沙
一捧沙里,应有光阴如许:柔白中有呼啸的粗粝,且呈异色。
一片沙上,一段驱寇与凯旋的往事,被吹散又聚拢。
……被聚拢又吹散:只是人与事恍惚成一些远远近近的影子。迷失的人,迷离的眼神,迷幻的、与之纠缠不清的肉欲的欢场。
一条似曾丰腴的外沙河流啊流,倏忽消失,只剩枯干的称谓。
不要往沙里细看,一粒微沙足以硌伤眼睛。
沙堡如城,白日繁喧与静夜深谧,反复氤氲其上。
沙在一点点往下滑落。
盐灶路
原来海是近的。
原来海就在脚下。垒灶。生火。海心甘情愿地沥干水分,成为你的纯洁晶莹的盐。
生活因此有了滋味。品读一种烟火,也有了滋味。
原来,只是你与海,只是一个垒灶。然后越来越多……
原来是村,越来越大,挤成了老城一条街。
现在,海很远了。
远到随掬一捧海水,都有可疑的糜烂气味。让人无法亲近。
于是你洗净了手,香火代替了那烟火。细绵。若有似无。
宜于风中飘摇。
滨海新村
一度是这座新兴之城高尚的租赁地。
连片的小楼,烘托出山头一样的草莽与虚荣。各色公司在镀金的招牌上变换名称,皮包里有的是大小项目。英雄不问出处。
她从一辆走私车下来。咸味的热风掀动深蓝色将军呢的半腰裙,露出一小片凝脂。
她在那个下午略显高傲的侧影,輕易地,和椰子树的冠叶撕在一起。
不过三十年,新村已旧,像时光,有着太多被用坏的部分。
一个人又转回被电线扯乱的巷子:寂寥,冷清,间杂有高低的市声。
从小卖店的老板娘漫不经心的眼神里,他似乎看见,撕在一起的椰叶,低垂下来。
龙华路
你曾经沉默、荒芜,愿意与闹市保持一点疏离。像这条街。
青春扯动盲目的旌旗,在椰树上飞舞,你还需要长大。像这条街。
柴油发电机在每家铺面的屋檐下突突作响,发动起跃进和开发的年代。岛上的第一个冬天,就让你如火如荼。像这条街。
你有太多可以用来纪念这条街的:比如纠结的长发、流行于那年的米色风衣、闯海人才有的焦灼的眼神……比如南宝牌啤酒和金梅州香烟。
这条街仿佛一夜间,爬上高楼又滑落地面。但它得用一段时间去变旧。
用一段与你青春等长的时间:平淡已成习惯,斑驳也是。像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