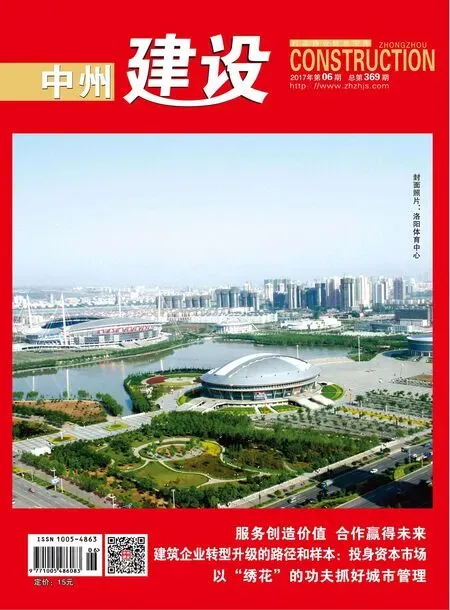罗马:没有终点的城市
文 / 胡颖蓓
罗马:没有终点的城市
文 / 胡颖蓓

城市规划是一个过程,从来没有哪个规划有过真正的完结篇——正如老话所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因为城市规划总是伴随着城市发展,不断进行自我修复式的更改,有时表达的是尊重,有时则是妥协。正是如此,规划使城市变换出无穷的魅力。如今我们在罗马所见的古建筑,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前。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罗马一直在通过引导新城建设、外迁部分城市公共设施及政府办公职能,从而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1997年,罗马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其历史城区范围总面积扩大到约6500公顷。老城内以多样性为原则,保留了一些公共设施、政府办公及居住功能,既保留了历史的原真性,又使城市充满了活力。
场景化和生活化
规划师对罗马的最初印象,很可能是诺利地图[詹巴蒂斯塔 诺利(Giambattista Nolli)于1748年所绘制]。他将城市表现为一个具有清晰界定的建筑实体与空间虚体的系统。城市仿佛一幅历史地图,让人不禁对古老的场景充满想象。历历在目的,是纳沃纳广场上演的激烈海战演习;西班牙大台阶让人不由回想起好莱坞的浪漫电影,跃跃欲试地吃一支奥黛丽·赫本尝过的冰激凌。那些陈列在游客们面前的古建筑和古遗址,更令人震撼不已。时钟好似戛然而止停留在某一个时刻,一幕幕都显得不那么真实。
这一切归功于意大利对建筑历史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强大能力。1889—1890年,米兰的高等工业学院,开始讲授历史建筑保护的研究、保护和修复的课程;1892年,通过了保护古建筑的法律;1960年,罗马大学建筑系设立古建筑保护的研究生院;1955年成立了“我们的意大利(Italia Nostra)”这一保护历史建筑的民间组织,旨在宣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它拥有几十万会员,下设资料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和教育机构。1966年,在罗马设立了名为伊克洛姆(ICCROM)的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意大利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理念,及其成熟的修复技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罗马不仅有让人啧啧称赞的博物馆和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生活趣味的地方。这才是罗马得以生生不息,并被世人公认为美好城市的最重要原因。
和所有具有吸引力的大都会一样,罗马既有时尚光鲜的T台走秀和美女华服,也有流离失所的乞丐和流浪猫。这个城市不是因游客、考古学家或是政客们而存在的,而属于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
很多文章都提出,欧洲历史建筑之所以能保留下来,而中国建筑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建筑材料大多使用了易于保存的石材。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后者采用了适当的修缮工程。罗马的历史建筑每隔几年都会在旅游旺季过后的9月进行维修,每年维修不同批的建筑。维修期间,通常采用绘制着原来立面的防雨布进行遮蔽,在维护清洁和安全的同时,又使城市风貌不会过分难堪。这种做法的成本并不高,却非常有效。
历史城市的街道大多非常狭窄,不便于市政设施的设置。工程技术规范和历史街区保护,经常是一对矛盾,也常常困扰城市建设者们。然而,简单选择拓宽道路,或将历史老街打造成古建筑陈列馆,使之变成一处旅游景点,也未免太令人失望。因势利导,摆脱固化思维,采用吊灯的方式,则不仅避免占用原本就狭窄的城市道路,还能满足日常照明需求。这种在路当中设置吊灯的做法,在欧洲的小街道中比较多见。
不仅如此,生活化的城市把古典的艺术元素运用到新建筑的细部设计,从而使历史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延续。如佛罗伦萨的潮流服装店的马赛克铺地,就像极了不远处主教堂的马赛克地面。
包容和尊重
场景化和生活化的两个城市特性和谐共融,关键是城市的包容性以及尊重的气度。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看似是针对物质层面的协调,但也揭示了有关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城市设计是一个城市不断演变的过程,通过时间的累积,不断完善,展现对历史的尊重。如果做任何项目,都把周遭一切先夷为平地,无视他者的存在,追求标新立异,都是简单、粗暴、野蛮的行为,更谈不上“设计”两字。
以连接西班牙广场和圣三一教堂的西班牙大台阶为例。圣三一教堂由法国国王在1495年资助建造,而西班牙广场上的“破船雕塑”是在1627年由意大利建筑大师伯尼尼父子设计,此时的大台阶则还是一条通往山上教堂的泥泞小路,直到1725年,法国大使赞助修建了直通教堂的台阶。这三者的组合,是经典且富有趣味的,演绎出各大王朝、教会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又将罗马洪灾的历史融汇其中。
其次,好的设计不仅是“以貌取胜”,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把握。设计必然带有设计师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判断,而能得到公众认可的设计才被认为是好的设计。这需要设计本身展现出对公众的尊重。
正是源于对公众目光的关切,即便是由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大师特拉尼1930年代设计建设的法西斯宫,在科莫这个湖光山色的历史小镇中,也并不显得太过于光怪陆离。
罗马也不是没有让人反感的建筑项目。如位于罗马广场群一角的白色大钢琴——威尼斯宫。游客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个还不错的建筑。然而,它却是个十足的假古董。在罗马当地人和意大利建筑师的眼里,它与周边环境十分不和谐,甚至被当地媒体评为最丑陋的建筑之一。可见,建筑和城市美不美,不仅要经历美学眼光的考验,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估。
继承和引领
如果说那些历史建筑群展现了设计对城市文脉的尊重,那么,当代新建筑则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激发城市新的活力。
罗马历史城区的北侧曾举办过罗马1960年奥运会。2000年,由大师伦佐皮亚诺设计的罗马音乐厅,如今尤为引人注目。音乐厅由三个主题组成,像是趴在山体上的三只昆虫——只是形态高度抽象,强调与周边山脉、植被等自然环境的融合,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也得到了公众认可。然而,在开工之初打地基时,角落居然发现了一处古罗马遗迹。当即,所有施工建设工作被喊停。设计师根据地下文物的范围,调整了部分原有设计方案。新实施方案保留遗迹原址不动,就地形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兼具室内、室外场馆。而这座音乐馆也成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化演艺场所。让出的一部分原有演出建筑面积,则被移到音乐厅入口处,并被设计成一个露天音乐厅。设计师的设计手法和对空间的利用非常巧妙和别致。再深入参观建筑的细部设计,你更会发现,现代的建筑结构和材质运用,与历史遗迹的结合,显得和谐优美。在这个项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建筑大师,对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所持有的谦卑平和。这不由让人敬佩。
在音乐厅不远处,是2010年开馆的罗马maxxi现代艺术馆。虽然这组建筑是由怪才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但新建筑的肌理与其周边的兵营建筑也形成了某种默契。更何况,设计在人流组织上完全符合行为动线的流向。从建筑的社会效益看,这确实是激发当地活力,复兴城市旧区的一帖好药。
城市畅想
我们总会羡慕欧洲小镇的人情味,和美国都会的振奋人心,以及日本城市的可爱精致。然而,要知道每座城市都深深烙下了其蓬勃建设时期的时代烙印。
欧洲的城市以中央火车站和教堂为中心,勾勒出宜人的空间尺度和惬意的生活场景,就像欧洲人一样享受着玫瑰人生。美国的城市以高效为特色,最大程度地展现了资本的力量,亦如美国人民一样简单直爽。日本的城市享有岛国智慧的立体城市格局,淋漓精致地演绎着超现实的未来科幻城市生活。
我们的城市建设呢?令人感到兴奋又困扰的是,我们的城市同时面临各类挑战。如上海,既有类似欧洲城镇的历史,也有美国城市开发的影子,近来又表现出日本城市对精细品质的诉求。或许,沉迷于某一个城市的美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好的城市,总是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