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的大都市:城市观念》译者随笔
文 / 叶齐茂
《嬗变的大都市:城市观念》译者随笔
文 / 叶齐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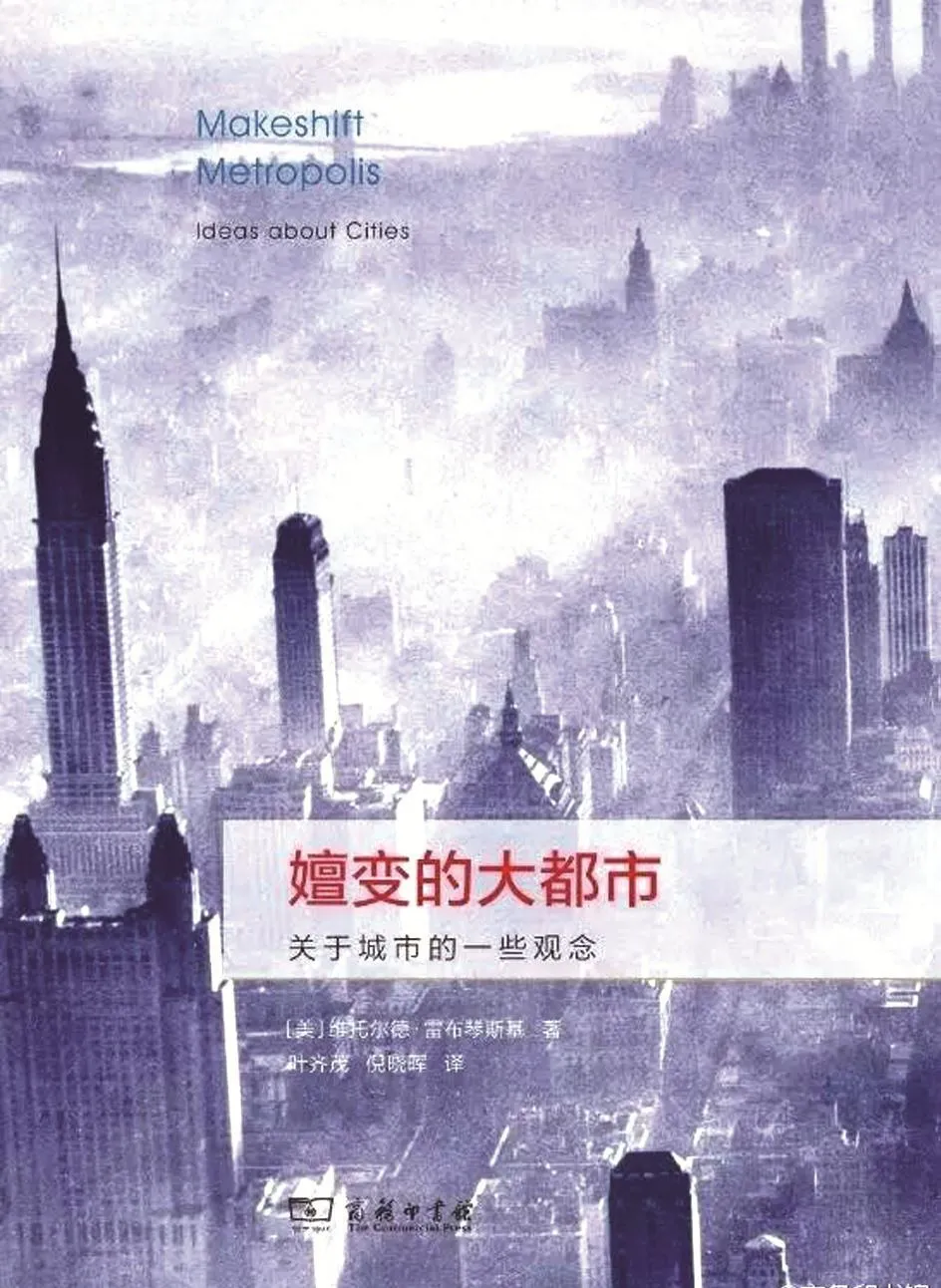
在《嬗变的大都市:城市观念》这本书中,雷布琴斯基教授用一个章节来阐述的那个“毕尔巴鄂异常”现象,用来嘲讽美国城市建设一贯攀比、跟风、赶时髦的那句美国俗语“跟着琼斯走”(to keep up the Joneses),用来为那些被媒体、房地产大亨及其大众称之为“给猪抹口红”(it's like a pig lipstick)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们叫屈的“世界贸易中心场地”设计案例,用来说明“雅各布斯大妈的偏方”(mother Jacobs home remedies)如何不灵验的那些案例,还有用来反复忠告规划师和建筑师不要把城市设计仅仅看成纯粹技术问题的那些案例。
《嬗变的大都市》的确值得一读。书中说的美国那些事,的确也成了当今中国的这些事:
“在任何一个时期,那些与商业利益相似的力量,富足、民间的追求、对未来的自信、一种认为自己的时代举世无双的感觉,需要自己的特殊表达形式,都在给公众对地标性建筑的欲望火上浇油。”但是,“毕尔巴鄂效应”可能最好称之为“毕尔巴鄂异常”,因为实践证明,很难复制“毕尔巴鄂效应”。
“公众的需要有可能创造城市的形式,但是,带有这种毕尔巴鄂效应的需要常常具有负面的效果。”“公众对新奇的需要不仅已经扭曲了建筑,也扭曲了城市设计。特立独行的建筑通常造成不良的城市邻里,一个标志林立的城市可能面临成为一个主题公园的风险,或者成为拉斯维加斯大街的风险。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个古板的19 世纪的建筑布局中,古根海姆美术馆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城市设计的成功范例,如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乔治王朝的爱丁堡和伦敦、19世纪的巴黎,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它们的街道和广场,以及运河的品质,它们民间建筑次序井然的美。当今城市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创造标志性建筑,而是创造出更多的这类布局。”
“美国的城市一般都会‘跟着琼斯走’。如果洛杉矶放弃有轨车,于是,有轨车即刻成了不时尚的东西;如果芝加哥建设了一条城市高速路,这条城市高速路就成了一种模式;如果纽约建设了一个文化中心,于是,较小的城市随之效仿。”
“纽约市最终选择的七个国际团队所提出的建筑项目,一般都忽略了这些现实的约束,集中考虑的不过是建筑形式……‘这就像是给猪抹口红。除开我们有了许多围绕这项重建工作而展开奇思妙想的建筑师外,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依然还在设计着同样的东西,不过稍微好看一点而已’……但是,亚罗的批判遗漏了这个一个观点:奇思妙想的建筑师和美丽的建筑模型,恰恰是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鼓动公众去追求的东西。”
“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期待在城市生活,否则,我们不会建设如此之多的城市。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期待生活在城市,而是我们期待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里。紧凑的城市还是蔓延的城市?老城市还是新城市?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并非很久以前,通过生活质量,我们还很容易区分大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当时还存在着时髦或世故的城里人和乡巴佬,以及那些陈旧观念所传递的差异。而现在的郊区和远郊区的性质,使我们很难确切地定义,哪里是城市结束和乡村开始的地方。”
正如雷布琴斯基教授所说,“城市不是在真空中成长起来的,城市社会物质需求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不仅仅不能在形体上把城市与历史分割开来,同样,我们也不能在思想上把城市社会物质需求与历史分割开来。”这不正是我们当今思考“新型城镇化道路”时必须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吗?
《嬗变的大都市》是一本有关“城市观念”的著作。也许那里讲到的“宏伟构想”,我们并不陌生,但是,那些“宏伟构想”的历史命运究竟如何?那些“宏伟构想”如何演变成“跬步”“模块”,最终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我们还需要聆听雷布琴斯基教授娓娓道来。所以,我力荐各位读者,抽时间读读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