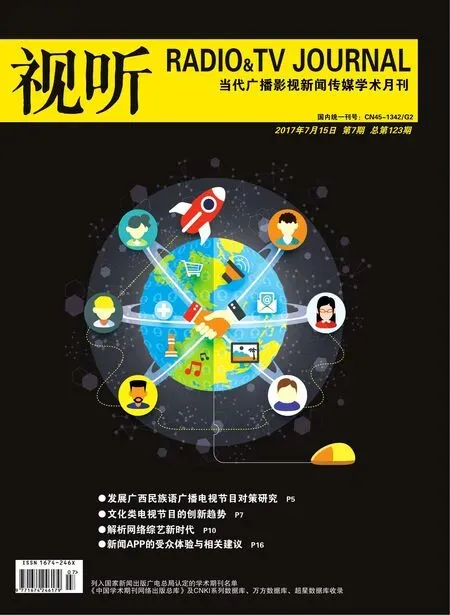踏莽寻猿
——记邦亮保护区东黑冠长臂猿的拍摄之路
□谈圳
踏莽寻猿
——记邦亮保护区东黑冠长臂猿的拍摄之路
□谈圳

东黑冠长臂猿是全球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此前已经在国际上被认定灭绝,但于2002年被重新发现活动于越南北部山区和中国广西境内。目前全球数量只有110只左右,中国境内有20多只,全部生活在我国靖西县境内和越南交界的喀斯特森林里。作为十多年来第一家拍到过东黑冠长臂猿的电视媒体,笔者与同事们蹲点在没水没电没信号的山里数日,最终采制完成并播出了新闻作品《中越携手保护全球极度濒危物种东黑冠长臂猿九年增添两个“新家庭”》和《探访“观猿人”》,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本文从一位亲历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记录了这段珍贵的采访经历。
题记
“山里过得不记日子,我们在里面久了,常常连亲人的生日都忘记了,但是那天新出生的小猿快满月了,我们还商量着是不是要给他们办一桌满月酒庆祝下。”
整理同期声时候,听到邦亮国家级长臂猿自然保护区队长韦绍干这句话时,脑海里立马又浮现出了他大男孩一般的笑容,仿佛一切都那么轻松畅快。其实,去过保护区我们才知道,在石山里队员们平时连喝水是收集来的雨水,用来洗脸刷牙都是浪费,煮包泡面吃就算是珍馐。没有电没有信号,他和队员们却常常要一个月住上十几天,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前才能回来,坚持追踪观测长臂猿十多年,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观猿人”的坚守,全球仅存100多只的濒危物种——东黑冠长臂猿才能被人类逐渐了解,才能更好地加以保护。
而我们作为新闻人,有幸能把他们的工作展现给观众,让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在为了濒危物种的保护而努力,了解到他们坚守的价值,我觉得我和同事们再辛苦也都值了。
心向往之
作为一名正牌的八零后,小时候,每周响起动物世界的片头音乐时,你都只能在电视机前找到我,身边还并排坐着我老爹,爷俩目不转睛。
电视机里高速飞奔的猎豹把羚羊扑倒后气喘吁吁而猎物却被鬣狗叼走,百兽之王狮子怒吼着驱散秃鹫才能抢到食物,河马竟然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幼崽踩死鳄鱼,这些美丽绝伦的镜头即使是通过黑白电视屏幕看到也显得如此地生机勃勃,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动物们的呼吸触手可及,那时候我对摄像机、摄像师的工作还没有任何概念,也绝对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后,我也有机会亲自拍到野生动物的镜头,并且可以浅显地体会到一个野外摄像师的不易。
有备而来
2016年下半年,和搭档赖秋羽找到中越联合保护东黑冠长臂猿的选题后,因为拍摄对象是我们从未涉猎过的野生动物,就开始谋划如何从软、硬件上能够满足这次拍摄。
得益于从事电视新闻行业十年有余,我积攒了许多宝贵的摄像经验,但平时拍摄对象多以人物、静物为主,即使对要求最严苛的时政拍摄,拍摄地点也无非就是会场或者走访现场,变数相对可控,用光、构图的标准已经了然于胸;然而,多位有野外拍摄经验的前辈提醒,野生动物的拍摄可完全不一样,野外不仅环境恶劣,情况复杂多变,而且由于天生的警惕性,遇到自己觉得受到威胁的环境,野生动物们远远的就会离开,有警惕性高的甚至离人三四百米远就绕道了。
在整个准备阶段,请教了拍过野生动物的纪录片部老师,也请教了喜欢拍野生鸟类的摄影爱好者,这一圈聊下来,我倍感压力,我知道:想要拍到一段合适播出用的镜头,不仅仅是有风餐露宿准备和吃苦精神就可以的,在软硬件上都要有所准备。软件上,除了过硬的拍摄实操经验积累,更需要掌握动物的活动规律,以及长期耐心的蹲守,甚至天气因素都很重要。除此以外,更需要的是专业级别的硬件达标——为此我专门打报告从播出部借出了四十倍的佳能长焦镜头和专用配套三脚架,加上索尼的PDW-700高清蓝光摄像机,索尼EX1R小高清,组成了一大一小、一长一短双机拍摄的基本硬件保证,心里才稍微定了神。而因为爱好摄影摄像自购的设备这次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去的同事吴新顺背上了最新的便携式航拍器Mavic Pro,可以从空中以“上帝视角”鸟瞰长臂猿生活的喀斯特森林;我则带上了可变焦拍摄的三轴稳定器大疆osmo+,以及固定器可以将其佩戴在身上解放双手,以第一人称视角真实记录石山里,我们手脚并用游走在危险边缘的攀爬行进画面。
由于事先做了充足的沟通,了解到山里没有电,我们还特意备足了够用足足三天的电池,这一车的设备把一辆越野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为了减轻负担,能把这些设备全都扛进山里,最终我们甚至连换的衣服都没有带,穿着仅有的一身衣服,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湿了干、干了湿,三天后出山时,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是厚厚的盐渍,连不沾水的冲锋衣领口袖口全都已经变色。

踏莽听猿
尽管做了充足的拍摄准备,心理上也再三告知自己,这趟“寻猿之旅”行将不易,可是其困难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如何不易?
事实上,在采制的第一条新闻播出后,我曾在自己的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很多人看了后,觉得那句我把这次采访当作“最后一次”,说的是自己的工作态度——但事实却是,在邦亮喀斯特山林里的那72个小时,我真的不止一次以为自己回不来——步履蹒跚手脚并用地从近乎垂直的石山上攀爬上去后,站在没有半寸平地的山顶朝下回望时才知道后怕:脚踩手扶的每一块石头随时都有剥离的危险,来时路的每一个落脚点都是可以瞬间变成万丈深渊;表面看上去如同平地、盖满树叶的石缝不止一次让我们陷入踏空,甚至受伤,每次艰难地拔出脚来才看清:原来每条石缝都深不见底,肆意吐露着冬天石山的寒意……
山里的日子,我们每天天没亮就从露营点出发,近百斤的设备由大家分担扛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石山密林里。伴随着天色渐渐亮起来,不知道名字的鸟叫声忽远忽近地从树叶间来,当天亮到我们刚刚能够看清路的时候,几声不同于鸟叫的声音从大山深处穿破密叶丛莽而出,似哨鸣般悠扬又如同笛音般婉转,美丽的歌声逐渐由缓变急最终变成高低不同数个声部的重奏,回荡在山林里,更萦绕在我心间,久久不能散去,这时大家才仿佛完全醒来,精神为之一振,知道我们要找的精灵就在附近。其实事后我才知道,当今世上十多种长臂猿,每一种甚至每一群的啼叫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东黑冠长臂猿的叫声在长臂猿家族里最为委婉悠扬,是长臂猿中的“女高音”。
林海窥猿
我们用了近一个小时“爬到”观测点之一“老狼洞”,在一块突出的山体上架好长焦镜头的摄像机,保护区工作人员负责用双筒望远镜大范围搜寻,一旦找到了再用单筒望远镜仔细定位。这说起来似乎很轻松,但是对于我这样连真正长臂猿影子都没见过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第一天的等待一无所获,第二天等到上午九点多,随着一阵不同于风向的树木摇动,保护区的人员拍了下我小声说:200米外的树上有一只黑色未成年猿。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绿色为底色的树林中,满眼都是斑驳的黄黑绿三色斑点,揉揉眼睛再仔细看:除了密密麻麻的树叶,还是树叶……慢慢地,过了十分钟,我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芝麻大小的黄色色块,明显逆着风的方向运动在树尖上,我赶紧把摄像机镜头慢慢推上去,没想到,黑白的寻像器这时候又帮了倒忙——满眼的树叶这时候变成了黑白两种颜色,我又找丢了方向。
尝试了数次之后,高度紧张的我汗流浃背眼睛生疼,几近崩溃有些一筹莫展,只能改为用摄像机自带的彩色液晶屏去找。虽然平时对摄像机操作十分熟练,但是这时似乎任何经验都用不上了,仿佛这会儿只是单纯地考验眼力的时候。这茫茫林海中,用镜头找猿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定下心来,借助低亮度的液晶屏,我最终惊喜地找到了坐在枝头的东黑冠长臂猿,忧郁的眼神,毛茸茸小脸,黑色的是幼猿和成年公猿,成年母猿则是黄色的。镜头里的它们行动优雅,用修长的手挂在树上,穿行在林间是如此悄无声息,它们三五成群或悠闲自得地摘食树叶,或懒洋洋地坐在树干上互相梳理毛发,以家庭群为活动单位的猿们还会紧紧抱在一起睡觉取暖,别提有多可爱了。
屏住呼吸拍了整整一盘90分钟的蓝光碟之后,长臂猿的一家仿佛知道我已经有足够的素材,就慢慢地隐入了树林。保护区的队员们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蹲守第二天就能看到长臂猿,而且还是这么绝佳的位置。在回到营地后,看了这些可爱的镜头,保护区队员说这些镜头是他们工作这么久见过的最清晰的东黑冠长臂猿的画面,我们也是拍到东黑冠长臂猿的第一家新闻媒体。
执念为信
2017年1月27日 1∶37分,点了“保存”按钮之后,我如释重负地关掉编辑软件,长出一口气:近一个月来,梳理十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剪接为了紧凑而俩字一刀的同期声,编辑跨越五种拍摄机型的画面,7分37秒,整整199刀,终于完成了自己这农历年的最后一条新闻——走近“观猿人”,而这天是大年三十,刚好给猴年划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
尼采说过,“一个人若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所以,在旁人看来,困苦的生活状态是用来“忍受”的;甚至作为旁观者,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否明白自己为了什么而坚持。这就像走近“观猿人”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职业存在;在朝夕同处了72个小时后,我们感叹他们工作生活如此艰苦,且为他们的“坚守”而敬佩不已;在采制结束后,编辑新闻的时候,一次次地看到镜头里,他们谈到自己被毒蛇咬、摔下山间被滚落的巨石砸中等种种惊险的工作经历,都是哈哈地一笑而过……年三十凌晨时分的新闻中心编辑机房里除我以外四周空无一人,我却忽然醍醐灌顶,有种遏制不住的冲动,想要隔着屏幕和我们的“观猿人”紧紧拥抱一下:不被别人理解,却执着于自己的选择,恐怕,我们走的都是同一条艰难的路!
(作者单位:广西电视台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