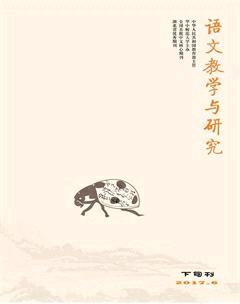平衡术
谭舒尹
我将一条条木枝以手掌为支撑点一层层叠出枯树的模样。这棵“树”延伸的枝丫已经长达两米。我的左手微微发抖,大滴汗珠顺着我的鬓角滑下,为了保持住木条的平衡,我不敢呼吸。“砰”地一声,房门被踢开了。父亲手拿酒瓶,摇摇晃晃地撞进来。他俯下身捡起散了一地的其中一根木条,边笑边用木条有节奏的拍我的脸,“你喜欢玩这个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个‘不正经。”
他总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孩子,我却不这么认为。不就是喜欢几根脏得发霉的木条?要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我也答不上,只是每当我拿起一根木条,并让它在我的摆布下平衡于空中,我的内心会感到平静。
五年前,母亲和父亲离了婚,她嫌弃他,和一个有钱人住城里了。那以后,父亲开始以酒代饭,喝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父亲抽完我,丢下木条,淡淡地说:“你走吧,我养不了你了。”
我找了一个旧布袋,将我的木条装进袋子里。我很幸运,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母亲曾说过,城里人就不一样。不过,地铁站,有很多同我一样的人,有带着一把吉他,一把口琴,走到哪演到哪的。有画画的,在给路人画肖像。我,只有木条。
“喂,小子,你碍着我道了。”一个满口黄牙的人朝我吼。
“你是哑巴还是脑残,我和你说话呢!”
“你是不是找揍?”
那黃牙抓起我的布袋甩出十米远,我朝布袋走去。别惹事,别惹事,我内心在祈祷。那一晚,我带着伤痕入眠。妈妈,您骗我,您说只要我不招惹别人,别人就不会欺负我的。
接下的几天,我在地铁站口尝试着我的平衡术表演。欣赏这种“活”的人不多,有时听到咣当地硬币入碗声,我知道,是路人对我的随意施舍。这天,一位老先生上前来找我搭话,“好小伙。看你半天了,叫什么名字?”我有些惊慌,双手抓紧了手里的布袋。
“哈哈!不用紧张,我叫孙明。你这‘活,在我们这里不多见,你愿意和我走一趟吗?”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毕竟,我要活。
孙明将我带进他经营的茶馆。茶馆面积不大,但人挺多。
“以后在这儿演吧,吃、住我包了,”孙明拍拍我的肩,“咱这有个常客是个大富老爷,看惯了相声听腻了小曲儿,想来点新鲜的。”孙明拉我到一张桌子前坐下,接着说,“这周日,这老爷要给他小儿子办满月宴,你就拿出绝活来,让老爷开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靠厨房边的小仓库腾出来给我做房间,吃喝住练都在房间里。周日,外面隐隐传来唱戏的声音,我坐在房间里发呆。
“到你表演啦,”孙明轻叩我的房门。
“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传统艺术表演——平衡术!”主持人下台来,拍怕我的肩。为我伴奏的是一个弹古筝的姑娘,婉转的琴声响起,全场安静下来。我拾起木条,集中了注意力,找到平衡点后开始一根一根叠加。叠到长达一米,琴声中夹着观众的赞美;长达两米时,琴声节奏放慢,观众轻轻感叹;加到了二米多时,琴声渐渐变弱,我屏住呼吸。
“儿子!”琴声戛然而止,木条散了一地。多么熟悉的声音。母亲!正当我想开口回应的时候,坐在观众席前排的那位富老爷站起来拉住她的手,笑得一脸恶心,“怎么啦?宝贝!上个厕所回来怎么变奇怪了,你认识那个小鬼?”母亲什么话也没说,眼睛却一直看着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愣愣地站在原地。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她,她大概过得很好,精致的妆容,娇嫩的皮肤,和我记忆中的母亲完全不一样。
收起了对母亲再次唤我的期待,我蹲下来将我的木条收进布袋,站起来向众客鞠躬致歉。就在那礼毕抬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母亲的泪眼,至今,我都不敢形容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我发现我自己并不那么厌恶母亲了,她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不能决定天“下不下雨”。
回到后台,孙明担心地跑过来,紧张地说:“没事吧,小兄弟?”
“没事。不过,我要离开了,谢谢您照顾我。”
“唉,没事就好,年轻人多出去走走也好,磨磨心性。绝活么,大多是闯出来的。对了,这里有些钱,你拿去。”
我用孙明的钱,买了一张去A市的车票。
学校:广西大化县高级中学
导师:唐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