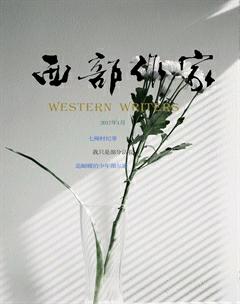追蝴蝶的少年图尔逊
帕蒂古丽
大个子图尔逊在堆满草垛子的院子里追我,我爬上草垛子,他拽住我的小裙子往下拉,我小裙子一提,就上了院墙。
我一边大声喊着“图尔孙,图尔逊”一边跑。图尔逊就是维吾尔语停下的意思。
我在院墙上跑,图尔逊在院墙下面追,眼睛里有不甘和余怒,那不甘是不敢上墙上来抓奔跑的我,那余怒是我偷偷翻进他家的院子,在草垛子上翻跟斗,弄乱了他垛的草垛子。
他先开始像赶一只做错了窝的兔子一样追逐我,我的惊惧和尖叫让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拥有足以征服一个黄毛丫头秘密武器。
我被他黄黄的眼仁里突如其来的光亮吓住了,他捂住自己的嘴,向我摆手,示意我不要大呼小叫,从院墙上下来。我知道他不敢上院墙上追,那样他就会输给了院墙外村里人的眼睛。
院墙上飞奔的我,完全不像是受了追逼惊吓的兔子。图尔逊像是被一只堵住他去路,在他面前飞来飞去的蝴蝶惹恼了,不小心一时失控。我是那只猛然间引逗起他追逐之心的蝴蝶,他只想征服那股弄不懂的飘忽,又害怕追急了,蝴蝶翻墙落地摔坏了翅膀。
那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我未长成的身子柔软如猫,纵然从房顶上落地,也不至于跌断翅膀,况且院墙外堆积着的虚土有一尺厚,轻捷如鸟的我落下去,顶多像一只麻雀从一根钢丝上飞临地面,估计连一星土花都不会溅起。
我得意自己贏了,赢在我能挑逗起这个高挑得像一棵白杨树一样的少年,发疯一样满院子追我,我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的他。
图尔逊输得眼睛里冒着怨毒的火,仿佛我戳醒了隐藏在他身体里的另一个他。他终于抛下另一个他,拍打掉衣服上的墙灰和杂草屑,垂头丧气地进屋去了,留给我一扇关闭的门。
一个没捕到蝴蝶的少年,也许觉得那只蝴蝶不属于这间阴暗的屋子。我张开翅膀愣在墙头,那种挑逗他的刺激的快感还在,被追捕勾起的的紧张和兴奋还没有消退,剧烈的心跳把尖叫卡在喉咙里,像一股旋风被院墙围住,急切地在院子里盘旋。
多少年了,蝴蝶保持着振翅的姿势。那是我玩过的最惊险的飞翔的游戏,我像站在悬崖边上,从高高的院墙往下看时,想象中坠落的快感让我尖叫不止。
身体里的危险被我喊出来,我用危险吸引少年,武装自己,那种危险像悬崖边上蝴蝶突然停住,用颤栗的翅膀诱惑追捕它的人。身体里还有一些细微到看不见的东西,被少年追我的脚步追索、盘问,而我还在懵懂中,尚不明了被追逼和讨要的到底是什么。
仿佛我的身体隐藏了一种危险的东西,似乎那种东西是他边追边塞进我的身体里,他要追上我,就是要拿回他放进我这里的东西,在口袋里或者裙子里,他不帮我指出来,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不知道的东西才会散发危险的气息。
只有他抓住我的脚,往下拉我的裙角的时候,那种东西突然像光点一样闪动了一下,很快就熄灭了。那是一只蝴蝶的秘密,很轻,随时都能被少年带走。
图尔逊的那间挂满乐器的小房子里,我只记住了躲避他的过程。我从屋子的这头跑到那头,扶着墙跑,手指掠过那些明晃晃乐器的线,碰撞出各种声响。他长长的身体紧随着我,他完全可以一把逮住我,像老鹰一样按住我,他长长的四肢稍一舒展,就能占掉半个房间。
我眼里的吃惊与恐惧,像两枚钉子将他的脚钉在地上,他仿佛怕痛一样,只把上半身尽量倾向我,两只长胳膊长臂猿一样伸过来,那像一个预备跑过来的姿势,又像是要接住我的样子,我无论往哪个方向跑,只要他原地转一转身子,把胳膊伸直,我就像一只球一样,顺利地落入他用十根指头为我编织的篮筐。
我惊恐中夹杂着好奇回头看他,那是扔给他的小小诱饵,让他不致在我的惊叫中失去追逐的勇气,我害怕这场游戏的结束,胜过了害怕这场游戏本身。他像围猎一只刺猬一样,不敢来抓我,只随着我转,好像从哪个方向触及我,对于他来说都很棘手。
在他看起来我似乎很受惊,仿佛将要被老鹰吞没的小鸡,其实我只是兴奋过头,那种被吞没的想象,使我感受自己怦怦的心跳,紧张中带着一种满足感,跟害怕不一样,似乎对某种不明袭击暗暗的好奇和期待,却看不知道它会来自哪里,又会袭向何处。
雪天里,跟图尔逊捉迷藏,我飞一样地绕着房子的四堵墙跑,在房子的一个拐角,擦伤了左边的乳苞。它硬硬的,未成熟的杏子一样,有着坚硬的核,从墙棱子上猛地蹭过去,擦破的皮碰触摩擦棉衣的里布,钻心地痛。
我用憋气锁住喉咙,努力不使自己叫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身体上凸起了两个尖苞,左边的尖苞跟墙的摩擦阻止了我的飞奔,墙像刮刀一样刮过去,刮掉了杏子嫩嫩的皮和黄黄的绒毛。发现两只小杏子的惊喜,一时间盖过了刺心的擦痛,那种惊喜似乎比刮刀还要尖锐。
从小喜欢跟我捉迷藏的图尔逊,后来成为有名的乡村乐手,我在一个又一个婚礼上看见他,他在弹唱中用目光和我捉迷藏,那些快乐诙谐歌曲的间隙,他用打飞眼、抛飞吻来追逐我,随着心跳加剧,乳苞鼓胀,我的左乳里隐隐地有一丝痛,像对那次擦伤的纪念。
多年以后,乐手图尔逊他用年轻的生命跟死亡捉了一次迷藏,在一个冬夜里死于醉酒。父母为他取的图尔逊这个名字,也没有将他的生命留住。
每个冬天,我的左乳都用肿胀和疼痛,来祭奠那个漆黑的冬夜里追逐我,第一次帮我发现它的人。每次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左乳就用隐痛来回应我,仿佛在说,那个几十年前的雪夜里,跟我捉迷藏的少年还在,他就躲在我的左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