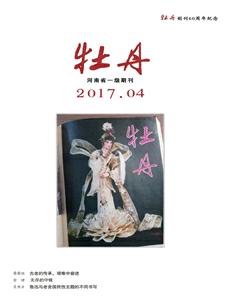偶然性事件在小说中的功与限
陈晓
《倾城之恋》与《家》这两个文本都把偶然性事件(战争和地震)作为小说实现圆满的契机,微小的个体也通过偶然事件的发生而与宏大的历史实现了联结。但是,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这种圆满只是暂时性的、无法永久,源于作者旨在通过偶然事件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另外,偶然事件对矛盾的“镇压”效力是有期限的,所以在新的矛盾产生时又必须出现另一轮的偶然事件进行补救,如此往复,导致小说叙事进入了不断循环的怪圈。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第一个对偶然性与必然性进行区分并深刻理解其本质的哲学家。他认为偶然是事物存在和发展中不经常出现的东西,是一种“遭遇”或“机遇”。偶然是不经常,偶然事件是不经常、意料不到的事情。但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偶然事件的发生是有用意的,而且是惊人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如果似有用意,似乎也非常惊人。例如,阿耳戈斯城的弥堤斯雕像倒下来,砸死了那个看节庆的、杀他的凶手,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张悦然的《家》这两个文本中,均出现了偶然性事件,并且偶然性事件对故事情节起着重大的反转作用。在《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的倾覆成全了一场爱恋;在《家》中,一场大地震成全了现代大都市无数青年男女的自我拯救。其故事情节的最终转折都由极具偶然性的事件(《倾城之恋》中的战争、《家》中的地震)促成。宏大的历史与微小的个体通过非常态的偶然性事件实现了联结,偶然性事件也对文本起着惊人的作用。
一、偶然性事件的情节效力
细察这两部作品,人们可以发现,结局所出现的新转机皆由于极具偶然性的非常态事件:一场战争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裘洛和井宇出现和解的转机源于一场大地震。偶然性事件的出现使故事情节发生逆转,似乎是一把万能清洁刷,把所有矛盾一扫殆尽。
在白流苏和范柳原反复纠缠的爱情角逐中,战争无疑是最关键的催化剂。白流苏两次从家出走,目的就是嫁柳,为自己赢得稳定的生存保障,此时心中并无爱情的苗头;而只有在战争倾城的那一刻,当一切物质、利益都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刻,她才抛下了现实和功利的谋生需求,真正爱上她身边的这个人。而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提到:“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他们把彼此都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仅仅是战争所引发的一刹那的悔悟,使他们不得不抛下世俗的算计而真正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助成了这场倾城之恋的缔结。通过战争和死亡的洗礼,白柳二人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不可把控,从而抛下了自身防范的盔甲,真正从心底焕发出真心。
张悦然的《家》描绘了现代大都市生活的一成不变与按部就班,使人渐渐迷失在由物欲和功利堆砌而起的牢笼中,逐渐失去生命力。生活犹如一潭死水,泛不起一丝涟漪。于是,爱情终究抵不过对自由与生命的渴望。裘洛和井宇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同一天逃离了死水般的生活,奔向寻求自由和自救的路途。井宇离家后到了地震救灾现场,他在写给裘洛的信中说:“每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生命迹象。这个词总是能够让我兴奋,仿佛抓住了生活的意义。”拯救生命的同时,井宇也在拯救自己,在救灾中重新意识到个人的真实存在和意义。裘洛和井宇两个人的出走是对六年同居生活和爱情的叛逃,而在地震中出现的那个酷似裘洛的背影,则提供了新故事发生的转机。
二、偶然性事件的精神效力
为何一对平凡男女的爱情需要一个城市的倾覆来成全?为何现代大都市的青年男女需要一场大地震来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因为阻碍他们的因素背后有着远非人力能撼动的强大支撑。这坚不可摧的支撑就是现存的整个人类社会秩序,一切矛盾和阻碍圆满的因素也都根源于此。既是症结之所在,那么要使一切达到圆满,根源就在于毁灭整个文明。这就需要一场非常规的、毁灭性的灾难来实现——把一切都销毁,再重新开始。张爱玲选择了一场倾城战争,张悦然则瞄准了大地震。这些非常态的偶然性事件并非只是实现圆满结局的简单道具,作者想通过其传达的是对整个文明的批判。
“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
“到原始人的森林里”意味着远离了文明,离开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只有在没有物欲功利和社会世俗干扰的情况下,白柳之间才有真心和爱情可言。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人的本质是爱欲,文明社会造成人的爱欲压抑,使人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所以,张爱玲最后以一场战争揭露了现存“文明”的虚伪,也倾覆了这一切虚伪,还给人类以本真的面貌。这不禁令人唏嘘:最有条件获得爱情的人,都需要通过倾城来成全,在这个“文明”之下若要真心地相爱是何等的艰难。所以,只有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家》中裘洛和井宇生活在后工业文明发达的现代大都市,每天过着固定刻板的生活,就像是日程表操持下按时准点游走的傀儡,毫无一丝生气。就如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的一样,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越多,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和否定性的空洞的“单向度人”。这就不奇怪为何井宇出逃后会如此感叹:“想想剩下的大半人生,觉得一点悬念都没有了,就觉得很可怕。”马尔库塞在其另一部著作《爱欲与文明》中认为文明建立在对人的本能进行压抑的基础上。马尔库塞还指出,在当代越加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文明对人的压抑有增无减,并渗透到人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和心理機制也更加异化。裘洛在已为人母的友人哄小孩之时,产生了如此念头:“这个小女孩知道她妈妈的双眼皮是割的吗……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在说谎了,连母亲那双冲你微笑的眼睛,都有可能会是的。”连母亲都是谎言的携带者,连人类最初始的母爱竟也有可能是虚假的,社会竟变异成如此虚伪之至。井宇在给裘洛的信的最后写道:“这里的志愿者像蝗虫那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是抱着自救的目的而来的。”后工业文明重压下产生了千千万万像裘洛和井宇一样的青年男女,需要通过救助罹难者来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自我拯救。“文明”的痼疾之深,已经不存在任何力量将其修正,只有通过天崩地裂、山峦颠倒的毁灭,才有可能重新开始,恢复到人类初始的本真。
三、偶然性事件的叙事怪圈
非常态的偶然性事件(《倾城之恋》中的战争、《家》中地震)的发生,使情节得以逆转而转向大圆满。但是,这种圆满和转机又是暂时性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偶然性事件只是暂时提供一个归宿,暂时把矛盾冰封,等到冰雪消融,矛盾又会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
“仅仅是一刹那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就算是倾城之战所换来的谅解,也仅够他们在一起活个十年八年,相爱需要通过倾城来实现,那耳鬓厮磨的长久相守又需要什么来成全呢?“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于是,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家》中裘洛和井宇经受不了现代大都市物欲生活带来的虚空,纷纷奔赴地震救灾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灵魂。但“提起行李箱”便消失于人海的潇洒真的就可以使人得到灵魂的救赎而重新拾起人生真实的存在吗?在地震救灾中固然可以通过对其他生命的救援释放那颗长久被都市物欲所强压的心,重新获得生命自由和真实的快感,但地震结束之后呢?“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他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结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重新过上没有自由和解放感的生活。”毕竟“一个小资产阶级主体要逃离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历史结构,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把灵魂的救赎寄希望于一个偶发事件,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可靠而不得已为之的事情,所以当地震结束,他们的灵魂拯救之旅也宣告结束。
尽管《倾城之恋》的结尾,白柳二人有了婚姻的结合,看似圆满,但读者仍能感到其中无尽的悲凉,并没有真正大圆满的那种欢乐、温暖的氛围。吴福辉说:“任凭你读《倾城之恋》的结尾如何粗心,这时也会猛然悟到怪不得缺乏一种‘大团圆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气氛。”但张爱玲多少还敢让一个城市倾覆来成全白柳二人,而到了张悦然就显然缺少了魄力:大地震所换来的只是圆满结局的一个看似可能的转机,地震中的那个神似裘洛的身影也有可能不是裘洛,故事只在出现了一个似有似无的转机时便戛然而止了。所以,作者所借助的这些偶然性的灾难事件并不能给故事带来真正的圆满。在这里,偶然性的灾难事件看似万能的其实又是无力的。人们禁不住要问:矛盾的缓解总是依靠着偶然事件,而当偶然事件的“镇压”失效,旧的矛盾又开始发作或新的矛盾又将产生,那么此时,面对这些新旧矛盾,是否又必须得依靠另一个偶然事件,才能换取另一短暂的春天呢?假如《倾城之恋》和《家》有续篇,十年八年后的范柳原和白流苏已把倾城之时所获得的谅解消耗殆尽,地震结束后的裘洛和井宇重新面对令人窒息的生活,此时,故事若想继续向着圆满发展,岂不是又要借助偶然事件的发生来缓解矛盾吗?一个城市的倾覆才换来白柳二人十年八年的和谐,那他们之后许多个十年八年的和谐岂不是需要又一场战争或比战争更具摧毁力的其他事件来成全?井宇和裘洛只有在大地震把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破坏之后,才能焕发出个体生命的活力。但是,他们救助罹难者的行为本身就是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所以地震结束后,他们必须得回到之前的社会结构中,直到下一次的偶然事件的出现将其拯救。如此往复循环,就进入了偶然性事件所带来的叙事怪圈——每当矛盾发生,就需要安排一个偶然性事件来缓解或解决矛盾;而当偶然事件的有效期一过,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此时又必须出现新的偶然事件来解决新矛盾,如此往复循环。历史的改变虽然关键在于偶然性,但偶然性出现的次数多了,就不再是偶然了,其改变历史的能力也随之下降直至消失。所以,矛盾的解决和大圆满的呼唤亟待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可一旦偶然性事件在小说中作为解决矛盾的道具频繁出现,不但其解决问题的效力下降或消失,而且也与现实的叙事逻辑相违。
四、结语
比较两篇小说:白流苏和范柳原都是无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却被更无法掌控的大命运成全了;裘洛和井宇各自以为自己是最先逃离对方的人,却不知彼此之间早已形同陌路,这种逃离又在一场大地震中出现了相遇的契机。作者或许想表达的是命运虽无法把控,却冥冥中早已有了安排,大命运和小命运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关系。大命运借偶然事件铺排人物的一生,个人则通过偶发的重大事件与历史接轨,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宏大的历史与微小的个体通过偶然事件联结到了一起。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