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并不割裂
吴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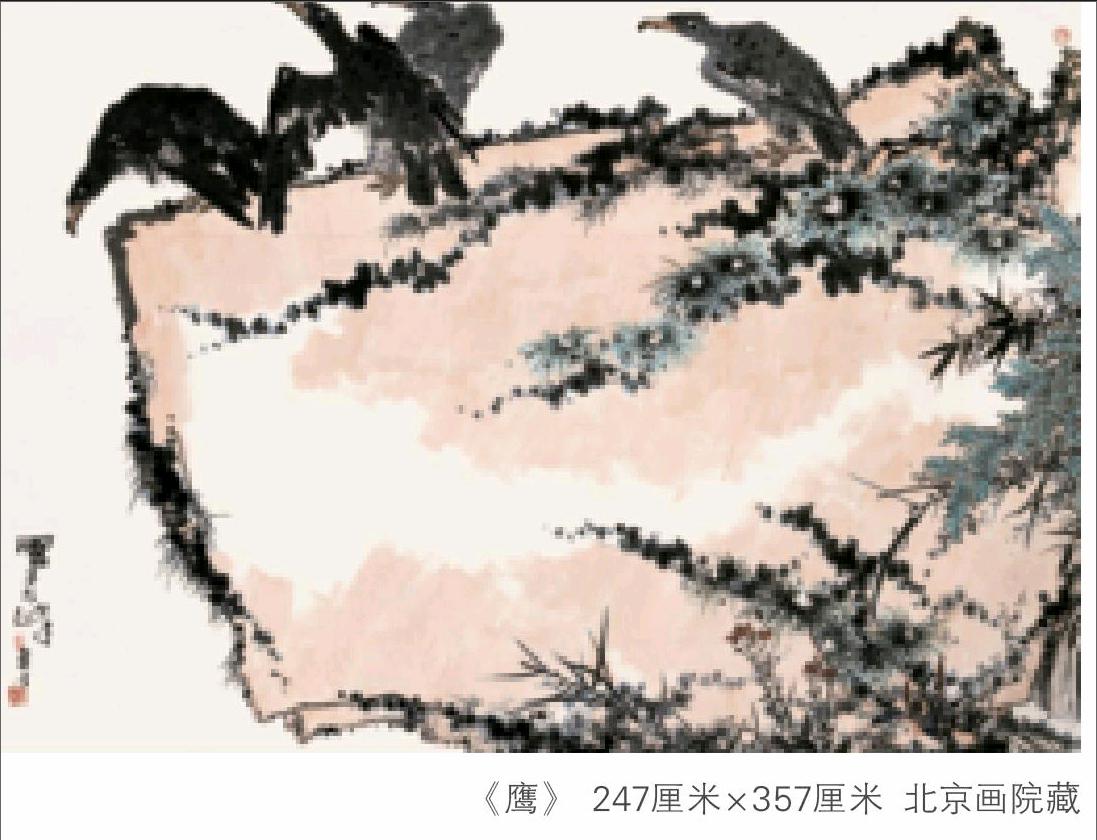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很多改变。而20世纪的艺术家,除了画好自己的画,还要面对各种新问题的出现,首先就要面对画为谁服务的问题。古人的书画创作是属于中国文人的,其意并不在于解决与社会、群体有普遍关系的强烈诉求。而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艺术家已经介于中国文人的理念和现代知识分子责任转化之间的关系,这让他们既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人情怀,希望自我愉悦,又有对视觉效果等其他方面的追求。
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化的过程,如北京中山公园、上海豫园等过去的皇家园林、私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公共空间。对于艺术品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展示空间,一种是公共交流空间,另一种是真正的美术馆。例如陈师曾、张大千、黄宾虹等艺术家都曾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水榭举办个人展览,过去三五好友间欣赏手卷、册页的私密性交流演变成为面对公众的开放性展示。
当整个社会对艺术品的存在方式要求不同了,空间的变化必须要求艺术家改变以往的创作思维。基于这样的变化,所有的中国画家都希望改变过去中国画不适应大空间展示的特点。笔精墨妙的中国画已经不适于案头欣赏,尤其与西方油画在一起展示的时候,国画表现出来的视觉张力明显不足。
那么,中国画如何在展厅中被看到,就成了当时很多画家急需解决的问题。经常有人用“霸悍”来形容潘天寿的笔墨,其实,对于空间的营造更能凸显其霸悍的视野。李可染善于用造境的方法营造空间,一定给观者制造一个空间逻辑,在一层一层地渲染中建立一个空间体系,又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种纵深关系,视觉上充满体量感和丰富性。而潘天寿与李可染的构图逻辑不同。为了让挂起来的画充满不弱西画的能量,潘天寿一直在平面系统里面寻找那种霸悍的张力。他在平面中并不讲求透视关系,往往在一张纸上做一个撑满画面的角,让人感觉整个空间都在膨胀,而画面中其他内容的每一根线条也完全是向四周张开的,从而占满整张纸的空间。潘天寿还会将画面中的重要内容如鹰、青蛙、猫等安排在画面的最上端,但由于整个画面的张力,视觉上并不会感觉有失重感和压抑感。
我们欣赏潘天寿的作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模拟一个300平方米的会议室,将潘天寿的大幅作品置于其中,你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他作品中的主体都不会被遮挡。如果很多人站在一张作品前合影,很多画家的作品画面主体会从照片中消失,而潘天寿的作品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潘天寿在教学中也注意让学生在平面中突出构图的能量。据张立辰先生回忆,潘先生上课时要求学生用最简单的方式分割空间,而他所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画兰草,他认为以这种方式划分的空间变化最为丰富。如果潘天寿有意完成中国画在空间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的诉求,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简化作品的形象,将构图更为清晰、明朗化,将笔墨更为霸悍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所谓笔墨的霸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笔墨完全是服务于这种结构关系。我们可以拿同样曾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李苦禅先生对比,看李苦禅的画,可以很近地感受每一笔笔墨单纯的能量,而潘天寿的笔墨能量是为结构服务的态度则更明显。当然,李苦禅也对空间感有追求,但那是一种更含蓄的能量,而潘天寿则更富有张力。
潘天寿霸悍的视野还表现在他的指墨画创作中。所謂的霸悍一定要有刚强的“涩”的感觉,而一味用笔去表现,到达一定程度后会变得熟且滑,指墨线条恰恰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笔与人心的距离更远一些,以指掌作画更贴近人的控制范围,线条也更生动、更富有心性,很多时候胜于用笔完成的效果。正是这样的现代意识,使潘天寿能够用传统方式在传统意识的延伸中达到现代的意愿。
对于潘天寿的研究应该放在20世纪国际艺术整体发展的逻辑中去看。因为如果仅仅是在同时代的比较中去看待一个艺术家,通常容易忽略其艺术成就;但如果将潘天寿放在一个国际艺术体系中去比照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确实做到了以中国方式与西方艺术拉开距离,所以他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如果从教学方面讲,当年杭州国立艺专明显区别于其他美术院校的一点是,对于中国画本体的传统的保留还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是潘天寿这样的大师留住了中国画的根。
中国艺术在上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所谓危机,也不过是其自省与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而潘天寿这一代人,以其自身的实践回应着中国艺术在历史中一时的失语与低落,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使这门艺术得以新的演进而不是真的断裂。
(注:作者系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