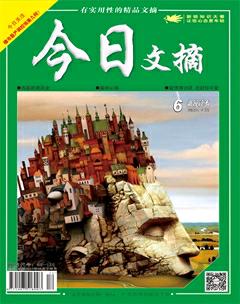人类为什么爱说脏话?
胡晴
《纽约书评》一篇文章说,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脏话的专着,阐述脏话的益处、历史,搜集五花八门的脏话。美国认知科学家本杰明·贝尔根刚写了一本《搞什么!》(What the F),印第安纳大学英语系的迈克尔·亚当斯写了本《赞美脏话》。
脏话也是一门学问。一个叫奇普·洛的美国人主张严肃对待脏话。他甚至创办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脏话,欢迎脏话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
科学家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杰认为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痛剂。他举例说,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虽然连亲属的名字都忘记了,词汇量也大幅度减少,但说起污言秽语毫不费劲儿。
一些神经科学家发现,尽管脏话也是一种语言,但是人类加工脏话并不在“高级”的大脑皮层,而是在“低级”的功能区,当人们说脏话时,大脑中主管情绪活动的部分即额叶系统会被激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们开车遭遇“马路杀手”时,说的脏话往往要比平时多得多——这无疑是最简单的舒缓情绪的办法。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一句恰到好处的“他妈的”还真能胜过万语千言。
2011年,英国基尔大学的理查德德德·斯蒂芬斯教授进行了一个实验:两组实验对象把手放进冰水里,一组可以大声咒骂,另一组则不能出声。然后两组人员交换位置,体验对方的处境,再分别测试他们忍耐的时长。试验结果表明,大声咒骂时,实验对象的心率加快,忍受冰水的时间大多能坚持60秒到90秒;而“沉默”组的成员则很少能坚持到60秒。
2006年,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在越南河内参加一场国际会议。头一天,为了打破冷场,越南和西方学者轮流比赛讲笑话。越南学者因为担心会惹是生非,坚持讲正经笑话。所以大家仍彬彬有礼。最后,第三位西方选手,即卡罗尔,讲了一个关于公鸡的下流笑话,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后来会议开得很成功。
脏话有打破隔阂的作用,在军队、体力劳动者、爵士乐团等群体中,脏话词语使用频率非常高。
迈克尔·亚当斯提出,脏话之所以能够提升人际关系,是因为它们以信任为前提,相信我们的交谈对象跟自己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不会讨厌我们使用犯忌的词。如果一种关系通过了脏话测试,他们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脏话简史》作者梅丽莎·莫尔认为:“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日本棒球明星铃木一郎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最喜欢在美国打球的一点是能骂人,他学会了用英语和西班牙語骂人。他说:“西方人的语言使我能够说我本来说不了的话。”
不过,即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脏话正名,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脏话仍然被视为禁忌。韦津利发现,《牛津英文词典》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把“fuck”这个词收录进去,兰登书屋直到1987年才收录它。
一位美国学者说:“我们要赞扬和感激那些继续审查脏话的人:法庭、一本正经的语文老师、出版物、不许孩子说脏话的父母。因为当对脏话最后的禁止消失时,脏话也将失去其力量。”到那时当你不小心磕到哪儿时,说一句“我擦”也不能让你觉得好受点了。■
(孙先宇荐自《华声》)
责编: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