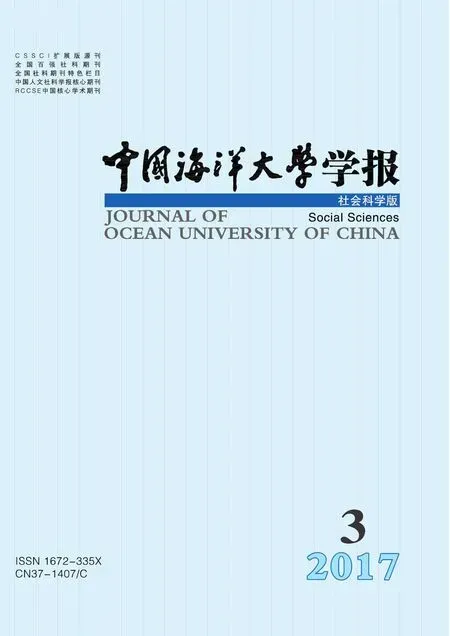贪污罪与盗窃罪法律处遇差异的社会学反思
刘用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贪污罪与盗窃罪法律处遇差异的社会学反思
刘用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贪污罪和盗窃罪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法律处遇差别的普遍化存在,实际上带来了刑罚配置的公平性问题。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当代法治国家,贪污罪的惩治一直重于盗窃罪,主要在于对前者身份的特殊要求。近年来的立法趋势显示,贪污罪轻刑化正在成为一种反腐治理新手段。从社会学层面考察,这一现状形成有社会、民意、政治、政策和立法五方面原因。应当适当修正这种奖励性的过于功利性的反腐措施,以回归贪污罪与盗窃罪之间犯罪与刑罚对应之本身的公平性。
贪污罪;盗窃罪;法律处遇;社会学;公平
贪污罪与盗窃罪本出一源,都是对将他人(包括国家)财产占有己有的行为处置,区别在于主体和财产的归属,从国家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视角出发,这本不存在因此而致的处罚后果之别,其主体的区别仅决定了罪名的相异。主体职务之特殊要求赋予贪污犯罪更严厉的惩罚,这应是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核心区别,然而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精神,同为占有他人财物只因主体的不同,在起刑点、法定刑及处罚上都存在贪污罪轻于盗窃罪的情形,职务本应赋予的特殊要求却流于形式。在大力反腐背景下,贪污贿赂犯罪的轻刑化趋势却有增无减,这一现象值得从制度设计上加以反思,以更好地实现刑罚配置和运用之公平性,同时,也是对腐败犯罪治理的另一思路。本文拟就此作番探讨。
一、贪污罪与盗窃罪的立法和司法处遇差异
(一)立法差异

客体立案标准法定刑从宽情节贪污罪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其中数额较大为3万至20万元,其他较重情节为1万至3万数额下的特定情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3-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盗窃罪私人财产所有权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其中数额较大为1000至3000元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3-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被害人谅解的;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由上表看出,同为侵犯财产权行为的贪污罪和盗窃罪在“出生”上就存在差异,盗窃罪追诉的起刑点大大低于贪污罪达十倍之多,侵犯私有财产和侵犯公共财产之“命运”在是否有罪上存在天壤之别。就两法定刑而言,除贪污罪保留死刑外,尽管同为相同的三档,但由于数额标准的不同,三档法定刑在具体运用上实质并不相同。此外,贪污罪死刑的适用十分罕见,就实践来看主要是保留其威慑功能。因此,基本上可以判断,贪污罪与盗窃罪命运的差异,其直接原因在于立案标准、数额标准本身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从源头上就显示了两者在刑罚配置上的巨大不公。
(二)司法差异

2004年—2014年全国贪污贿赂案件数据简表*根据2004年至2014年中国法律年鉴数据统计,年鉴所认定的贪污贿赂案件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集体私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他六种类型。
上表中可以发现,贪污罪人数占整个贪污贿赂犯罪人数四成以上,因而实际上也拥有五成以上接近六成的不批捕率,以及和其他犯罪相比相当高的不起诉率。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一旦被采取,将来极可能被判处缓刑或较轻刑罚,因而,也就意味着近六成的不批捕率将同样有近六成贪污罪被告人不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考虑一成左右的不起诉率,贪污罪的有期徒刑率也仅有三成,贪污罪刑罚结果的大幅轻缓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和趋势。然而,比较与之相近的盗窃罪,其司法处遇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2005年—2015年为时间段,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每年随机抽取10个盗窃罪案例,累积抽取110个案例为基数分析显示,共有被告人156人,逮捕108人,逮捕率为69.23%。取保候审37人(包括逮捕后取保),取保率为 23.17%,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90人,有期徒刑率为57.69%,判处拘役为9人,将有期徒刑和拘役合并计算,实刑比率为63%,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为32人,缓刑率为21%,另外,单处罚金为12人。不难发现,盗窃罪57.69%的有期徒刑判处率与贪污罪三成左右的有期徒刑率,盗窃罪21%的缓刑率与贪污罪六成左右的缓刑率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考虑贪污罪不起诉率甚高,两者在司法处遇上的差异将进一步拉大。
上述小样本统计可能不足以完全说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进一步从微观上验证这一推定,以2013年至2015年为时间段,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抽取贪污罪和盗窃罪各15个案例,所获结果也大致如是。即15个贪污罪案例显示,被告人26人,逮捕率为54%,取保候审率为46%,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9人,判处有期徒刑率为34.6%,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14人,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率为 53.8%,免于刑事处罚人数为2人,免于刑事处罚率为7.6%。15个盗窃罪案例显示,被告人24人,逮捕率为50%,取保候审率为50%,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数为17人,判处有期徒刑率为70.8%,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的人数为5人,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率为20.8%,判处拘役的人数为2人,没有免于刑事处罚案件。比较可见,盗窃罪有期徒刑率竟然多出贪污罪一半,七成以上判处有期徒刑,贪污罪还有7.6%的免于刑事处罚率,而盗窃罪没有免于刑事处罚。同时,在其他学者同期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抽样统计的研究中,盗窃罪的有期徒刑率也在六成以上,*据学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浙江省宁波市下辖11个县区2014年上半年盗窃罪判决情况抽样统计显示,抽取的539份盗窃案件判决书判处的630名盗窃罪犯罪人中,免于刑事处罚共计2人,占被告人总数0.3%;单处罚金刑共计30人,占比4.8%;判处拘役共计196人,占比31.1%;判处有期徒刑共计402人,占比63.8% 。参见林思婷、武敏.盗窃罪量刑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2014年539例判决为例[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4(9):15-16.而贪污罪量刑实刑率也基本与盗窃罪产生巨大反差。*据学者对江西抚州市2010年至2013年职务犯罪案件判决情况的统计,2010年至2013年,抚州市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审判环节的共354件共378人,其中有264人被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刑和免刑率占比为69.84%。此外,学者崔胜实局地实证调查的结果是,2012年某市两级检察院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11人,34人免予刑事处罚,占比30.6%; 44人判处缓刑,占比39.6% ;33人判处实刑,占比29.8%。 2013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5人,判决130人,其中60人免予刑事处罚,占比44.4%;1人单处罚金,占比0.7%;45人判处缓刑,占比33.3%;24人判处实刑,占比17.8%。参见季玉.职务犯罪轻刑化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17.崔胜实.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对反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J].中国检察官,2014(12):56.
此外,实务部门统计或调研数据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1]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在安徽省政法委开展的查办职务犯罪司法不公专项行动中,经过对全省8个地市的调研,选取了113件职务犯罪案件判决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判处实刑的44人,占全部案件总人数的38. 9%,判处缓刑的22人,判处免于刑事处罚的47人,这两项加起来合计69人,占全部案件总人数的61. 1%,而仅判决免于刑事处罚这一项即占全部案件总人数的41. 6%。[2]这说明,上述数据抽样和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当然,这种极不寻常的差异所导致的刑罚不公平问题并非没有引起高层注意,对此,司法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二、政府对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境遇“特殊化”的应对及其评价
面对贪污贿赂犯罪惩治方面的日益失衡,司法高层其实是早已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些遏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就已指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2011年11月,最高检也颁布《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对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的法律监督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同级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目的也是强化不当量刑的监督和制约。
在此基础上,2012年8月,“两高”又共同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问题做出了新规定。司法解释明确九类情形下一般不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即:(一)不如实供述罪行的;(二)不予退缴赃款赃物或者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三)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四)犯有数个职务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五)曾因职务违纪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分的;(六)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等特定款物的;(七)受贿犯罪中具有索贿情节的;(八)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情节或者滥用职权情节恶劣的;(九)其他不应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为强化执行领域的不正之风,避免在执行环节对刑罚打不当折扣,201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发《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减刑、假释裁定书或者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后十日以内,逐案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对原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减刑、假释裁定书或者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后十日以内,逐案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此外,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还对贪污、受贿罪案件设定了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制度。
总体来看,“两高”近几年来实施的上述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贿赂犯罪不当轻刑化的现象,提升了刑罚的本身的正义价值,取得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但在肯定其功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即这些制度的基本导向仍然被一些可能存在问题的理念所制约着,因而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实现中的公平性问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治吏宽于治民;其二,预防正义的限度;其三,和谐观念运用于惩治职务犯罪。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盗窃罪与贪污罪在1997年刑法之前都属于财产犯罪,至今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国家都将贪污罪作为侵占性的财产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将其和贿赂犯罪一起单列后,仍然未改变其财产罪属性。因此,同为财产犯罪,对贪污罪的惩治在起刑点、量刑情节之规定上,乃至实践中的司法结果,却出现了一种治吏轻于治民的局面,这一理念是否适合更好的惩治职务犯罪,或曰有力的反腐败,是值得商榷的。起码在民间和官方内部不同对象之间造成的刑罚适用不公平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
其二,对贪污贿赂罪在能够认罪退赃基础上,以及一些其他情节前提下,处以更轻的刑罚,实质上体现了通过预防正义来减少腐败的理念。官员和普通人在触犯财产罪金额相近及其他相同条件下,对官员更轻的量刑,一般而言,官员将失去再犯的机会,因而比普通人的预防功能有更好的发挥。但事实上,正如前述,官员的职务犯罪很难有再犯,一旦处以有期徒刑,将失去公职身份,从而不可能再有职务犯罪。从这一点上讲,其预防功能本身不可与盗窃罪相比。因此,基于官员再犯可能性、自我改造视角为其获得轻于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是难有说服力的。
第三,和谐社会目标提出以来,近十年中,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毛细血管化的结合式运用,在司法领域,也曾经提出司法和谐或和谐司法,这种政策因子对刑事司法特别是职务犯罪处理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在同为官方机构人员处理“自己人”问题上,并不会只对“外人”讲究和谐,而对“内人”格外严格,反而是在和谐理念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下,更容易潜在的对“自己人”落实更多的和谐理念,从而形成轻判的风气和做法。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气和趋势。但是,和谐社会虽然不能外于官员犯罪,其本身的着力点并非主要在于官员内部而在于社会、民间,因此,至少对官员犯罪的所谓和谐因素应当严于民间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一种特权的展现。
综上三个方面,其还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贪污贿赂罪特别是贪污罪的财产属性重于职务廉洁属性,而后者正是1997年刑法将贪污罪调整单章的法理原因。从立法目的上出发,应该更加注重公务人员职务廉洁性的维护,减弱其原属的财产罪属性,但就其具体制度而言,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九)以来,更加突出的恰恰是其财产属性而不是后者。特别是在刑罚运用上廉洁性几乎未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司法解释中特别注重退赃这一情节,明确规定不予退缴赃款赃物的,一般不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但全部退缴赃款赃物,可以适用。其中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的,放宽到一审宣判前退还也可以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另外,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不具有本意见第二条所列情形,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犯罪,一审宣判前已将公款归还,依法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在案发前已归还,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由上可知,现行对于贪污罪的惩治程度某种意义上就是看国家财产是否遭受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弥补直接决定了贪污贿赂罪的处理结果,而即使在盗窃罪中退赃也并非都有如此宽厚的待遇。如此一来,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之被破坏或侵犯所应得的刑罚会因为退赃而大大被消解,甚至荡然无存。近二十年来通过强化职务廉洁性客体来打击职务犯罪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反则制造了制度上突出廉洁性客体,实践上突出财产性客体的矛盾。当然,这也种局面的出现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
三、贪污罪与盗窃罪法律境遇差异的社会原因
(一)观念原因
任何刑罚都是相对的公正,包括对本类和他类犯罪及其相互之间。首先,在盗窃罪和贪污罪各自发展史上,都会经历一个对其刑罚配置认识的深化进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乃至不同的决策者都可能是各自刑罚因时而异、因事不同的原因。其次,在两种犯罪比较层面,同样对于两者刑罚配置正当性、合理性的认知也不存在真理意义上的唯一性,而更多的是可变性。譬如,犯罪之刑罚配置之直接根据是报应和预防,刑罚的公平性就取决于此两者的比例是否衡平得当,而这一认识仍然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之环境中来认知,抽象的脱离外在条件的纯粹“理性正义”很难实现,也可以说并不存在。其三,即使立法能够解决不同罪名之间的刑罚公平,在个案中,司法者也难以将绝对的公平变为现实,这还离不开带有主观认识特性的司法者,司法者将普遍的法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就是一种个别的过程。以上三者,乃是把犯罪及其惩罚放在社会系统性视野下的认识,因为法律制度本身是用来调整社会现象的,司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实现社会自我调整的手段而已。
社会的宽容度是现代社会文明性的重要指征,但宽容的运用和具体展现不仅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在阶层化社会的窠臼阴影之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施以各种宽容,司法者对犯罪人给予宽容,都存在一个由己及远的规律,或者说在心理层面,会存在自己和外人、圈内和圈外之别。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对盗窃罪是属于圈外人,官员(立法者也把自己作为官员)阶层之外者,因而对同属本阶层内部之人的法其宽容度要大于外人,特别是在司法中,会更能设身处地的想象其处境甚至感同身受,因而其内心宽容的区别是潜在的也是客观的。司法者对贪污罪之官员的特别宽容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把贪污罪作为社会内部特别是统治者内部的冲突,而把盗窃罪所代表的社会冲突认定为外部的、真正社会中的冲突,甚至是一种结构性冲突,更能够导致社会功能的紊乱,因而其处罚中的宽容度很难超越前者。
(二)民意原因
一般说来,处罚贪污的民意远大于盗窃,但这是总体民意,也是宏观认识。一旦案件涉及到自身财产,可能民众会更关心盗窃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间对盗窃感知度敏感,个人意愿强烈,对贪污相对距离较远,敏感度较低。*这里的意思不是否认民众不痛恨贪污且不愿意重处贪污,而是说,在保障民众自身财产安全前提下,民众愿意这样做,但和自家财产安全相比,民众更关心自身,更愿意从重处罚盗窃行为。这句话隐含这着一个结局,就是盗窃罪必须严加惩治,而贪污罪是否严惩并不直接关涉个人生活。盗窃行为一般是在社会生活的群体中发生的行为,容易引起“众怒”,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否则,大家对统治秩序的不良感受就会成倍增加,自身生活幸福指数下降不说,进而会影响执政者执政的稳固性,“替民伸冤”的惩治盗窃行为是历代统治者所不遗余力的,因为这实质上不是“为民除害”,而是为自己政权打口碑。因此重刑严罚一般人人称快,而不会考虑其实际危害乃至配刑的公正性问题。相对贪污罪而言,其占有的是国家财产,危害的也是统治者内部秩序,虽然其利用公共财富穷奢极欲的行为也令人不满,但这需要有极强“正义感”的群众来不断“抗议”,显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力度上其都会小于盗窃罪。因而,统治者进而司法者惩治盗窃罪所带来的收益——社会声誉及其他要远大于贪污罪。虽然,在当前和平时期,人们对贪污罪惩治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严厉反腐也是民意,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在经济困难状态下,民众任然首先关注的是自身财产和生活秩序的安宁。即使在当下的社会,也仍然难说民众关注反腐超过对自家财产安全的关注,只不过是反腐声浪过高并没有放在这一前提下比较罢了。因此,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决策者更能忍受哪怕一定程度上的不公正,即通过较重的盗窃罪惩治换来比较轻的贪污罪惩治更多的民意,从而也就是更能安抚民意的策略。
(三)政治原因
对于盗窃罪与贪污罪的不同境遇,公私财产保护的区别,社会阶层固化及改革开放以来一定程度上对腐败的容忍也是其政治原因。与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体制不同,公有财产的严格保护乃至公共经济体的特殊利益在我国一直是优越于私主体的。这一方面,可见我们宪法内容中对私有财产、私营经济规定的不断变更,至今,这种差别在制度层面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譬如1997刑法对盗窃罪死刑的设定中,就规定了金融机构这一特殊主体的侵犯可以判处死刑,而其时乃至今日,金融机构则主要是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许霆案中,坚决入罪而不能适用外国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也体现了国家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3]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对贪污罪的打击力度一定层面上要大于盗窃,以致在废除盗窃死刑后贪污罪仍然保留死刑,尽管实践中贪污罪的死刑(立即执行)已经仅成为一种威慑了。*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贿赂犯罪中适用死刑的非常少。省部级高官中仅有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刑法修正案(九)又对贪污罪设定了终身监禁,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但是,一方面我们不可从表面上或局部出发就认为贪污罪的境遇比盗窃罪更坏。因为,毕竟数额巨大的犯罪在两罪中占比都是极少的,我们不能从这些极端的情形中来比较两者。另一方面,两罪中常见的是普通数额的犯罪,实践上来看,受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对盗窃罪的惩治数量要远多于贪污罪,刑罚也更重,而这其实正体现出财产权地位不平等政治制度下的一种矛盾现象。对于前者来说,公有财产的保护在制度上、地位上高于私有财产,既体现在对盗窃罪的惩罚上,例如此前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可以判处死刑,也体现在对贪污罪的治理上,如保留死刑,并设立禁止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对于后者而言,公民盗窃公有财产和公职人员盗窃公有财产的一重一轻则又显示出对公有财产保护的矛盾态度,贪污罪并没有因公有财产被盗窃而处理更重,普通盗窃罪也没有因为不是盗窃公有财产而处罚更轻。解释这种矛盾的合理原因就是阶层固化带来的对本阶层的某种“偏袒”。以致,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三十余年中,从来都没有出现对盗窃罪的容忍,比如体现在盗窃罪的起刑点较低且调整较慢,*改革开放后盗窃罪立案标准调整了三次。1991年盗窃案的立案标准为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提到300元至500元;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则提高到600元。1998年3月,有关司法解释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规定为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5000元至2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万元至10万元为起点。2013年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为1000元至3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300000元至500000元以上。贪污罪立案标准调整了四次。分别从1986年1000元以上,1988年2000元以上,1997年5000元以上,2016年10000元以上。而在今日高压反腐之前,实质上却对腐败行为存在较高的容忍度。换句话说,当前进入贪腐犯罪的高发时期是有其基础和原因的。在这种特权理念制约下,即使出现了某些“倒霉者”、“不会办事者”,对其处罚也是能轻则轻的。
(四)政策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累计三次大规模“严打”,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严打”这这一政策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基本刑事政策,严打的对象就包括盗窃罪。当然如果从我国长期以来对社会秩序严格控制的视角来看,“严打”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古代刑罚世轻世重,就意味着在社会治安混乱时期,要运用异于、重于平时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秩序。这种治理手段一直被后世所延续。新中国建立于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之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新的经验,这种运动式政策也被用在惩治反革命及其他严重犯罪上。重刑治世和运动式推进二者的结合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严打”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传统氛围下的产物,盗窃罪被严厉惩治自然首当其冲。由于贪污罪并非直接破坏公共的社会秩序安宁,因而在“严打”的二十年间,一直未能“享受”运动式的打击,因此,直到上世纪末刑法修订前,并没有被施以重刑遏制。而其实,即使新世纪以来,贪污罪的惩治有所严厉,立法上的改变也并没有很好传导到司法层面,司法实践中,对待盗窃罪的“严打”思想仍潜存暗在,而对贪污罪主体的宽缓用刑则始终存在,甚至在赃款退还基础上一度成为橡皮筋一样的刑罚。
另外,作为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我国在立法和司法政策上也有着不同的待遇,贪污罪作为非暴力犯罪,处刑较轻被司法人员所认可,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正义的代名词。这是由长期以来对暴力犯罪处罚重于非暴力犯罪的政策惯性所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政策和认识的错误是明显的,非暴力犯罪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得到轻缓的处理。在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贪污罪惩治过度轻缓化的局面就正在被改观。
(五)立法不科学原因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在设置上的偏差定位,也会导致运行上的偏差。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在制刑层面,盗窃罪的刑罚配置就重于盗窃罪,譬如起刑点不同,退赃后从宽处罚的情节规定也不同,尽管我们意识到这种区别可能是有违制刑之公平的,但司法者只是制度的运用者,其遵循的结果自然就会带来配刑、量刑的差异。因此,两者差异最直接的原因,还应该是制度设置。但看待制度的形成,又必须放在政治、社会、政策等诸因素中考虑,才能认识其为何如此,故实质上,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错综复杂,对其全面分析判断才能更加客观的认知,从而做出更为合情合理的完善补救之道。如前所述,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仅仅是一时犯的“错误”,因此,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才是中肯的。同时,中国当下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逐步追求更趋合理的刑罚结构和类案、个案之正义,还必须有一种不自我满足的眼光,才能够以更小的代价换取制度的完善与进步。
四、如何实现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公平”
(一)消除财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真正确立同等保护理念
财产权不分所有者性质的平等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基本法理为诸多法治国家所遵循,这是政治平等权在财产领域的必然延伸,是现代平等权的基本要求。西方国家所主张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倒未必值得效仿,但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的同等保护待遇,或者努力缩小其间的差别倒是值得有所为的。就我国宪法发展的历程来看,已经具备了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基本法基础,这为盗窃罪与贪污罪同境遇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石。1949年《共同纲领》即具有了公私财产同等保护的规定,但1978年、1982年宪法实质上有所倒退,1988年宪法修正案开始加以纠正,1999年、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公私财产受到同等保护。特别是2004年国家对公私财产的保护都运用了同样的“不受侵犯”一词,并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从制度表述和定位上基本完成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使命。特别是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施行,在再次重申公私财产不得侵犯之外,进一步使上述宪法规定从宏观层面走向了具体制度保障。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上述宪法要求在贪污罪与盗窃罪处遇问题上实质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反而出现了一种好像更加偏重于私有财产之保护的假象。比如在起刑数额问题上以侵犯私人财产权为主的盗窃罪要比贪污罪低十倍,退赃后贪污罪的刑罚显低于盗窃,这意味着国家在私有财产保护问题上使用的规制力度要大于对国家财产的力度,但实质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并不能藉此得出这一结论。一般而言,中国民间长期以来是缺乏财富的,小民百姓的财产十分有限,设定高的起刑点会脱离现实,完全不能起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之目的,另一方面,基于观念、民意、制度等原因,国家对贪污罪的处罚因为其主体的“内部性”而给予了更宽缓的规定,这种对处遇上的倾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统社会中的身份性、特权性因素,亏国家不亏个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体制内的“公约“性。因此,这两种犯罪主体之间的“差别待遇”并不能代表国家对整个公私财产保护的态度和做法。而只有在公共财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安全保障、市场进入和退出等方面和私人财产的全方位平等才是真正的同等保护。
因为,冲淡亏国家不亏个人的这种身份社会的残余观念只有在在市场经济完全成熟起来以后才能逐步被荡涤,而成熟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主体面前平等思想也会进一步遏制从立法到司法环节这种观念的滋生土壤。进一步说,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平等是改变贪污罪处遇被特殊“优待”的大环境,只有这种大气候得到改变,才能在微观领域实现在贪污罪与盗窃罪在侵犯财产面前的同等惩罚。一句话,改变当前贪污罪处遇中的特殊“优待”虽然离不开相关制度和措施的调整,但其真正命运在于统一财产权保护理念,实现同等保护。
(二)以大社会秩序观重新审视贪污行为的规制
在黑格尔明确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区分开来之前的古希腊,市民社会理论的萌芽——公民社会的概念既已被亚里士多德和智者学派所倡导,此时的市民社会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4]启蒙运动各资产阶级学者进一步将同样古老的社会契约思想融合运用于市民社会理论中,从而描绘出诸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制衡的理想政治图景,正是这一理论创举将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推向到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在欧洲诞生了崭新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以致今天,这一理论仍然是西方社会乃至法治建设极为推崇的思想基础。或曰之,现代政治进步和法治社会,没有市民社会与国家两分理论,就不会诞生和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创建的基础,但实际上由于把市民社会起源本身看做“神秘和幻想的”[5]因而是颠倒的,其真正目的和结果恰是国家出发来决定前者,对此,马克思才特别对这种唯心主义史观作出了批评。马克思指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6](P247)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P247)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政治规律的把握,大大拓宽了人类社会自我治理和发展的思路,从而为设计现代的权力制衡和政治监督奠定了基础,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就在市民社会对国家有序的监督与制约上。
但是,两分式的政治观并非没有缺陷,两分式的社会治理认识带来了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异的治理手段,运用于市民社会的不一定适合于政府本身,适合于政府本身的未必能用在市民社会中。进一步说,两分式的认识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两种秩序观,即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秩序和政治国家秩序。面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法治和政策也进一步获得了法理上的正当性。于是,在现代人心目中,这种本来归于一体,天然并不分割的人类社会被逐渐固化的两分式认识所习惯化,人们对两者不同的治理方式也渐趋麻痹。这种治理模式如果能够采取对两者各自得体的措施并兼顾两者之间相对的公平当然最为理想,但由于国情和传统的区别,一旦两种分离式的治理难以兼顾两者之间的公平性,甚至形成各自不得体的现状就将完全走向这一理论设计的反面,尤其是在固有传统中国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其弊病就更为明显。
中国曾经是长期处于国家淹没社会的社会,近百年来,才逐渐实现了社会的诞生和发展。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出现,国家领域的治理以其难以根除的特权而优越于社会的现象,长期的市民社会的弱小也很难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甚至默认其合理性。事实上,贪污罪与盗窃罪的不同命运正是这种弊端在刑法领域的展现之一。在这种模式下,往往不是社会决定国家、政府,而是不自觉的走向了轻社会重国家的理论窠臼,从而也就在事实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前提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既要看到二者的区别从而相异而治,又要注意二者的共性,从而避免带来公平性的危险。也即在坚持两者分离基础上,还需要一种大社会秩序观,毕竟无论是政治国家内的犯罪,还是市民社会中的犯罪,都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背离,其共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衡量贪污罪和盗窃罪作为财产犯罪之间的公平衔接,在酿造合理的刑罚结构的同时也更好的维护社会安宁秩序。
(三)突出贪污罪职务廉洁性客体,设定重于盗窃罪的法定刑,扩大禁止减刑、假释的适用范围
1997年刑法修订后,贪污罪所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已经从理论共识变为实际制度,如前所述,将贪污贿赂犯罪单列一章,一则突出对该类犯罪的专门整治,二则从法律上突出对职务廉洁性的严格保障,但事实上,从如前贪污罪与盗窃罪处罚结果的对比来看,刑法对职务廉洁性的保护和被侵犯后的惩罚与修复目标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反而是徒具形式的。例如现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对贪污数额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在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前提下,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贪污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有前述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而盗窃罪在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情形下,具有法定从宽情节、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不是主犯、被害人谅解及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条件,且情节轻微的,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同样,在诈骗罪的处理也是如此。比较来看,贪污罪和盗窃罪一样都重视了财产秩序的维护,而恰恰没有突出贪污罪惩罚中职务廉洁性客体的刑罚体现,或者说这种体现过于微不足道,以致失衡。明代后期曾经出现过监守盗轻于常人盗的特殊便宜规定。*清代薛允升曾言:“古人之法原有至理,天下未有生而为盗者,教养不先,而穷苦无度,迫于不得己,非尽小民之罪也,在上者方引以为愧。为忍尽法相绳,亦网开一而之意也……监临主守俱系在官之人,非官即吏,本非无知愚民可比,乃居然潜行窃盗之事,有何情节可原之有!”(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M].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50.一度曾为史家所诟病。
为此,应当将贪污罪惩治中的职务廉洁性之刑罚存在重新恢复出来,让其这一点上与一般的财产犯罪有所区别,并以此体现对贪污犯罪更重刑罚的正当性理由。也即,在此认识下,重新设定贪污罪法定刑。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将贪污罪的第一档提升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对贪污受贿犯罪在判处死缓情况下设定了可以限制减刑、假释的规定,和其他犯罪相比,这无疑加大了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因此有学者担忧这会造成刑法各罪名之间刑罚的不公平,为什么其他犯罪没有而单独贪污罪限制。这正是中央严厉惩治贪腐行为的有意措施。我们姑且不论这一制度创新是否会在各罪名之间制造不公,贪污罪是否比其他犯罪更需要终身监禁,单假定这一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我们会发现终身监禁制度仅仅打击了“老虎”,而对大量的“苍蝇”,乃至“小妖”们并不适用。由于“大老虎”的有限性这必将大大影响这一制度的实际功效。实际上,对普通贪污犯罪限制减刑、假释可能要比对个别要犯来的更有社会效果,更能为群众所感知,其预防效果更佳。因为,“生活”在百姓身边的小贪小腐相较于巨贪更为百姓所痛恨,反腐的传导力更强。因此,建议将限制减刑、假释制度扩展到普通犯罪中,只有完成一定的间隔以后才可以减刑假释,以体现重于普通犯罪的惩治理念,以便取得更好的惩治效果。
当然,与之相应,也应当调整在贪污罪条款中专门性的规定从宽制度的内容。即使在满足了认罪、退赃、减少损失发生的条件后,也应当严格限制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至少不应该在贪污罪条款中,专门强调这一规定。即使需要适用,也完全可以根据刑法总则裁量运用。而一旦在条款中再次明确,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就是告诉司法者,这一处理在需要时可以放手适用。当然,对于减轻处罚、从轻处罚都应当如此。总体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不适用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而是要建立一种相对重于普通财产犯罪的刑罚结构,在此基础上,运用宽严相济才是合理的。如果,只能说在现在轻于普通财产犯罪的基础上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和体现,那只能是对这一政策精神的误读,助长了一个不具有善和正义性的刑罚体系。
(四)入罪上要降低贪污罪起刑数额
社会危害性或法益的侵犯性价值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在社会财富较为丰富、货币日益贬值的时代,侵犯财产而入罪的数额因而需要合乎时宜的有所提高,这是社会系统论思想决定的罪与非罪区分的重要标志。这种观点也是当前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以及两高司法解释所秉承的,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并非没有缺陷,特别是在和盗窃罪起刑数额不一致的前提下。理论上说,在犯罪比较猖獗的时期,起刑点的调整频率应该慢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这体现了对犯罪处罚的严厉性,但我们在量刑问题可以实行多种宽缓的选择,从而做到法本身的威严性与罚的机宜性之结合,如果过于跟紧经济发展的水平,实质上无异于降低法本身的威严。贪污罪起刑点的从5000元调整为3万元,特定情节下1万元之幅度是明显跟紧社会经济发展的,甚至还有些超前。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元,3万元相当于比一个中国公民全年工作创造的财富更高,试想,这样的数额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这笔财富都不是小数字,也即3万元的起刑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衡量3万元是否恰当不应当以中国的GDP数额为准,也不应当以人均国民收入为准,因为只有人均纯收入才能更贴切的体现财富数额的时代价值。作为对比,2011年,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贪污25000美元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这条新闻轰动了美国,而2009年美国人均收入是61000多美元。[8]而且25000美元被如此吃惊,显然这并非其起刑数额,而且就是按照这一数额也是远低于其人均纯收入的,更别说高于这一标准。
另外,在当前反腐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调高贪腐犯罪的起刑数额也并非最佳策略。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公共财产价值的评估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定的,按照这种逻辑,同样数额的财产社会越发达其价值越低,故经济越成熟,在设定起刑数额上就愈应不断调高,以做到相适应。于是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自然也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但司法解释确立的立案标准为1000元,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立法解释将其调整为一般2000元,1997年《刑法》则再次调升至5000元,目前新的提升后一般为30000元,特殊情形下为10000元。这一规制贪腐犯罪的思路尽管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很有市场,也具有其成立的道理,但它无疑忽视了贪污罪并非纯粹的财产犯罪这一特性,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并不会具有水涨船高的特性,不会因为时代和财富的变化而有质的变更,因此,按照经济富裕程度不断调高贪腐犯罪起刑数额的逻辑并非是无懈可击的,至少在较为频繁的变动上是存在较大问题的。同时,这一逻辑也忽视了当世社会人民的感受,对于五千元而言,还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忽略数额,他相当于城市低保的10倍,相当于内地很多地区人员的2至3个月工资,这也正是一些人大代表提案反对的原因。*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提交了“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建议。李大进认为,贪污受贿的5000元定罪起刑点坚决不能变。郑赫南.既要“零容忍”也要“精准打击”[N].检察日报,2015-03-10:02.对此,还有一个对比,就是盗窃罪虽然也遵循了与时俱进的起刑数额递增的逻辑,但其最高标准3000元仍然没有超过贪污贿赂犯罪起刑数额调整之前的5000元,更何况其最低起刑数额1000元。如果说在当世,人民对数额较大的财产仍然感受为1000元即可达到,那么调整之前贪污罪的 5000元仍然应该属于社会普遍认可的数额较大,将之抬升至30000元,显然明显背离了公众的感受和认知。虽然一个最容易出现的辩护就是实践中5000元贪腐数额被追诉的几乎没有,因而只具有象征意义,故应当调高,但其实实践中没有并非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这种数额的贪腐行为,而是追诉机关没有对其追诉罢了,这是执法和司法本身的问题,并非能够算作立法之错。
(五)司法适用上要突出贪污罪惩治的正义价值
存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贪污罪惩治的预防效果高于盗窃罪,前者几乎不存在再犯的可能,而后者再犯的比例不在少数。这也决定了某种程度上贪污罪在司法环节上的处罚明显轻于盗窃罪的部分原因。20世纪以来,刑罚的预防功能日益被突出,此长彼消的结果导致惩罚犯罪的报应价值日益被弱化,这种局面的形成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正义观。虽然现代社会预防正义作为正义的内涵已日益被人们接受,但传统的正义主要是报应正义或惩罚正义的观念还并没有到可以完全否认的地步,犯罪分子再犯的可能再小,也不能替代或消除刑事责任是产生于已然犯罪行为这一基础。因为无行为则无犯罪、刑罚不惩罚思想的原则仍然为现代刑法奉为圭臬而不可突破。因此,在贪污犯罪中的刑罚评价必然是兼顾两者的,而不宜因为贪污犯罪的可改造性大于盗窃罪,在配刑上更甚至在在量刑上有特别的照顾,从而人为导致两种基本性质类似的犯罪的命运形成较大的反差。这不仅是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刑事责任承担需要注意的问题,更是任何犯罪惩罚应该坚守的原则。而且对于当下的贪污罪和盗窃罪而言,其更应当遵循这一理念,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作为支撑。
首先,贪污罪要惩治的重点是对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破坏和玷污,而这一点,刑罚愈加关注,国家对公职人员职务纪律和职业道德的维持性就愈强。这种刑罚理念是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法治政府所必须坚守的,而如果一个社会对贪腐犯罪惩罚的重心不在于此,而是其占有的财产数额和退赃能力的大小,实则是逐本求末的颠倒了刑法在贪污罪惩治上的使命,其越是重视国家公共财产的“复原”,其就越偏离刑罚的“主题”,就越可能导致在贪腐犯罪的惩治上背离正义价值,尤其是民众所坚守的正义价值。在当今时代,社会对司法机关处理贪腐犯罪普遍较轻的感受正验证了这一点。
其次,在当前职务腐败犯罪十分严重的时期,刑罚注重报应正义对于贪腐犯罪而言更有必要性。对于贪污罪和盗窃罪的刑法评价,社会和体制内人员的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别,体现在体制内认为公职的丧失、政治前途的失败、社会声誉的毁灭等也是官员职务犯罪后需要承担的一种“不利后果”,而这种“不利后果”一般是盗窃犯罪所没有的,故即使对贪污犯罪的惩治比盗窃罪有所轻缓,实质上其严厉性也是不亚于后者的。很明显,不自觉的非刑法评价已经被包含在刑法评价之中了,而民间社会并不这样认为,民众的评价和比较标准则只是量刑的轻重多少。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报应正义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的所遭受的待遇的确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进一步导致了贪污罪惩治中正义价值的削弱。为此,司法者必须跳出贪污罪被告人失去的比盗窃罪更多从而在刑罚上予以平衡的心理,一视同仁的在犯罪问题上进行公正的评价,从而突出其惩罚的正义根据。只有如此,才是刑法的本然使命,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反腐效果,也能够最大程度上在人民心中构建司法的正义与权威。
[1] 徐日丹.最高检:近七成职务犯罪获缓刑免刑 防轻刑化[N].检察日报,2010-11-19.
[2] 周平.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问题调研报告[D].合肥:安徽大学,2012.
[3] 鲁珊:“英国许霆案”的不同之处[EB/OL].http://news.163.com/12/0527/03/82FTGBUE00014AED.html,2012-05-27/2016-09-17.
[4]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4,(5):68.
[5] 易承志.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回溯[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5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吴翔.美国新泽西州三市长在内的44人涉嫌腐败被捕[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j/gj-bm/news/2009/07-24/1788766.shtml,2009-07-24/2016-11-14.
责任编辑:周延云
A Soci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ofCorruption and Theft
Liu Yongjun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0, China)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corruption and theft is quite common in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level, which would lead to a suspicion of penal fairness. Both in ancient China and contemporary states governed by law, the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has been more severe than theft, mainly due to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former identity. In recent years, legislative trends show that light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is becoming a new anti-corruptionmeans, undoubtedly giving rise to the unfairness of penalty between corruption and theft.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has beenshaped by society,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policy and system.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amend this kind of incentive and utilitaria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return to the fair penalty between corruption and theft.
corruption; theft; law treatment; sociology; justice
2016-10-10
201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司法队伍稳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6BFX004)
刘用军(1972- ),男,河南卫辉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制度研究。
D902
A
1672-335X(2017)03-00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