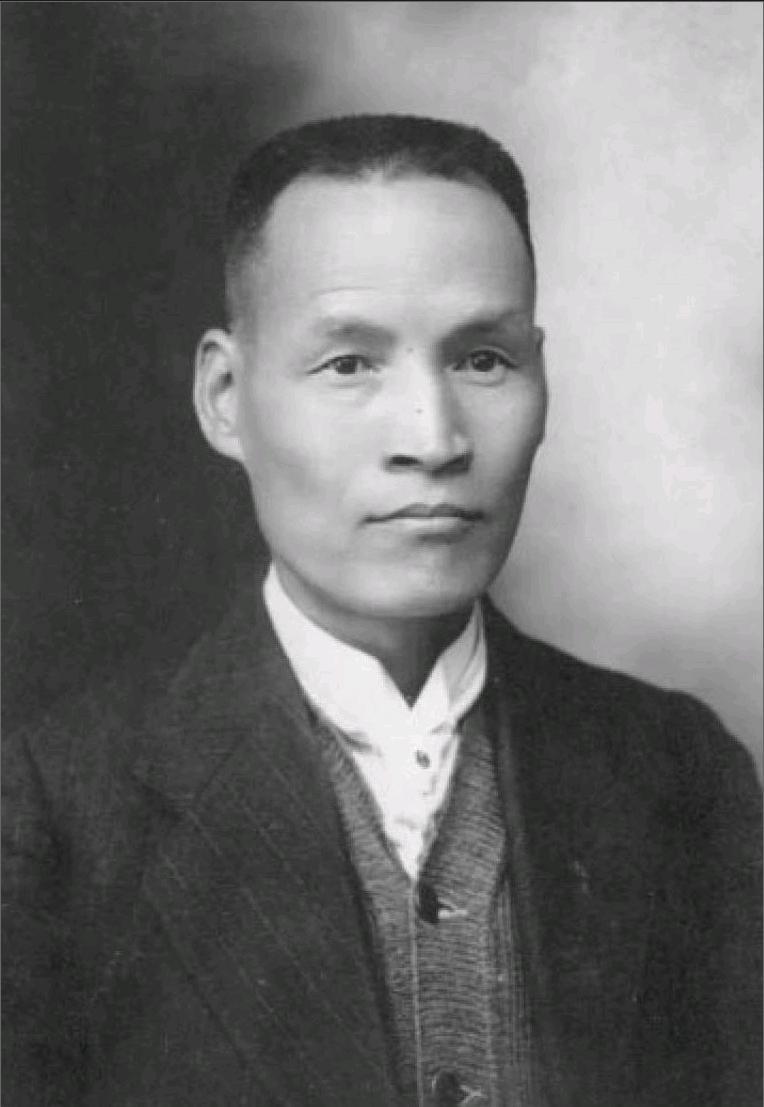近代黄河治理科学化考略
周蓓
谚云“水治则国治”,历朝视黄河治理为重要政事,无不竭尽心力以为之。然至晚清,内乱外患,国力匮乏,治河要政,无复过问。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于河南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北部),改道山东人海,酿成巨灾。明清时期黄河治理一向以“筑堤防,增坝埽”作为攻守之策,在维护水利系统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但终非根治水患之策。
19世纪60年代,黄河改道造成的系列问题引起了西方水利工程师对黄河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水利之兴,肇自上古,“工程学术为世界冠”。近代水利科学和工程技术虽有迅速发展,但目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欧美人士莫不钦佩赞叹,甚至将黄河堤坝与大运河、长城并列为“中国三大杰出的人造工程”。而中国历史上一些治河名臣的治黄理念恰与现代水利理论相接近,这使得近代中西方水利专家关于黄河研究的讨论与对话能够在延续传统的状态下对等进行。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水利专家提出了“河工科学化”的口号,黄河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堤防到全流域管理的重大转变。张含英曾坦言:“中国水利事业虽有悠久之历史,但自科学方法之输入,则可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而以近30年之发展,有显著之进步。”(《张含英治河论著拾遗》,黄河水利出版社,2012年)本文仅就晚清至民国时期黄河治理科学化的几个节点作一初步考略,以求方家指正。
晚清黄河治理的政治与技术困境
咸丰时期,朝廷疲命于东南,铜瓦厢决口后,更资以河为屏障,决口由“缓堵”至不堵,对于治河实在是力不从心。清廷在雍正年间设置南河、东河河督,分别管辖江苏段和河南、山东段。“河工本系专门之学,非细心讲求,躬亲阅历不能得其奥窍”,河员必须试署一年,期满黄河安澜后,方得实授。由此可见朝廷对河员选拔的严格和慎重。黄河北徙后,南河机构在咸丰十年(1860年)被裁撤,东河机构也逐渐缩减,铜瓦厢以下的新河道由不谙河务的各省督抚负责,河政体制濒于解体。
自决口之时起,朝野各方即对是否让黄河复归故道几度展开争论。从政治上看,明清时期黄河与漕运关系至为密切,除黄河本身之一部成為漕路之外,洪水及大量泥沙对于漕运及河道有着绝大的支配力,致使漕运断绝,酿成国家极重要之问题。冯桂芬曾言:“近代治河总为漕运索掣,以致两难。”(《显志堂稿》)漕运制度决定了黄河治理必然要围绕着“保漕”来展开。河务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物料、劳力和技术来维持,代价极其高昂,黄河改道山东后,漕粮改为海运,河工经费骤减。时值清廷边疆危机四起,无论塞防海防均急需大量军费保境固边,黄河复故需耗资五六百万,巨款难筹,权衡利害,复故之议遂屡次被否决。
从技术上看,华北平原人口日繁,人进水退,河道面积缩小,自然之水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束缚,固定河道成为明清两代治河之首选方策。明代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清代靳辅继之“以堤束水”,均是采用堤防作为固河之技术手段。新河道形成后,河政崩坏,下游河防虚空,两岸“乡民荷锸携筐,自筑小堰以卫田庐”(王质彬:《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3年),堤防以民埝为主。直至同治末年,始有官修堤防,其时距铜瓦厢决口已有二十年。寻根扫描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治和动员能力,水利技术则为社会经济制度服务,整套治河体系历经明清两代已日臻成熟,其有效性也已被证明,那么,这种“成法”便不会轻易改变。当政者不希望承担由于变革带来的不稳定性,因为它可能造成民生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导致政局跌宕。因而,明知黄河亟须大治、根治,晚清朝臣们论治河依然因循“增立堤防”的旧章,提出“治标即所以固本”来敷衍搪塞。伊懋可认为,18、19世纪中国的水利经济陷入“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模式中([美]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治河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限制了河工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晚清黄河治理在政治和技术两方面均遭遇困境重重,如何突破瓶颈,人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向外探求新的治河对策。知河而治:近代测验理念引入及其
应用实践
历代论治河之书数不胜计,“惜多数作者长于文字,甚于知河”(《历代黄河文选》[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不了解河性,水文知识贫乏,成为黄河不能根治的重要障碍。18世纪初,清廷利用耶稣会传教士的勘测技术来测量疆土,地理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因素,逐渐被运用于水利工程。
咸同年间,冯桂芬即强调有选择地利用西学,认为治河非有精密测量不可,河臣们也意识到测绘河图与河工关系尤重。光绪八年(1882年),河道总督梅启照派员测绘河图,并言“黄河修守之法,必先明乎河面之广狭,河身之深浅,河流之曲直,而后知缓急之机宜”(《再续行水金鉴》第十一册,河水六,卷一百九)。光绪十五年(1889年),河道总督吴大潋上疏请求朝廷在河南省设立河图局,“选调津沪闽粤各局熟谙测绘之委员学生二十余人,咨送来豫,分段测量”(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七,工政四河防三),由具备近代测绘知识和技能的人员用仪器精确全面测量河南、山东段黄河。
伴随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渗透,近代水利科学和工程技术也被介绍到中国,欧美工程师们相信,西方科学能够帮助中国减轻黄河的灾害。早在清朝官员建议实测黄河之前,一位英国人便对新河道进行了测绘。1868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成立“黄河新河道考察委员会”,英国探险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以利亚(Ney Elias,1844-1897)带领一支探险队历时两个月,对黄河的新河道进行勘测,从铜瓦厢到人海口“绘其新道之图”。他将此次探索黄河河床的情况写成论文发表在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第一次精确描述了黄河改道的情形。
光绪十三年八月(1887年9月),黄河在郑州决口,历时一年零四个多月才得以合龙,堵口耗资达一千万两白银,这使得黄河治理再度受到各方关注。中西人士纷纷设策论法,登诸报章,其中“西报所载长章短篇不下数十篇”,“雄辩侃侃,互有烦言”(《格致汇编》1890年第五卷,夏)。1889年,受荷兰海外工程推广社团派遣,近代第一个欧洲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访的两名工程师向李鸿章提出中荷水利合作建议。他们重申堤防是第一位的同时,指出近代水利工程广泛搜集水文学数据的重要性,如速率、排放量、化学成分、沉淀物负载等,并预言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治河经验与近代水利知识相结合,将会突破黄河治理的困境。虽然清政府最终没有接受合作计划,但荷兰人带来的全新水文学知识,开启了中西水利合作交流的新意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黄河筹议大修,李鸿章奉旨“考求西国治河新法”,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受邀来华考察黄河。他明确提出:“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从全流域治理的角度看待黄河问题,言历代谈治河者所未言。同时指明治河应先办三件事:“(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之宽窄、深浅,堤岸之高低、厚薄……均须详志。(二)测绘河图。(三)分段派人查勘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再续行水金鉴》第十四册,卷一百三十九,河水九)此三件,均未脱“知河”二字。知河而治,新兴的水利科学给困顿了半个世纪的黄河治理带来了一线曙光。
精确测量是用科学方法治理黄河的初步工作,中西治河专家莫不建议由测量着手。1917年,北洋政府聘请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费礼门(John Freeman1855 1932)担任督办运河工程总局顾问,从事改善大运河工程及黄河研究。费礼门两年间数次实地考察了黄河下游,他发表了《中国的洪水问题》,文中对中国历代治河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但认为实地“用科学方法作各种观测”,在实验室“用新式仪器作精密研究”,“使过去所习用之旧法得以改良,仍有其必要”。(《历代治黄文选》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洋政府时期,黄河下游管理分属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政府,各有其测量机构。山东河务总局最早成立测量组,历时7年完成精确测绘,得到山东黄河河道详图,这是河政机构首先实测的带有等高线的现代地形图。191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在黄河若干地点作水平测量,并分别于河南陕县、山东济南泺口设立水文站,测验流量、水位、含沙量和雨量等,这是黄河干流上设立最早的水文站。虽然各省测量工作的标准不统一,但在政局复杂、财政困难的情势下,测绘工作始终不断,收集的数据也极有价值。
1933年9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调派一批技术人员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测量队,以及导渭工程处测量队和水文测量队,将基础测量纳入日常河工范畴。至1937年,实测完成黄河孟津至利津一段黄河河道及两岸地形,共测河道图1.3万平方公里,计万分之一图692张,此为黄河下游治导工程之主要资料。(《黄河水利事业资料》,民国36年2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9-50-261-01)1934年成立精密水准测量队,至1946年完成从青岛至兰州黄河流域的精密水准测~2586公里。黄河之辩:民国时期黄河问题讨论
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英国工程师玛礼孙(G.J.Morrison)考察黄河前,曾前往天津拜谒李鸿章,交谈中,越发感受到黄河治理的难度:“余屡谒李傅相及他大宪面谈此事,得悉黄河之灾,为害最重。初思,所已试用修治之旧法可必能成功;再思,如用所设各法修筑堤岸或可能成功;后思,无论用何法修治总不能成功。”(《格致汇编》1890年第五卷,夏)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最大与最小流量相差甚远,洪水期短,多数泥沙是在洪水时带来的。令中外水利界人士困扰不已的,无非为其举世无匹之含沙量找到解决方略。至入民国,黄河问题的独特性令西方水利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持续而深入。
治河之主要目的在于防洪,堤防则为防洪之首选,而黄河之堤防系统却时常受到批评,盖因“堤之为用在防洪,未可以治河工具视之”(《黄河问题讨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20世纪以来,中外水利学者针对如何改善黄河堤防系统展开了热烈讨论。
1919年,费礼门实地考察了黄河下游,他有两个重大发现:其一为黄河下游的堤距过分宽广,即便最大洪水也仅需三分之一英里的宽度就能够顺利通过,而实际堤距却达四至八英里;其二为洪水期间的黄河能够自行刷深河床,一日之内便可将无数细沙挟往他处。他建议筑一条直线新堤以约束新河槽,使之不复迂回曲折于两岸中,但必须在黄河选择长约二至三英里的河道先行试验,以便验证和改良其建议。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恩格思(Hubert Engels,1854-1945)以首创模型试验著名,是近代水利界权威之一,他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即以黄河为题。他认为黄河堤防之病不在于堤距过大,而在于缺乏固定的中水位(常態水位)河岸,因此河流便得以在两堤之间左右摆动,不受束缚,一旦河水中流逼042近堤身,决口则不可避免。主张治理黄河以固定中水位河岸为第一要务,即在现有内堤之间,裁去弯曲过甚的河槽,避免河水直冲,堵塞其支叉,并施以适宜的护岸工程。
方修斯(Otto Franzise,1878-1936)是恩格思的学生,受聘于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闲暇之余也从事黄河研究。他撰写了《黄河及其治理》一文,发表前曾给恩格思看,方氏治河主张与费礼门更为相近,即在现有黄河洪水河床中加筑新堤,使之缩狭,达到刷深河床的目的,与其师的观点显然有异。恩氏则认为此乃一不合理之举,竭力反对一切缩窄堤距之建议。二人往返讨论,短短数月之内,往来信札多达一二十通,演成激烈的笔战。恩氏提议将双方信札寄予沈怡,在中国发表,以便引起公开讨论。
西方学者关于黄河问题的讨论引发国内学者的积极参与,信函、人员往来交流不断。我国水利学家李仪祉主张通过试验来解决彼此间之争端,试验的目的在于探究堤距对于洪水位、洪水之冲刷力(河槽是否被刷深)及河底与滩地之形成等所产生的影响,为确定黄河治导方案提供科学的参考。1931年7月,恩格思在德国奥贝那赫的水工及水力试验场做了大型的模型试验,试验结果显示,将堤距缩小之后,洪水来临时,河床非但没有被刷深,水位反而被不断抬高。但因此次试验用的是清水,与黄河的水文状况不尽吻合,建议特别为黄河再举行一次试验。试验在1932年6月至10月进行,名为第一次黄河试验,试验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
1933年8月,黄河突发洪水,陕州测得最大流量竟达14300立方米/秒。李仪祉致长函与恩格思,表示赞同他固定中水河槽的主张,同时提出两岸滩地亦须保固。1 934年,国民政府委托恩格思做第二次黄河试验,并委派沈怡赴德参与此事。第一次黄河试验采用的是直线形中水模型河槽,此次则改为“之”字形,以便复核第一次黄河试验结果是否正确。
李仪祉还交付沈怡一封手札,嘱咐他代向恩格思请教,其中最重要的是廓清方修斯与恩氏不同的治河观点。特别是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倡导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之说,此说在明清两代的治河实践中均一贯秉承实施,虽然未能全部奏效,但部分生效之处已是效果彰著。从字面上理解,潘季驯的理论与荷兰的单百克、美国的费礼门、德国的方修斯的治黄主张颇为吻合,均为缩狭现有堤距,以刷深河床,降低洪水水位。古今中外赞成此说者众,而恩格思教授独排众议,竭力反对。尤其前两次的黄河试验也证明方氏的主张并无实现之可能,这些矛盾之处不能不使李仪祉和沈怡感到非常疑惑。李仪祉时任黄河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治河大业,更期待能通过科学实验和国际学术交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
中国古代治黄有着丰富的堤防经验,但积累经验有余,理论推导缺乏,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16世纪中叶以前,堤防在中国一向被视为有害无益,反对造堤者甚众。自潘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之说提出,观感始为之一变。潘氏筑堤有遥、缕之分,“遥堤约拦水势,取其易守也;缕堤拘束河道,取其冲刷也”(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2,水利珍本丛书本)。由此可见潘季驯当日治河,也尝有固定河道之意,只是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罢了。恩格思在复函中指出:依潘氏原意,此项缕堤乃在寻常水位时,作为固定河道之用者。似此工事,这般使用,其性质已不能以堤视之,而应看作固定中水位河道之护岸工事。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之一种方法,此点实非常合理。(《黄河问题讨论集》)潘氏利用缕堤即可固定河槽,与恩格思的方法实则相同。潘氏力主筑缕堤以束水,按理他也会赞同费、方二氏的主张,但亦指出,若堤防过于卑薄,便起不到制约作用,“且夹河束水,窄狭尤甚,是速之使决耳”。堤距过狭反而加速溃决,这里所描述的结果正与黄河试验重合。
黄河洪水多形成于中游,澎湃激荡,骤出峡谷,挟沙带水,其势凶猛,宽堤距可以缓和水性,其作用如同蓄水库一般。三次黄河试验均证明,同样筑有堤防的河槽,堤距宽广者(宽大的洪水河槽)较之窄狭者有利,“大堤距乎?小堤距乎?”的论争至此已经廓清。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平汉铁路黄河桥下游三处地方实测黄河横断面,三个横断面俱甚为宽阔,但河槽反得以刷深更多,这就足以证明恩格思所做黄河试验之结论与实际相符合。试验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就是发现和检验新的发现。
综观之,中西古今水利学者对于黄河治理,所采之方针在原则上实无二致,即所谓“以水治水”,借河水自然之力以刷深河床,由此達到降低洪水位之目的,所不同的是各自建议所采用的方法。而从实际工程性质言,则恩、潘意见更趋一致。历经几年的研究、辩论、试验,运用近代水利理论对古代黄河堤防体系进行了科学分析,黄河问题讨论至此告一段落。
结语
自洋务运动始,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逐渐引入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后,改良派开始将政治革新与科学昌明联系起来,认为“西政之善本于科学”(《严复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人们逐渐认同这种观念,即科学是一种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客观方法,凭借其广泛的、具有精确性的知识体系,不仅提供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全新的世界观,而且可以成为治疗中国百病的一剂方药。利用科学方法解决黄河问题,使其摆脱“中国忧患”的象征,成为中国水利工程师奋斗的目标。近代黄河治理科学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积极迈进。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民国黄河档案研究(1911-1949)”(14YJA770022)、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民国黄河河政体系研究”(2014-GH-4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