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曾祖母
张慧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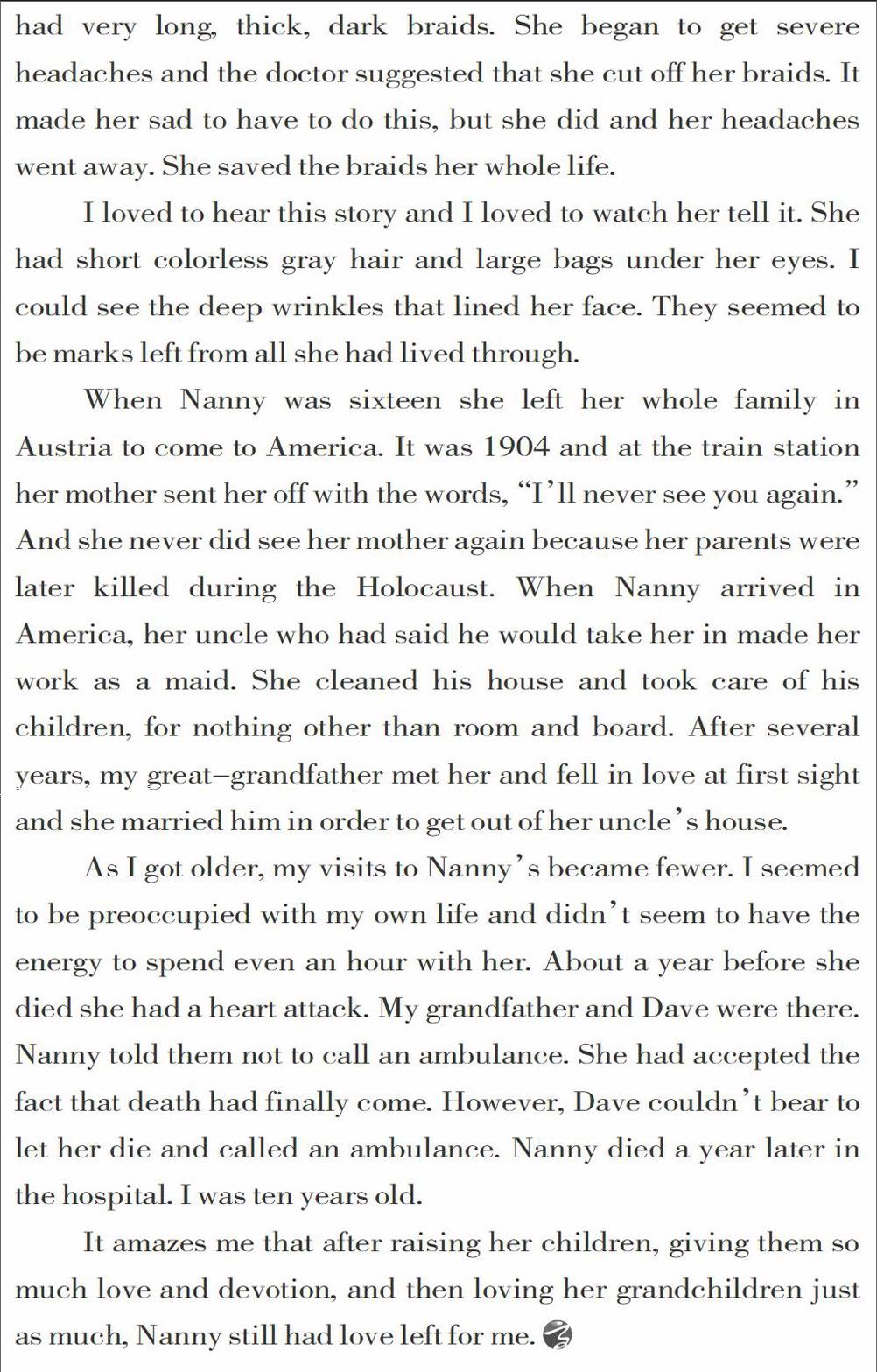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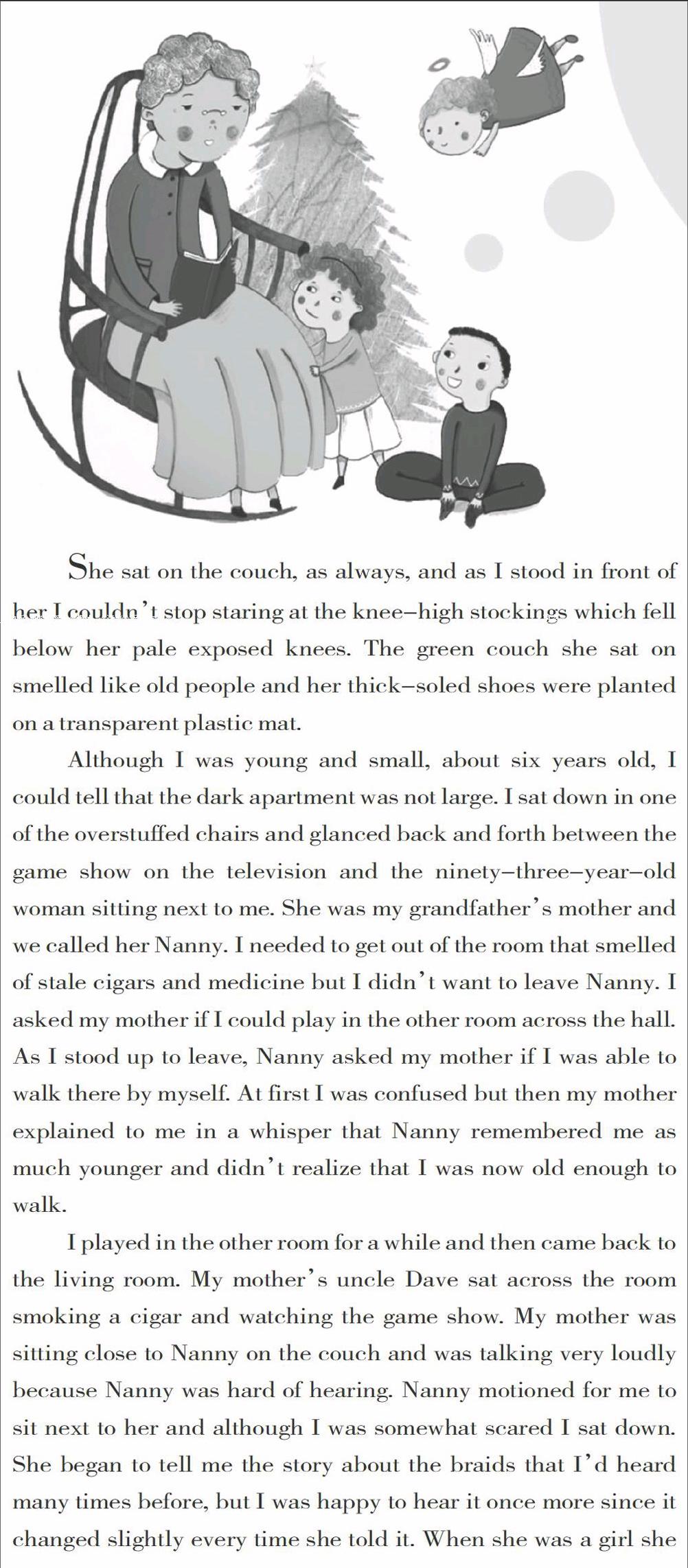
她也坐在沙发上,和平时一样。我站在她面前,忍不住盯着那双及膝长袜,袜子已经滑落到膝下,让她苍白的膝盖露了出来。她坐的那张绿沙发闻起来有股老年人的味道,她脚穿一双厚底鞋,踩在一块透明的塑料地垫上。
尽管我那时还小,大概六歲吧,但能感觉到那套昏暗的公寓面积不大。我在其中一把带加厚软垫的椅子上坐下,眼睛在电视上的竞赛节目和这个坐在我身边的93岁老太太之间来回扫视。她是我外祖父的母亲,我们叫她外曾祖母。我想要离开这个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雪茄味和药味的房间,但我又不想离开外曾祖母。我问妈妈,我是不是可以到走廊那头的另一个房间去玩。当我起身要走时,外曾祖母问我妈妈,我是否能自己走到那边。一开始我很困惑,接着,妈妈就悄声和我解释:外曾祖母记忆里的我比现在小得多,她没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会走路了。
我在另一个房间玩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客厅。妈妈的叔叔戴夫坐在客厅的另一头,一边抽雪茄,一边看竞赛节目。妈妈则紧挨着外曾祖母坐在沙发上,很大声地说话,因为外曾祖母耳背得厉害。外曾祖母示意我坐在她身边。尽管我有那么几分害怕,但还是坐了下来。她给我讲起了她的辫子的故事,我虽然之前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还是愿意再听一遍,因为她每次讲都有一些小变化。她还是个姑娘时,有又长又粗的黑辫子。后来她开始头疼,而且疼得厉害,医生建议她把辫子剪掉。虽然剪头发让她很不开心,但她还是照做了,她的头也就不疼了。这辫子,她保存了一辈子。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也喜欢看她讲故事时的样子。她有一头灰白的短发,眼睛下面有大大的眼袋。我能看到她脸上布满的深深皱纹,它们就像是她一生的经历留下的印记。
外曾祖母16岁时离开家人,独自从奥地利来到美国。那是1904年,她的母亲在火车站送她时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也确实再没有见到她母亲,因为她的父母都在二战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被杀害。外曾祖母到美国之后,之前说过要收留她的叔叔却把她当成了女仆,支使她干活。外曾祖母为他打扫屋子,照料孩子,得到的却只有每日的食宿。几年后,我的外曾祖父遇见外曾祖母,并对她一见钟情。为了离开叔叔家,外曾祖母嫁给了他。
随着我慢慢长大,去外曾祖母家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我似乎整日忙着过自己的日子,根本没有精力花上哪怕一个小时陪陪她。她在去世的前一年犯过一次心脏病,我的外祖父和戴夫当时都在。外曾祖母跟他们说不要叫救护车,因为她已经接受死神终于来了的事实。然而,戴夫不忍心就这么让她离开,还是叫了救护车。一年后,外曾祖母在医院里去世。那年我十岁。
外曾祖母不仅养大了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有如此多的关心与热爱,而后又对她的孙子们付出了同样多的关爱。经历了这些之后,外曾祖母依然还对我疼爱有加,这着实令我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