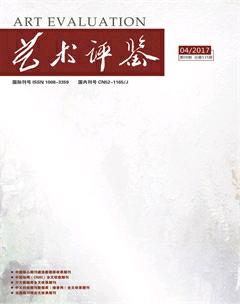理解周文中: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关键词是“独立”
杨思思
摘要:旅美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以一种批判、反思现代性的哲学高度审视音乐文化的未来,站在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上,结合亚洲传统美学和西方前卫技法进行音乐创作。周文中先生创立“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架设理解与对话的桥梁,对于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他认为其关键词是“独立”:独立于西方文化,独立于自己的文化,独立于陈规陋习。理解周文中,就是要理解其关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关键词——“独立”,即独立地对待文化传统、独立地坚守民间传统、独立地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周文中 中国音乐文化传统 民间音乐文化 中西音乐文化理解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08-0002-05
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音乐创作、表演、教育以及理论建构等策略问题甚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引入西洋音乐教育体制建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一百年之后,音乐界开始反思这一教育体系置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和未来建设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一反思起始于20世纪末尚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音乐》所刊发的有关“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两期增刊,《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刊发的“多元音乐教育”增刊以及音乐理论界有关“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大讨论,可以看成是这一反思的主要标志。而此时期的周文中则在一次“欧亚音乐节”(1993年)上明确提出了欧亚音乐未来发展策略的关键词是“独立”,这正是我们理解有关中国音乐未来发展和建设的基本依据之一。
旅美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当时中国所遭受的世界现代性极端形式强加给中国的民族灾难,以及中国深厚的艺术文化传统和地方音乐民俗均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使得作曲家总是上升到批判、反思现代性的哲学高度审视音乐文化的未来,站在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上,结合亚洲传统美学和西方前卫技法进行音乐创作。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一位热心的文化使者,周文中先生创立“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架设理解与对话的桥梁,重新解读和诠释东西方艺术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当地少数民族族群有形与无形艺术遗产的“保育”工作,并通过开办培训班在当地年青人中传播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只有根植于本地文化所生产出来的艺术才能有自己的独立性,也才能对世界文化有真正的贡献。[1]对于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是“真正勇士”,其关键词是“独立”:独立于西方文化,独立于自己的文化,独立于陈规陋习。[2]
“独立”一词的提出,是周文中先生站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上对现代化语境中音乐文化生产深邃地反思批判的结果,是对当下东方音乐创作和表演所表现出来的西化行为和“依附性”发展深刻剖析和否思的结果,是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和思想“禅”悟之后,将其明确为中国音乐艺术未来发展之动力和主体性的哲思和宣言。理解周文中,关键在于理解中国音乐文化如何走上未来的独立发展之路。
一、独立地对待文化传统
对于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及其当下的价值和意义,周文中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与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文论中,也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
周文中先生的创作总是从中国的哲学思想出发,将自己的创作技巧看成是逐渐结晶而成的儒家美学观念和道家德行观念的流露:乐“生于情”,音为“乐之象”,旋律和节奏乃“音之显现”,大音并非在“艺之善”,而是要达到“自然固有的精神力量”。[3]
1949年,周文中先生创作了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山水》,这是作者对山水之自然和山水之艺术的深刻领悟。其中三个乐章分别建立在一个传统的中国旋律模式上,以引喻的方式表达自然的景色、声响和诗意。作品的最后部分采用了明人刘基的词《眼儿媚·秋调》所表达的意境:萎萎烟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两行疏柳,一丝残阳,万点鸦栖。用声音作为书法之笔来表达山水形貌之局限,胸襟之深广,自然之本质以及中国绘画的水墨精神。[4]
1960年,周文中先生为木管交响乐队创作了《隐喻》,采用《易经》卦相和阴阳关系建构曲体,“其基础是八个象征性图形的体系(卦),每个图形都是两极,即阴和阳的一种三线的排列,阴和阳分别由一条断线和一条直线代表,这些卦相滋生万物的不断变化的力量,在恒变和恒定的状态中相互作用。”“八个‘变就是八个变化不定的调式,其每一个调式本身都在持续变化,但又处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统一体中”。[5]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周文中先生一直在中国传统中历练乐思,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区寻求音乐创作的观念和形式技法。如:自《隐喻》中首次试验了“可变调式”之后,周文中先生开始对这个综合了中国易经哲学和书法艺术原则的音乐语言进行了长期探索,陸续创作了长笛与钢琴二重奏《飞草》(1963年)、打击乐四重奏《谷应》(1989年)、弦乐四重奏《浮云》(1996年)、《流水》(2003年)和六重奏《霞光》(2007年)等。[6]
周文中先生所撰写的文论也在许多篇幅中表达了他独立地对待文化传统的思想。在《走向音乐的再融合》(1967年)、《东与西、古与今》(1968年)、《亚洲观念与20世纪西方作曲家》(1971年)、《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1981年)等文论中,充分显示了周文中先生的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学腑和独到的洞察力。他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音乐史料,从新儒学的视角出发,对孔子的“乐论”,庄子的“道德”观念提出了符合当代艺术发展的诠释,认为儒道之“德”标准可以解释为“事物的本性”(that by which things are what they are)。[7]
一般认为,中国音乐是注重单旋律构造的音乐,但是这种单旋律的基础却是一个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单音。与同沈洽先生注意到一个单音的音腔一样,周文中先生也将单音作为“音乐意义的单元”予以肯定,以结构的观念来看待单音的偏移属性。在他看来,中国音乐传统中有关单音的偏移属性乃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技术传统,如何对待这一传统手法,关涉到音乐创作的立场。他认为,“一般反对将音的偏移作用视为作曲之实质元素的立场”是一种负面观点,“这种观点若是成立,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有多声部音乐,也不会结构性地运用音量和器乐音色。第二,这个观点只有当我们将音乐局限在西方音乐的范畴里才会具备有效性。”[8]因而在周文中先生的观念里,中国的单音是一个音乐意义的单元,它的偏离、它的游移非但不应嗤之以鼻,反而应该将其肯定为西方音乐所不具备的中国音乐所特有的结构性要素。
周文中先生将中国音乐和亚洲音乐的形式、内容以概念和观念上升到美学高度予以解读,以此提出了亚洲美学的观念。那么,什么是亚洲美学?周文中先生举出了十个初步设想:1.吸收外来文化;2.大众音乐与精英音乐的互融;3.音色与音高互补;4.语言作为美学的先导;5.诗、画、乐三位一体;6.表达中的隐喻;7.结构的简练;8.与宇宙和谐;9.超越对自然地模仿;10.重视精神修养。上述十个方面反映了周文中先生对亚洲(包括中国)音乐美学传统的基本认识,具体到中国音乐美学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音乐美学的社会学传统。周文中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收外来文化的能量。中国文明的巨大容量总能有效地平衡这样周期性汇聚的外来音乐文化影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外来观念。显然,周先生对中国音乐文化这一容量的评价是基于中国历史上魏晋、隋唐时期对于外来音乐文化的消融能量而言的,他相信中国文化的整合能力,但也指出了“自己的意愿”的重要性,以我看来,周先生这里强调的“自己的意愿”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传统的根基作用和主体地位。对于大众音乐和精英音乐的互融而言,周文中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音乐实践有着周期性的分与合、民间与宫廷、大众与精英之间相互传播、融合。这样的事件自然是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有关的,但是重要的这种大众与精英互融之后所形成的观念对于中国音乐艺术乃至亚洲音乐艺术的发展来说却是纯艺术性的。勿容置疑,这一传统,即在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音乐趣味或美学信奉上的交融过程,看起来与吸收外来观念一样都是音乐中的复兴力量”。[9]
第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技术性传统。首先,周文中先生从荀子的《乐论》中考察中国有关乐、音、声的传统观念,提出古代乐器的八音分类实际上是按照音的特质为标准的,所谓“八”,即是指乐器的“八种音色”。一个乐音不仅由音高也由音色来定义,是音色和音高互补的结果。正是由于音色和音高互补,因而语言便成了美学的先导,诗与画与乐三位合一,在诗歌和绘画简练手法的互融中,乐之结构也越发简练,这一切均出自中国汉字的表意性、象形性和形声性。周先生认为:中国汉语的每一个字自身都是一个诗意的、图案的、声音的存在,同样,“乐音作为一个包含音高和音色的声音现象,其自身也能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表现特质的音乐事项。換句话说,单个音的产生与控制可以创造出足够丰富的音乐维度,如音高、音色和音强的改变,诗意的或声音的美均由其自身所唤起”。[10]
第三,中国音乐美学的精神文化传统。对此,周文中先生提出中国音乐美学是与宇宙和谐的美学,作为农耕文明的民族,中国人按照传统致力于自然,并在精神上被自然之美所吸引,在此基础上超越对自然的模仿,进入一种精神修养的境界。如在古琴音乐中,由空弦的散音表示“地音”,因为散音厚实而又宽广;由泛音表示“天音”,因而泛音空灵而又神秘;由按音表示“人音”,因为按音由人控制,有着较多的机巧。
周文中先生不仅重视东方传统,同时更强调深刻地领会传统之神韵,针对西方作曲界的“东方思潮”,将东方作为奇异色彩而浅尝则止的风潮,他多次告诫西方青年作曲家要注意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和内核。他用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话“物物而不物于物”作为告诫:利用物而不受制于物。他说:“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往往是危险的,而今天却不幸相当盛行,那就是过分草率、肤浅地捕获一些新观念和新技巧,并纯粹将其当成异国文化的常规和成果。东方的伟大之处确实是在于其利用物的智慧及其对任何新异的、非必要的外来物的回避。不理解庄子的教诲,而去纯物质主义地采用东方的实践,只会产生出更多的20世纪风格的《土耳其进行曲》”。[11]
二、独立地坚守民间传统
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著名作曲家,深入民间不是为了“采风”,而是为了民间传统的“保育”,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许多从事音乐创作的青年才俊亦重视民间,深入民间,但其目的并未是关怀民间、理解民间,而是将民间视为其创作的元素去填充其曲作的版权。周文中先生对待民间的态度截然相反,在“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周文中先生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达十余年之久。对于全球化所携带的西方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排山倒海而来的冲击,周文中先生给予了人类生态主义的终极关怀,他说:“我们认为原住民与地方文化的生存空间应该与一些自然界‘濒临绝种的生物一样获得保育。”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除非进行有效的‘拯救,否则所有原住民的、区域性的、甚至重要的非西方文化都可能成为‘濒临绝种的文化”。[12]
然而周文中先生对于民间文化的“保育”有着自己“独立”的认识,他告诫我们,民间文化的“拯救”只是采用一种静态模式的话,那么保育工作将难以持续。只有让民间文化同时继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才会出现蓬勃生机。[13]但是,谁是继承和发展民间传统的主体呢?学者在此中有何贡献呢?周文中领导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在云南的两个合作项目解开了谜底。
项目之一是帮助云南民族学院成立民族艺术系,其目的是以教导原住民的音乐、舞蹈、视觉艺术和工艺为主。据介绍,云南民族学院最初是想成立西式的艺术系,在历经长达4年时间的劝导,决定与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依据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优势,创办前所未有的民族艺术系。“这个艺术系成立于1994年,聘请村里的艺术大师来从事短期教学,学生也会定期到村里与当地的大师学习,并与村里联络人共同做田野调查。”显然,我们看到了周文中先生有关民间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主体”的主张,这一主体即是当地文化传统的“持有者”,而非学者、政府等文化他者。
项目之二是成立了一个田野考察团,与村里受人尊重的人士合作,共同进行研究。该团队成立于1994年,由云南当地的文化人类学家带领,参加的机构是省级的文化机构,为了促进以小区为单位的文化研究,该团队还与村里小区做进一步交流。如与丽江附近纳西族村寨合作,为当地年轻村民提供民间传统技艺的训练,又如与巍山县合作,对14世纪流传下来的鼓楼与周围环境进行修复。这一团队的研究工作强调“合作”这一概念,尊重主体的文化诉求,专家学者以“合作”的姿态参与原住民的文化发展计划,是周文中领导的民间文化“保育”工程的关键词。
周文中先生敏锐地洞察到民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必须落实到中国现行音乐教育制度的改革的问题上,这正是他“独立地坚守民间传统”的核心所在。他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彻底崩溃,教育改革旋即进行。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日本与苏联的影响,这些教改是以减少中国文化课程为起始的。他发问:如果中国的教育舍弃了中国艺术、文学、哲学,甚至是历史的课程,那么我们如何期望这个国家拥有激发出属于现代中国或东西方融合的文化创造力?他提出,我们必须改革当下教育的基础课程,需要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不仅针对艺术而是全面性的,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的教育工作者为他们的学生开设亚洲人文学科的课程以及相关研究。
三、独立地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
如何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周文中先生反对四种极端的声音:一种是来自西方的霸权意识:如果你(非西方)能像我们(西方)一样创作,你必是一个天才;一种是来自西方的优越论:戈壁沙漠地区的音乐是绝顶原始的,也绝不可以像我们一样高雅;一种是来自东方的极端民族论:我们必须通过回到我们两千年前的辉煌来保存我们的文化;一种是来自东方的依附发展论调:你必须跟着西方来使我们的思想现代化。[14]
上述第一种观念同样遭到了葛兰西的批判。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资产阶级现代性是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15]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自认为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如果说上述的第一种声音是一种西方强势心力的宣传论调的话,那么周文中先生首先发觉了这种宣传论调的霸权意识,他忠告非西方世界的艺术家:非西方世界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或更好的艺术家,而是具有独立思想和勇气的艺术家。[16]
上述第二种观点十分传统,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在十九世纪得以发展,它源自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观点,以欧洲的技术标准和美学标准将世界文化分为高级与低级、先进与落后的层次,最终造就一种“欧洲文化中心”的论调。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觀,让欧洲无视历史真相,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最终造成整个世界的学术界,长久以来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东方内部的文化中心论调,这一文化中心论调是现代性进化论观点和文化霸权意识的变相处理。最终使得东方世界往往采用封闭式策略。将东方与西方置于一个不可调和的两极,人为地隔离或对立起来,将自己想象在一个封闭的时空结构里,希冀在这一想象的相对封闭的时空结构中,建构起相对独立的自成一体的传承体系,以实现东方文化传统“正宗”的、纯粹的继承和传衍。以上策略无疑是现代性“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的一种变相处理。[17]周文中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愿景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下,这种美好“愿景”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东方音乐文化传统的自在性行为将不断遭到解构。因此,他警告:“就东方作曲家来说:羞辱西方现代音乐,却不了解其文化内涵,或只是将自身文化中的某些特性移植到西方音乐的理论与实际创作中这几乎与西方全盛时期的奴性崇拜没有两样”。[18]
第四种观点是一种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研究领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了其核心思想之所在:即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并表现为“支配——依附”性结构关系。[19]在中国当下音乐文化发展策略中,“依附性”表现为西方专业艺术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支配。管建华先生曾说,“依附性地发展,促成了西方音乐单边主义的扩张,音乐技术对音乐生活世界的殖民。更大的失误在于,我们会在世界音乐中以音乐专业现代性的专业创作作为我们音乐文化唯一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依据,充当西方音乐体系整体性中的‘中国元素,由此丧失了自己音乐文化历史的整体性”。[20]
周文中先生正是在反思、批判上述四种极端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未来音乐发展的核心概念:独立!独立地对待文化传统,独立地坚守民间传统,独立地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就中国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而言,对待文化传统,既要深入细致地理解传统,又要在传统的根基上大胆而又勇敢地创新传统;对待民间传统,不仅要坚守传统,不能静止地固守传统,要在继承中发展传统;对待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判断,既要反对文化霸权,又要警惕文化奴性,既要独立发展,又要防止封闭,既要学习他者的优长之处,又要摒弃文化中心观念和优越论调。这里,我想摘取周先生在一些研讨会上的谈话和文论中的论述作为本文
四、结语
(一)我指的是目前我们更应该强调东西方之融合而非影响,因为东西方融合即指明了东西相互间不可避免的影响。……不管他喜不喜欢,用传统风格或纯粹的西方风格都无法使他扮演尽职的角色或对东西方交流有所贡献。……作曲家必须掌握双文化或多文化的能力及音乐语言,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很重要的元素。(“亚洲及西方音乐、影响还是融合”,韩国国家艺术学院,汉城,1977年)[21]
(二)就西方作曲家来说:提倡回归过去的实际创作,或抄袭以前的伟大成就,是自恋的最佳表征,并且是走进死胡同的最糟路径。……执意忽视他人文化的智慧,一味地扼杀他人对自身文化的意识则成了文化殖民主义。……宣称西方音乐在近几世纪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则又是一种自欺自贬的做法。(ISCM-ACL,世界音乐节,香港,1988年)[22]
(三)我有意偏向那些我认为更具有“亚洲性”而非在阐述观念上更接近西方美学的原则。西方音乐美学的主要趋势是将音乐视为一种纯粹的音乐现象来研究,认为音乐只有在其自身的术语体系中才能被理解,因而导致西方对美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结构和风格上的考虑。(“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23]
(四)中心(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作者注)注意到,中国富有创造性的青年艺术家们常对西方现代理念有一种肤浅的热爱,但他们对其文化环境却缺少了解,或仅仅是将他们自己的文化特征移植到西方理论和实践之中。同样普遍的是,在文化突变的年代,有些人会对自身的文化或现代西方文化采取否定与排斥的态度。……警惕“文化殖民”——无论是给予还是获取——都是各种文化间交流计划的基础。(“美中艺术交流:一种哲学探寻的实践”)[24]
(五)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些亚洲国家已经在为重新发展他们的音乐实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一些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幸的是,他们多数成就难以超出艺术殖民主义特点的范围。他们多数新音乐尽管技术精湛,却实际上是西方的,缺乏来自融于自身的文化之根才能有的那种灵魂。……亚太作曲家的新纪元意味着这些作曲家,将不只求西方世界的肯定或成就。他们要求自己对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样都要有透彻的了解。……但如果大部分的亚太音乐教育继续跟随西方模式,把音乐家当成欧洲人来训练,这个新纪元永远不会来到。……最后,亚太社会应该停止捕捉西方脚步的殖民思想。他们必须明了自己在文化方面对新世界秩序能有什么贡献,他们也必须学着尊重其他的艺术创作者,他们也许不属于西方或东方,但实际上却兼容并蓄地超越二者。(鞑靼斯坦喀山“欧亚音乐节”上的讲话,1993年)[25]
注释:
[1]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2]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53页。
[3]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3-4页。
[4]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5页。
[5]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7页。
[6]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2页。
[7]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3页。
[8]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8页。
[9]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06页。
[10]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08页。
[11]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6页。
[12]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樂文集》,第175页。
[13]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75页。
[14]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62页。
[1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53页。
[17]张应华:《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音乐学院,2012年。
[18]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60-161页。
[19]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35页。
[20]管建华:《在中国的音乐学院中设立戏曲民间音乐系的思考》,第16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宣读,2010年10月。
[21]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58-160页。
[22]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60-161页。
[23]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13页。
[24]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31页。
[25]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第162-164页。
参考文献:
[1]梁雷主编.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张应华.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12年.
[4]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5]管建华.在中国的音乐学院中设立戏曲民间音乐系的思考[R].第16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宣读,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