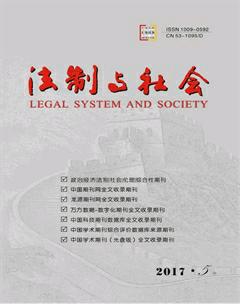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理解与适用
摘 要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是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仍依附于母体的胎儿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在法律单独保护范围。但是,胎儿毕竟是现实生命个体的早期存在方式,因此,加强对胎儿权益的保护,赋予胎儿接受遗产继承和财产赠与等民事主体资格,便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自然人民事法律保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不同,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只是一种期待权,胎儿出生时是活体,是这种期待权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必要条件;在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同时,关注胎儿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保护,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胎儿 民事权利 能力 财产权 生命健康
作者简介:邓周易,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282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总则》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对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增加了“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兒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从民事立法上赋予胎儿接受遗产继承和财产赠与的权利能力,从基本法的层面为贯彻执行我国继承法关于胎儿预留份的规定和合同法关于财产赠与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拓展民法保护的领域,提高我国法律的文明程度和全球化水平,推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与国际胎儿民事保护法律制度接轨,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概述
在民法上,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必要条件。民事权利能力分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法人民事权利能力,两者在取得的条件、权利的范围和成熟的期间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区别。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自然性、法定性和不可剥夺性等特征。首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自然性,即西方国家所谓的“天赋人权”,它伴随生命的诞生而当然地为自然人所享有;其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法定性,自然人能否享有或享有何种民事权利能力均由国家法律所赋予,如在古罗马,法律将奴隶视为物或财产,即属于权利客体,奴隶主或领主可以像对待牲畜一样任意残害奴隶,奴隶并不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再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不可剥夺性。民事权利能力与人身和财产密不可分,没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生命个体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限制或剥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就意味着自然人可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而陷入生存或发展的困境,甚至会失去生命本身。
二、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保护
对人权利的保护是法律出发点和归属。独立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既是自然人属于“人”的必备要件,也是自然人享受民事权利能力的生物性或生理性要件,即有生命的自然人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没有生命的东西不是自然人,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已经告别人世间的逝者和尚依附于母体的胎儿,已经不属于或还不属于独立的生命个体,因此,世界各国法律均不承认或均不赋予死者和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底线”。
但是,已经孕育于母体的胎儿毕竟是鲜活的生命或人类生命的早期存在方式,胎儿最终都要脱离母体降临到人世间,并加入到生命个体成员和社会群体的生活行列之中。而且,胎儿还寄托着父母的情感和亲人的期望,甚至是父母或亲人生命意义之维系,并承载着“传宗接代”和种族繁衍的神圣使命。当胎儿的生命健康受到伤害,当胎儿的父母或亲密关系人因财产继承或财产赠与需要处分财产或分割财产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发生,胎儿的人身或财产权益是否应当给予保护,就成为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设计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胎儿权利保护的历史悠久,早在古罗马时期,罗马法就确立了当涉及或遇到胎儿利益的法律问题时,将胎儿与已出生的生命个体同等对待的处理原则,罗马法学家保罗在其论述中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法律原则:“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问题逐渐增多,为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以不同的立法模式加强对胎儿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概括世界各国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体例或模式,有下列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对凡涉及胎儿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事项,均给予胎儿与自然人同等的保护。瑞士、匈牙利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持此种态度。《瑞士民法典》第13条规定:“子女,只要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 ;《匈牙利民法典》以胎儿出生时是活体为条件,胎儿从出生前第300天开始就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己出生”。
第二种态度是只针对涉及遗产继承或财产赠与的特定事项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持此态度。《德国民法典》规定:“在继承开始尚未生存、但己经孕育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意大利民法典》第1条规定:“同样可以对己经受孕的或者某一生存的、确定之人的、即使在作出赠与之时尚未受孕的子女进行赠与”;我国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也采取这种立法体例:“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第三种态度是不承认或不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1964年《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持此态度。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从这种立法体例中得出这些国家对胎儿权益不予保护的结论。以我国为例,虽然我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没有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但是,1985年4月10日通过的我国《继承法》第28条就已经对胎儿的权益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此,不能仅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就断言中国对胎儿的权益不重视和不保护。
三、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理解和适用
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主体资格、一种期待权相同,胎儿的民事权利也是法律赋予胎儿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要成为现实权利需要同时具备或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胎儿出生前必须要有涉及胎儿利益的遗产继承或财产赠与行为或事实的发生,二是胎儿出生时必须是活体。如果胎儿出生前根本就不存在涉及胎儿利益的遗产继承或财产赠与等民事法律行为,也就不存在胎儿出生后的财产遗留问题,即胎儿无权主张或请求其出生前的财产权益。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死胎),即使存在胎儿出生前的遗产继承或财产赠予行为,已经分给死胎的遗产或已经赠予给死胎的财产,也视为不曾发生或认定无效。
出生是法律事实中的自然事件,直接关系到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有或无,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根据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的观点,胎儿的出生包含“出”和“生”两个要件:“所谓‘出者,乃由母体分离是也。所谓‘生者,乃保持其生命而出是也(否则谓之死产),至保持命之久暂,亦非所问” 。可见,“出”和“生”是两个法律事实,“出”是“生”的前置要件,但“出”不等于“生”(也可能是“死胎”或“死产”)。关于“出”的时间,学说上有阵痛说(认为妊妇开始阵痛就意味着胎儿出生)、一部露出说(认为胎儿一部分脱离母体即为出生完成)、全部露出说(认为胎儿全部脱离母体之时为完成出生)、断脐带说、初啼说、独立呼吸说等;关于“生”的标准,独立呼吸说为目前学界通说 。
胎儿同时具备“出”和“生”两个要件,即完成了由胎儿向自然人的转化或蜕变,法律赋予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变成婴儿现实的民事权利。还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胎儿出生前发生了涉及胎儿权益的遗产继承或财产赠与等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胎儿出生时是死胎(死产),死胎的近亲属(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是否有权主张或诉请涉及胎儿利益的财产(遗产或赠与财产)。从各国立法规定看,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以胎儿出生时是活体为要件的,法律并不承认或赋予死体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如:根据《瑞典民法典》第31条规定和:“出生之前之胎儿,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己出生”;我国《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司法解释,对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原来已经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的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解读为“胎儿特留份”,笔者认为,这是对《继承法》规定的误解。在我国继承法律关系中,“特留份”特指《继承法》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继承法》第28条“遗产分割时,应当保护胎儿的继承份额”的规定,则应当准确地解读为“胎儿预留份”。“胎儿预留份”与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的“特留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两个概念的法律意义完全不同:第一,“胎兒预留份”,保留的只是一种“继承期待权”;而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继承人的“特留份”,则是对现实权利的保留;第二,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是继承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尚孕育于母体的胎儿还不是现实独立的生命个体,只是可能或潜在的“准继承人”,虽然也有遗产继承的民事权利能力,但这种民事权利只是一种期待权,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则该预设的胎儿民事权利,则视为该权利自始不存在。
从各国立法中“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视为已出生”、“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讲究用词中,我们也可以读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之间的区别,即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准民事权利能力”或期待权。
四、胎儿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自然人两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法律在赋予胎儿遗产继承和财产赠予等财产权益“期待权”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赋予胎儿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益的赔偿“请求权”,也是各国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胎儿生命健康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胎儿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刑事保护和民事保护两个法律领域。就胎儿生命健康权的刑事保护而言,主要涉及堕胎或人工流产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受宗教传统的影响,国外信奉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法律不允许堕胎或流产,人工流产被认定为是谋杀或故意杀人行为。如:1803年,英国通过了《妇女堕胎法》,堕胎者最高可处以死刑。但是,自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之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多数国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堕胎。在美国,1973年美国联邦法院就通过个案判决的形式承认了堕胎的合法性,确定了怀孕12周之内可以堕胎的法律适用原则;波兰法律规定在对母体健康构成危险、胎儿严重畸形和刑事罪行期间怀孕等三种情况下允许堕胎;爱尔兰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家,在过去,堕胎在爱尔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2013年爱尔兰也通过了《2013孕育生命保障法案》,准许在母亲有生命危险、可能自杀等限定情况下堕胎。美国法律倡议组织“生殖权力中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立法上仍然限制堕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均允许堕胎,虽然在允许堕胎的国家中堕胎的条件或限制的法律规定并不统一,但是,允许堕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二)胎儿生命健康权的民事法律保护
由于胎儿对母体的人身依附性,胎儿还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因此,通常将胎儿视为孕妇身体的组成部分,对胎儿的损害即是对孕妇身体造成的伤害,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由孕妇或孕妇的近亲属行使,胎儿并不享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胎儿不享有涉及生命健康权内容的民事权利能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胎儿受伤的风险也在增大,因胎儿受损诉请法院判决的案件不断上升,胎儿的生命健康权的单独保护,便成为各国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从立法上看,1900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就规定了胎儿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在侵害发生时,死者与第三者处于其据以对该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负有抚养义务或可负有抚养义务的关系中,且因死者被杀害,该第三人被剥夺抚养请求权的,赔偿义务人必须在死者推测的生命期间会负有抚养义务的限度内,通过支付定期金向该第三人给予损害赔偿。即使在侵害发生时该第三人已被孕育成胎儿但尚未出生,也发生该项赔偿义务”;1899年颁布施行的《日本民法典》第721条也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虽然英国是判例法国家的代表,但是,英国于1976年却通过了专门规定侵害胎儿民事责任的成文法——《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该法涵盖“生而患有残障之儿童的民事责任”和“怀孕妇女驾驶时对胎儿所生侵害之责任”等内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判例法国家也以法院判例的形式确认了当胎儿的健康权受到损害时(如伤害孕妇致流产等),在胎儿出生后,胎儿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向法院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请求。
与胎儿的民事权利的法律适用条件相类似,对胎儿生命健康权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也是有条件的,即以胎儿出生时是活体为要件的。也就是说,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一种“期待权”,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死体,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样“自始不存在”,在此情况下,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能就会转化为孕妇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对胎儿的伤害被视为对孕妇身体的伤害,损害请求权则由孕妇或死亡孕妇的近亲属享有并行使。
(三)我国法律对胎儿生命健康权保护的特点
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单独就损害胎儿生命健康权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并不代表我国不注重对胎儿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保护。与国外直接赋予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立体体例或保护方式不同,我国法律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胎儿的生命健康权。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确立了对于被判处死刑的怀孕妇女实行缓刑的法律原则,之后的《后汉书》和《晋书》中均有因为怀孕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待产后执行的案例。北魏法律正式确立孕婦产后百日行刑制度,这一制度一直被后世法律所沿用。另外,中国古代法律禁止对孕妇进行刑讯与施加笞、杖刑,严禁斗殴致孕妇堕胎与强迫孕妇堕胎的犯罪行为 。
我国现行刑诉法关于对怀孕妇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缓刑和监外执行的规定,刑法和刑诉法关于对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中关于损害妇女流产属轻伤等规定,都体现了保护胎儿生命健康权的法律原则。在刑法之外的法律领域,《婚姻法》和《劳动法》关于男方在女方怀孕期间不得以原告的身份提出离婚诉讼的规定,关于女职工在怀孕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关于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进行高强度工作的规定等,也体现了对胎儿生命健康权的人道主义保护。在司法领域,对于伤害妇女身体造成胎儿流产的民事赔偿,一般是从精神损害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赔偿项目中体现和实现。
诚然,通过保护怀孕妇女人身权利的间接方式保护胎儿生命健康权,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和不足,完善并加强对胎儿生命健康权的直接保护,应当成为我国法律发展或完善的方向。
五、结语
我国《民法总则》赋予胎儿涉及遗产继承和财产赠与方面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任重而道。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胎儿看成是现实生命个体早期的存在方式,胎儿出生是生命的延续,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是生命的夭折。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胎儿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的残害,致害人都应当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其中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保护和关怀,应当成为完善与发展我国法制的努力方向。
注释:
[意]彼德罗·彭梵德著.黄凤译.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戴永盛译.瑞士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王利明.民法学(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5.
龙卫球.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97-198.
彭炳金.论中国古代法律对孕妇人身权的保护.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