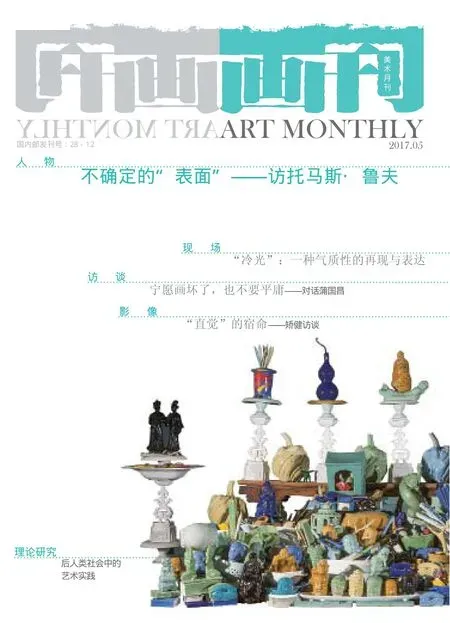不在此地
——对话庄辉(下)
杨 青 庄 辉
不在此地
——对话庄辉(下)
杨 青 庄 辉

《祁连山系-11 》 庄辉 彩色喷墨打印 110cm×88cm 2015 年
编者按:从1992年创作第一件作品《为人民服务》开始,庄辉的艺术一直持续关注个人身份和集体主义的关系。城市、农村、工厂不仅是他在首件作品中设置的三个场域,也成为他20多年艺术创作的视觉重心。从工厂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农村,庄辉在三者的时空关系中穿梭游荡,探讨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种种问题。然而,近两年来,庄辉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具体的变化,艺术家的注意力渐渐由人群投向荒野,由社会转向自然。 常青画廊正在展出的“庄辉:祁连山系”,即呈现了庄辉的艺术转变的最新动向。在展览现场,庄辉用影像、绘画、装置搭建了一个与祁连山对话的空间。通过作品的呈现,庄辉将观众的视线和情感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未知的自然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祁连山系”展览和庄辉近年的艺术变化,《画刊》特邀媒体人、策展人杨青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谈,话题涉及庄辉艺术的方方面面,分两期刊登,以飨读者。
(接上期)
(四)
杨青:你在“玉门计划”之前的作品都非常关注个体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命运遭遇,那么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只能说越来越剧烈。你为什么放弃了对社会的观察和介入,转而进入了戈壁滩的无人区,进入了祁连山里游荡?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转变,希望你能谈谈。
庄辉:我在经历了“玉门计划”产生的思想上的困顿之后,觉得既然我们靠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能找到一个参照系,让自己能够不断反躬自省。产生后来的转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往往走入困境的时候还不自知,而且欲望在到达了一定限度的时候已经变得忘乎所以,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参照系统,让人们能够看到除了现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的世界;另一个原因是刚才我们谈到现实当中有那么多问题,我们都在试图寻找解决方式,但是问题只会越找越多、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我们是否把其他更大的一个空间的事情忘记了。因为这两个原因,我开始离开了之前的创作轨迹,想要找一个更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祁连山。
用一个具体作品来举例,《木工师傅边角料》那个作品产生的想法,就是我当时在木工房里看到木工把有用的板材都截走了,丢弃了剩余的一些形状奇怪的废料。当你把这些木块捡回来,用雕塑放大5倍做出来之后,突然发现它也是一个形状,它自己形成了空间。原本这个无形的空间我们是看不到的,是被忽略掉的,当我们现在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看不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反倒被我们丢弃掉了。
杨青:你所说的“看不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怎样理解?
庄辉:就是指我们认识之外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无形的,它包括特别多的东西。比如说一种理性的和精神的价值体系,已经很少有人在谈这个东西了,我们一直在忙碌争执关于它的对错问题。这只是我们从无形空间当中随便找出来的可以感受的事物之一,我觉得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应该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看人类的这些活动和行为。

《祁连山系-04》 庄辉 单路视频、彩色、无声 10分23秒 2014 年
杨青:认识之外无形的空间也很大,自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包括宗教,但是你为什么落脚到了自然界的祁连山?
庄辉:因为我们现在认识的范围也就在自然当中,除了人的欲望之外,我们能感受到自然的存在。选择在祁连山也是因为它比较具体,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不希望把话题一下子拉到无限远的地方让人捉摸不到。我有哲学的思考,但我不是哲学家,我毕竟还是视觉艺术家,我的空间是靠视觉来打开,不是靠书本或者是言辞,所以还是必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宗教虽然也是在欲望之外的,可是我对宗教没兴趣,因为宗教是一个过去式,并且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过宗教。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精神生活,这就回到中国人讲的山水观念。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精神归宿,那就是在山水当中,这个在绘画里体现得最明显。画里边讲究几法,其中就提到可观、可赏、可游、可走、可居,这几个都是人对自然和山水画赋予了精神的投射。我们没有宗教并不是多么遗憾的事,相反也许是更高级的层次。
(五)
杨青:“庄辉个展”也是很具有转折意义的展览,对于展览的方式、空间的定义和观众的观看都发生了改变,秦思源说“庄辉个展”是你对过去的一次告别,我个人反倒觉得“玉门计划”是告别,“庄辉个展”则是一个开始,从此之后开启了另一种工作方法和展览方式。
庄辉:我做“庄辉个展”其实特别想打开人对空间固有的认识。我们一般对空间的想象都在不断地设计当中,目的就是怎样形成一个展示空间。当我把设计这个概念全部丢掉以后,把作品放到戈壁滩,突然发现所有的设计是一个玩笑。也许我这样讲要招无数人的痛骂,可能会有人说这个无耻的艺术家,多少人都要靠设计这门行业生存下来。
杨青:这种变化也是很颠覆性的尝试,你不再设计空间了,或者说不再挑选空间了,这种重新寻找作品和空间之间关系的方式,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新的出发点?
庄辉:实际上就是打开人的空间意识,这个空间已经不再是具体到某一个白盒子、某一个建筑设计,而是时空。“庄辉个展”之所以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和时空有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展览让我们看问题更宽阔、久远一些,人只有拥有了一个宽阔的眼界和心态,很多眼前具体的事情就会很容易解决,否则永远会陷入各种纠结。刚刚我们说的还有无数的问题等着我做,玉门之后还有无数个问题,那都是纠结的问题。
杨青:因为有了“庄辉个展”这次决绝的实验,有了这种对打破空间迈出去的一步,是不是才有了关联到祁连山的进一步的思考?
庄辉:这两个时期确实有关联,两条线既有平行也有交叉,在去戈壁滩之前就有出走祁连山。我觉得一个在生、一个在死,这两个时间关系上没有绝对的前后次序。
杨青:你在“庄辉个展”里面解释过这样做的原因也包含了对艺术体制的反思。
庄辉:刚开始肯定有一些对应性的反思,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就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游戏制度,在这个制度里大家的关系都特别单一,利益变得最重要。体制是一个很小的事,对艺术体制的反思其实也不需要,因为你打开的是另外一个空间,体制内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些在时空里边显得特别微不足道。
杨青:2014年你做“庄辉个展”的同时参加了一个群展“不在图像中行动”,展示的并不是作品的结果,作品记录的过程也并不是为了特定的展览而做,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展览。
庄辉:“不在图像中行动”更多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家工作的状态,而不是一堆视觉的产品。我觉得策展人是比较针对展览内部机制的一些问题展开探讨,这个话题恰好和你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艺术机制里的问题有关。

《祁连山系-15》 庄辉 单路视频、彩色、有声 10分 2016 年
杨青:参加“不在图像中行动”这个展览也包含了针对体制的思考吗?
庄辉:我做完了“庄辉个展”才接收到这个展览的邀请,我感觉自己已经把“体制”这个事想明白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障碍。策展人看到我的“庄辉个展”之后就想把它放到“不在图像中行动”里,《安西风口》则是单独为这个展览做的。如果不是参与“不在图像中行动”,《安西风口》这件作品我就可能放在“祁连山系”展览里边了。

“庄辉:祁连山系”展览现场
(六)
杨青:《安西风口》里拍摄的图像每两个小时自动回传到邮箱,拍摄是完全不控制的,而《祁连山08》的录像是由红外线感应拍摄的,只有周围出现动静的时候才被激活,两个展览里的这两件作品都有某种不去控制作品发生的感觉。
庄辉:对,而且有一点,它的空间跟我们有一种隐隐的联系,比如两个作品都是把记录的仪器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跟你有关系,但也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自己拍了,发过来到邮箱里边。
杨青:我也感觉到这里面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不在图像中行动”开启了另一种展览的视角,即呈现那些不可记录或者是无需被视觉展示的东西,这些会不会是跟“祁连山系”又有一个前后的逻辑关系?真正的东西并不在展厅里发生,而我们像一个滞后的二手资料的接收者,该怎么看这种展览的表达?
庄辉:我只能说说我的初步想法。既然我的前提是希望把另外一个空间给显现出来,我就在想如何显现的视觉方法,“祁连山系”相当于我把另外一个空间的东西在常青画廊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了,我更多的是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个另外的空间的存在,而不是单单看我的作品多么的有意思和出彩,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做。
杨青: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了作品而做,也不是为了展览而做?
庄辉:对,我就是为了把那个空间给显现出来。那个无形的空间你总得用视觉传达出来,于是我从无形当中挑了一些有形状的显现,处理得不是特别过分,避免强调作品的完成度,或者是作品本身物质的那个状态会呈现到多么精确的地步。
杨青:你没有去强调作品的完成度,仅仅是因为“祁连山系”是你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抑或这是整个计划当中贯穿的原则?
庄辉:我想这个会有变化。“祁连山系”是这个项目的开始,第一步我觉得空间被显现是重要的,第二步可能根据我做艺术家的个人嗜好,慢慢地个人趣味就会出来了。下一步我会关注自己在祁连山这块地方感受到的另外的视觉经验,或者是个人体会更深刻的一些感官经验等等。以后也许会比较多呈现这些,可能在作品当中关注更多的是语言。
杨青:在“祁连山系”里面还可以看到你以前创作方式的一些延续,最近的像《安西风口》这种不受控制的拍摄,远一点的,例如一楼展厅里的在游荡中拍摄的几千张祁连山图片,经过高度的压缩,这个方式好像在《甲乙丙丁》的那个作品里也有出现。
庄辉:还真的是这样。《甲乙丙丁》那个作品都快消失了,它是1999年的作品,也使用了这种图片压缩的方式,当时是压缩成8厘米×15厘米的照片,模模糊糊有一点形状,没有“祁连山系”的图片压缩得这么极端。前后两个作品相比,前者是父亲,后者是儿子。

《祁连山系-12》 庄辉 石包石、喷气装置等145cm×120cm×55cm 2016年
(七)
杨青:你从2011年就开始去祁连山,一直到今年做个展,在这个当中一定是有大量的素材搜集和创作的,为什么在展出时确定了常青画廊展厅里三个不同楼层的作品层次?
庄辉:这个展览交了一份大家看起来还算满意的答卷,秦思源功不可没。他的策展经验很丰富,工作也特别细致认真,也有国际视野。从2015年10月开始,我请他做策展人着手进行工作讨论,中间有一些小的变化,可是我们一直在保持讨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周讨论两次。这个展览的呈现不是特别具体的作品性很强的表现方式,而是包含了一些空间上的处理。我个人的经验,做展览一般来说要给观众有三个不同的观看阶段,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单调,哪怕是一个绘画的个人展览。就算你没有三个阶段,也要多几个层次让别人去感受和观看,不然就特别单一。正好常青画廊有三个楼层,所以我们就做了对应的空间分配:第一层就是大自然;第二层是我个人在自然当中的投射;第三层是祁连山当地的人怎么看山和画山。
杨青:第三层的壁画很有意思,它提供了一种祁连山人观看山的心理视角。
庄辉:是的,我在祁连山一个庙宇当中发现了很小的壁画片段,是关于佛教里面的故事。我尝试用过油画和丙烯,但是都达不到壁画的墙面产生的那种滋润的感觉。这要归功于旦儿她这几年一直在画色粉画,我拿起来也并不陌生,而且我以前也画过板报,我就用色粉画尝试画了两三张,发现这个正是我要的效果:同样可以留下壁画的线条的痕迹,块面当你处理有两三层厚之后会产生很均匀的感觉,像是涂墙的质感,并且有纸质的温度在里边。

祁连山系-16 》庄辉 色粉 2016年
如果让我画祁连山,去表达人和山的关系,我可能处理的方法完全是透视学,或者是我们学过的一些视觉的方式来表现。可是当我把壁画画面当中的人移植到我的画面,我也就深刻体会到它为什么可以达到那种山和人的关系,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因,这个原因和他们的想象力无关。
杨青:在当地人眼中,是不是山就等同于自己?
庄辉:对,就是这个原因!比如说现在这里就是一个空山,如果你走累了,就会打开羊皮袄躺着歇一歇,养足精神站起来继续走,渴了喝一捧泉水,饿了带着干粮补给一下,你和山是平行的。山既是山,但也不是山,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和山的关系才可能达到自由穿越的程度。这不是想象力的问题,这种感觉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刚开始我误以为壁画的画师是通过佛教的感觉达到了忘我的状态,然后进入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中,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画师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他与山之间的心理自然而然能够随意穿越。
杨青:这个展览整个展厅的作品更像是一个整体的行为、一场行为的记录,我觉得艺术家在这个空间里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行为给显现出来了。
庄辉: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艺术家回答的,而是应该交由观众讨论。别人都在忙着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都在工作室搞这个那个,而我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有点儿是在瞎转悠,山里边没事游荡游荡,拍点儿照片或者是捡点儿石头回来,你刚刚谈到这个行为是整个的气氛给外界形成的艺术家状态的认知。一个艺术家除了作品以外还是应该给外界带来一些有趣的话题。
杨青:到了祁连山这个阶段,你似乎也仍然在关注个体的存在。
庄辉:我也没有过度关注个体的存在,我只是离开了人群,离开了那种具体的关系。
杨青:在这个山里面是想发现另一个自己吗?
庄辉: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也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里的自己的内心,能跟这个地方贴得更近。更近的话能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能发生好多的事情。比如说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某些东西,消化你身体里面的某些东西,至于日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也并不知道,这个反倒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杨青: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可能性?
庄辉:任它流淌,自由地行走。我既然选择了祁连山这样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是想撒点儿野,放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