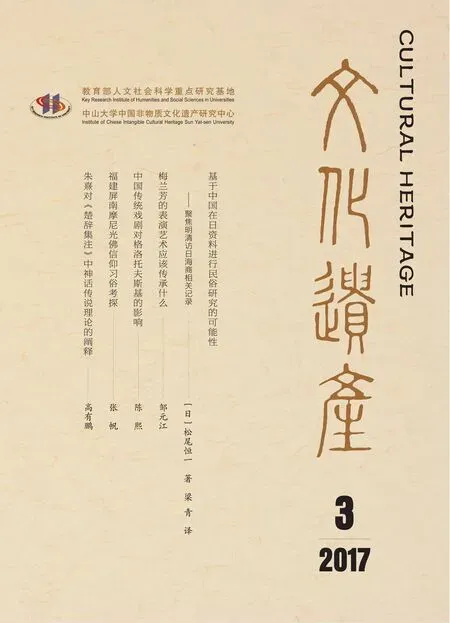福建屏南摩尼光佛信仰习俗考探
张 帆
福建屏南摩尼光佛信仰习俗考探
张 帆
继福建泉州、莆田、福州、霞浦等地系列摩尼教资料发现后,新近在福建省屏南县又发现民间摩尼教科书和三尊被称为“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的神像,当地还生成独特的活态摩尼光佛信仰习俗,周边区域也存在相近的信仰禁忌与习俗,这是摩尼教进入民间社会,在地的衍化与变迁。
屏南 摩尼光佛 信仰习俗
宋以来摩尼教外托道教而存身,明代以来遭严摈,在福建日渐与道坛法事结合,产生以民间道坛仪式为框架,摩尼教教义、神名为内容的清幽仪式。在福建,陆续于泉州、莆田、福州、霞浦等地发现摩尼教神像、石刻、科书及其他文物,新近福建省屏南县降龙村又发现民间带有摩尼教色彩的科书和三尊被村落称为“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的神像。①2015年2月屏南县宣传部副部长张峥嵘、电视台台长李锐提供摩尼光佛相关信息,并与本人共同调查,特此说明并致谢。
该村民间道坛科书中摩尼教科书比重很小,现存仅三本(两种),极可能用于摩尼光佛庆诞仪式。与摩尼教在福建其他区域的传播不同,降龙村除了形成正月初五摩尼光佛庆诞、摔跤嬉戏等民间信仰习俗外,还视摩尼光佛为喜欢恶作剧的孩童佛,其信仰渗入村落及周边区域的民众日常生活,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禁忌与习俗。
一、降龙村与三尊摩尼教神像
降龙村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隶属福建省屏南县寿山乡,东与周宁县毗邻、南与蕉城区(原宁德县)接壤、西北与屏南县棠口乡、双溪镇相邻,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全村现有280人,除一户姓林、一户姓苏外,其余姓韩,为韩姓聚居村。明天顺二年(1458),韩姓先祖财什公迁入降龙村,为开基祖,当时降龙村尚无人烟。二世祖善八公开始兴建宗祠,乾隆年间宗祠遭火灾旋又重建。②(清)韩世明:《高阳韩姓正谱》,光绪三十一年(1905),手抄本。祠堂现设固定神龛供奉韩公、韩母及临水夫人陈靖姑,另有一空龛,每年正月初五安奉村民称之为“闽清佛”(即“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的三尊神像。村落主要民间信仰祀神有五显灵官大帝、临水陈李林三夫人、大圣王③大圣王是猴神信仰,一些地方大圣王的早期身份为临水夫人陈靖姑收妖故事中的丹霞大圣,西游故事深入民间后,附会为齐天大圣孙悟空。、林公④民间传说林公名林亘,在福建省周宁县玛坑乡杉洋村修行,因伏虎而被村民尊为神,立庙祭祀。民国陈赞勋等修《周墩区志》记载“神于宋时升化,肇迹杉洋,清封忠平大王”(《周墩区志》“卷二”,据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0页)。林公在闽东一带广泛奉祀,又常与临水夫人陈靖姑并庙,以杉洋林公宫为林公祖庙。等,水尾封坛祀土主。村落每年最盛大的活动曾是九月廿八“五显”庆诞,村落韩姓道师存留的科仪、戏曲文检中,保存民国时期五显庆诞请戏班的戏单。其次是临水夫人及林公的庆诞活动,清雍正十三年(1735)屏南建县前,降龙村归属古田县管辖,古田临水宫是临水夫人祖庙,每年正月十五临水夫人神诞前,村民必到临水宫请香接火。林公祖庙坐落邻县——周宁县的玛坑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降龙村民每年舆神赴祖庙请香,在一次请香后,全村遭瘟疫,十户半空,由此废弃林公信仰。酬神请戏、请香接火、巡村绕镜以及正月初五摩尼光佛庆诞的摔跤活动,是村民每年主要的信仰习俗。
降龙村韩姓道坛为家族道坛,坛号“寿发堂”,行持闾山派、释教、梨园教、摩尼教四类不同教门的法事*福建民间道坛教派多而杂,闾山派、释教、梨园教均为民间道派,闾山派系民间道教一派,又称闾山教、武教、三奶派等。流行于以福建为中心的南方地区,道师在民间称“尫师”“师公”“法师”等。闾山派的巫教色彩浓厚,以许真君及陈、林、李三夫人为法主神,道坛法事与民众生活关系紧密,以祈福禳灾为主,科仪类别多而丰富。行法时,法师系红裙、吹龙角、执铃刀、鞭麻蛇,与宋人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录》记载“罡捻诀,高声大叫,胡跳汉舞,摇铃撼铎”无二致。梨园教全称“梨园正教”,是流行在闽东北一带以提线傀儡为法事特征的闾山派支派之一。梨园教以戏神田窦郭三元帅(或田窦元帅)为法主神,道师兼傀儡师,既行法事,也提演线儡,以演傀儡为法事科仪组成部分,除了演傀儡外,道师亦可提偶身赴民家做法事(如“包公搜间”,道师提包公偶身做法事)。法事以祈福禳灾为主,科仪多源于闾山派,有遣瘟、保安、延生、保病、保苗、祈雨等。法事过程若演傀儡,则称“戏筵”,不演傀儡称“平筵”。(叶明生:《梨园教,一个揭示古代傀儡与宗教关系的典型例证——以闽东梨园教之法事傀儡戏为例》台湾民俗文化基金会编《国际偶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3月23日版),降龙村韩姓道坛梨园教科书均称“戏筵”。释教又称文教、瑜珈教、金山道等,所用仪轨与经文借用佛教,与密宗关系密切,又借用道家仪轨,形成外道内佛的特色,主要法事为超度正常死亡或“落殇”等意外死亡的幽事,也有祈安、祈雨等醮仪与保安、过关等小法事。。道坛现存明隆庆、崇祯年间科书,至迟应在明末已设立,科法活动延续至1982年最后一位道师韩云助亡过,才告终结,存续时间400余年,可谓渊源深厚,传承久远。道坛现存200多册科仪文检,现由韩云助之子韩乃绥*报道人:降龙村村民韩乃绥,谱名韩仁绥,1947年生,韩姓道坛后人,退休。韩乃绥幼时曾跟随父亲韩云助参与道坛活动及傀儡演出,19岁外出参军、工作,已退休,访谈时间:2015年2月25日。保管,其中有三本(两种)摩尼教科书《贞明开正文科》、《贞明开正奏》,从内容看用于该村每年正月初五摩尼光佛庆诞祈福仪式。
降龙村保存三身与摩尼光佛信仰相关的神像,88岁高龄的村民韩世金(1928-)说:“我做小孩见过有三身,中间正身,边上两个后来塑的。”*报道人:韩世金,男,1927年生,降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2月26日。三尊神像造像各异,遵从民间神位排序传统,以中座为尊,左座次之,右座第三*下文关于造像描述,得到宁德市高级中学美术高级教师阮惠珑先生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第一尊:中座,祀奉于村民韩华清家(见彩页图1):木雕坐像,像与座为整木所雕,白蚁侵食严重。通高47厘米,像高32厘米,头高11.5厘米,前底座高15厘米,背座高20厘米。头身之间用榫连接,头曾掉落,现缠黑胶带,脸部饱满而身形略显削瘦。神像薙发,三道额纹,张目、眼窝较深,高鼻梁、高颧。嘴角上扬,内着常服,外覆法服,左前胸用镮固定,偏袒右肩,宽衣博带,为老僧形象。结跏趺坐,木座似为莲花形,左手持念珠。右手结手印,屈中指、无名指,大拇指横于指上,伸食指、小指。左手持念珠放于左膝上。造像造型饱满,刀法简洁、洗练。像背放置七宝灵符的“佛臟”已开口,封口的木块遗失,神像开光时安放之物亦遗失。背座凿两个抓手之口,方便握取神像,这证明该神像并非固定供奉一处,而是各家轮祀,经常移动搬取。此像饱经香火熏燎,表面墨黑,极可能为明代所刻,故老相传为开基祖迁降龙村时携带而来*报道人:韩荣豹,男,降龙村村民主任,访谈时间:2017年3月29日。。村民韩云远亦有一尊自雕神像,奉祀家中,为仿制品,形貌差异较大,神像木座泥塑,着僧衣,结跏趺座。右手上举,指拈一珠,左手结印放于左膝上,约为清代雕刻。
第二尊:左座,奉祀于村民韩云资家中(见彩页图2):彩塑坐像(底座为原木),通高46厘米,像高34厘米,头高9厘米,前底座高12厘米,背座高21厘米。神像梨形脸,身形饱满,略有肚腩。头略仰,结发髻,系发之条下垂于肩,内着上衣下裳,外袍对襟而结,从残存颜色看,外袍应为红褐色,袍角残存用于装饰的金色五瓣花,下裳为蓝色,宽衣博带,较另两尊造像衣摺更琐碎、繁杂,下着鞋,右手平张,覆于右膝,左手持念珠。左座神像与右座外形接近,但细节差异较大,雕塑技艺水平低于另两尊。村民介绍,该像原系木雕,年久腐坏后重塑,从外形、叩击声、重量等方面判断,为泥质彩塑。
第三尊:右座,奉祀于村民韩云议家中(见彩页图3):木雕坐像,像与座为整木所雕,白蚁侵食严重,外漆部分脱落,脸部饱满而身形略显削瘦。通高44厘米,像高36厘米,头高11厘米,前底座高8厘米,背座高18.5厘米。结发髻,系发之纚下垂于肩,木雕的弧度显示出纚的柔软。内着深衣、右衽,外袍对襟而结,宽衣博带,衣摺简约。右手握拳搭于右膝,左手持念珠,脚着翘头履。造像造型饱满,刀法简洁、洗练。像背“佛臟”开口,开光时放置七宝灵符等物已被取出。背座凿两个抓手之口,方便握取神像。此像与第一尊像相近,亦疑为明代之物。
该村几乎家家在中堂悬挂神榜,书写当地祀神。神榜一般由道师安设,旧例本村道师安神榜,列“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神位(见彩页图4)。外村道师安神榜,不列“摩尼光佛灵相尊公”之位。笔者访谈屏南县其他道师,亦不知道“摩尼光佛灵相尊公”为何神。1982年韩姓道师韩云助去世,道坛传统中断,新写神榜虽沿旧例,但将“摩尼光佛、灵相尊公”列入神榜的已不多见。神榜上“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神名连书,村民可能因此误会为一神,称三尊神像均系“摩尼光佛灵相尊公”。
三尊神像居中一尊着僧衣者无疑为摩尼光佛,也许初刻神像时因摩尼光佛之“佛号”而使匠人对造像产生混融佛像的想象。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记载宋代摩尼光佛神像初传福建的情形:“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摩尼教来华,神名、教义多比附佛教,怀安人(福州城内县邑)李廷裕误称摩尼像为“佛像”,对于不识摩尼教为何物的乡野之民来说,这种误会更易发生,以佛像标准来塑雕摩尼光佛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灵相尊公多有记载,祖籍福建闽清的南宋道士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录》说:“昔苏邻国,有一居士,号曰慕阇……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宋)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灵》卷一“师徒问答”,《中华道藏》第十九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福建省晋江市苏内、溪东村境主宫的摩尼教神像中三幅为“摩尼光佛、都天灵相(又称灵圣公)、秦皎明使(千春公)”。*粘良图:《闽南晋江与闽东霞浦两地明教史迹比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就目前资料所见,福建区域内的“灵相”至少有三种内涵,其一“土地灵相”,降龙村摩尼教科书《贞明开正文科》称“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土地灵相、善神护色、有碍无碍、荷护正法”,土地灵相神阶可能类似土地公,位阶不高,担负守护一方乡土之责。其二霞浦文书中的“护法威灵相”*本文所引霞浦文书,转引自元文琪、陈进国、马小鹤、林悟殊、杨富学诸位先生相关研究文章及霞浦县柏洋乡龚为民先生提供的部份科书、家谱图片,特此说明并致谢。,应该系护法神之属。其三都天灵相,作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泉州梨园戏,传承多个南戏剧目,《王魁》被称为南戏首本,该剧第二出“桂英割”唱词有“望天灵圣相相保庇”*泉州地方戏研究社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四卷《梨园戏(上路)王魁》,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天灵圣相”可能与晋江苏内、溪东村所供奉的“都天灵相”以及摩尼草庵之旁石碑横额上的“都天灵圣”一致,也可能与梨园戏上路派流的输出地温州一带的摩尼教信仰有关。泉州方言“都”为大之意,“都天灵相”即“大天灵相”,这位灵相可能位阶较高,因此在苏内、溪东村境主宫中,序位仅次于摩尼光佛,而高于秦皎明使。秦皎明使在福建各地民间摩尼教科书中较多见,《贞明开正文科》称“末秦皎诸护法,一切降魔众,愿降灭神,保护清净法门”,当为护法之神。
2017年3月降龙村民在屏南县寿山乡白玉村又发现一尊摩尼教造像(见彩页图5),风格及大小与第一尊、第三尊神像类似,应该是同时期之物。降龙村故老相传,财什公迁降龙时,带来文武两尊神像,二世祖乡五公、善八公兄弟因是否建宗祠意见不同,兄长乡五公携武身像迁棠口乡大洋村,其后人又迁回距降龙村4、5公里的白玉村,神像在白玉村内发现,现祀于民家。*报道人:韩荣豹,男,降龙村村民主任,访谈时间:2017年3月29日。神像为木刻,通高“44.8厘米,底座宽27厘米”*韩荣耀、陈孝眷:《屏南降龙:摩尼文化研究又有新发现》,http://www.todaypn.cn/Item/6818.aspx,头戴帽,帽上两条垂绦落胸前,造像内着深衣、右衽,外袍对襟系结,似为短袖,左右袖口飞扬,右手握举胸前,左手握拳置于左膝,左右手心有孔,应该曾握物件。该像与福州浦西福寿宫疑为摩尼佛的造像外形颇有相似之处(见彩页图6),皆为袖口飞扬、手握物件。不同的是,福寿宫造像下身雕铠甲,白玉村造像长袍覆膝,下身为整木,未雕甲冑,手上所持之物已不可考。
晋江草庵附近苏内、东溪村境主宫的摩尼教神像“居中是摩尼光佛,左一为都天灵相,左二为境主公,尽左边画福德正神;右一为秦皎明使,右二为十八真人,尽右边画观音菩萨”,神像以中左右三座为尊,中座摩尼光佛,左座为穿文服的都天灵相,右座为穿武服的秦皎明使“身着甲胄,双手执剑,交叉于胸前”*粘良图:《从田野调看明清时期泉州明教的走向》,《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主二副明显遵循福建多数民间祀神规律,例如临水夫人与黄、杨二将,妈祖与通天眼、顺风耳。二副中也常见一文一武,尤其对外来、不甚了解的神,常塑无名文官、武卫为属神。循此规律,并借鉴泉州苏内、溪东村境主宫所画摩尼教神像,降龙村三尊神像极可能为摩尼光佛及穿文服的灵相尊公、武身的秦皎明使。上文第二尊神像塑造时间明显晚于第一、三尊,可能系乡五公带走神像,后人在较晚的某一时期补塑,白玉村神像可能就是武身的秦皎明使。
二、摩尼光佛庆诞仪式及信仰习俗
摩尼教信仰进入降龙村后,村民以农历正月初五为摩尼光佛神诞,产生由道师行持科仪的庆诞仪式及摔跤习俗,道坛仪式与民间习俗共同构成完整的一年一度摩尼光佛祭祀活动。生于1924年的村民韩云善回忆,自己十多岁时见过庆诞仪式,廿多岁后因社会动乱未再见到过,也就是说大约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庆诞仪式中断,摔跤习俗也随之消失。韩姓道坛末代道师韩云助之子韩乃绥回忆自己6岁左右,曾见父亲行持过摩尼光佛庆诞仪式,其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生于1927年的村民韩世金回忆,摔跤习俗在“文革”前消失。*报道人:韩云善,男,1924年生,降龙村村民;韩世金,男,1927年生,降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2月26日。综上,大致可以认为,摩尼光佛的庆诞仪式与摔跤习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消失,2017年春节期间摔跤习俗已恢复。
(一)摩尼教科书所记载的祭祀仪式
降龙村韩姓道坛保存三本(两种)摩尼教科书:其一《贞明开正文科》,道光十二年(1832)道师韩法真抄本,以下称《道光本》;其二《贞明开正文科》,不著抄写人及抄写时间,内页破损、脱漏较多,内容与《贞明开正文科》大体相同,下文称《残本》;其三《贞明开正奏》,笔迹与《道光本》一致,且有“韩法真亽用”款识,抄写人无疑亦为韩法真。《贞明开正文科》*《道光本》与《残本》同文异版,本文以《贞明开正文科》并称这两个抄本。的内容或韵或白,主要是迎请、赞叹摩尼教诸神。《贞明开正奏》是对摩尼教诸神及地方乡神、前代道师的褒扬、祈求,多处夹杂音译文字。《贞明开正文科》与《贞明开正奏》皆为韩法真使用的科书,极可能系每年正月初五摩尼光佛庆诞科仪,原因如下:
《道光本》页末款识“道光拾贰年十一月初一日吉,明尊科、二时科完毕”,直接说明抄本为“明尊科”“二时科”所用,科文称“专祈福筵内外安宁无碍”,“降魔植福保安道场”,“贞明法院诸佛真人祈禳会上”,《贞明开正奏》称“祈福会上一切圣贤降吉祥”,均说明两种科书用于祈福禳灾清吉道场。科书内容是对诸神的迎请、赞叹与祈求,虽然涉及不同教门诸神,但以明教诸神为尊,请神时以“贞明法院诸佛真人”为首,且将科仪冠以“明尊科”,明显是以明教诸神为主神的仪式。科书还使用10段音译文字,其中2段重复,为“阿弗里持善和,末啰摩尼,佛里瑟德徤□诜嗢持,阿佛里,持善匀,弗里瑟德徤诜难波悉缚难”文内有“末啰摩尼”;第10段音译文字“奥和里持善和末啰摩尼里耶加度师”也有“末啰摩尼”与“加度师”,据马小鹤先生考证“伽路师”通常翻译为圣哉之意*马小鹤:《摩尼教三常、四寂新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待刊。,以上3段音译文字无疑是对摩尼的赞叹。
村民韩云善回忆,仪式在黄昏开始延至上半夜,下半夜由各家拜祭。《道光本》称“今日(夜)仰对上方宝界明尊”,“今日今夜,惠明座前”。《残本》“今夜时,惠明座前”。《道光本》《残本》后半部均称“第三时”,可能援引古代印度及佛教将一昼夜分为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后夜的六时时间观念,韩姓道坛科书有《二时科》《夜三时科》《六时奏》,疏式抄本内有《第三时牒式》《第四时牒式》《第五时牒式》《六时关式》等,均为以时间单位为仪式单元。《贞明开正文科》“第三时”可能是日没时做科所用,《贞明开正奏》末页韩法真补写文字:“上来夜迎贞明法院诸佛真人、合坛列位圣贤光降道场”,据此,仪式行持时间应当是傍晚延续至夜间,与村民韩云善的回忆一致。
从屏南县及邻近古田、周宁、宁德、寿宁、政和等闽东北各县民间教派科书及各类清幽仪式现场考察,道坛仪式往往遵循固定仪程推进,以洒净、(建坛)、请神、(安座)、献供、申愿(读疏、呈奏等)、送神等不同科仪构成“请神-申愿-送神”这一完整仪式架构,在固定架构内,置入不同仪式所诵的不同经咒,各科也会依据不同目的及仪式大小而有增删。在仪式所营构的虚拟世界里,行持者(道师、尫师、僧人、礼生等)借鉴人类社会交往秩序与伦理,展现人神交往仪礼。依据《贞明开正文科》内容,可以初步判断毫地例外地遵循了“请神-申愿-送神”仪式架构,记录了完整仪式过程:《贞明开正文科》前半部(即“明尊科”)为洒净、请神;后半部为颂经咒、拜忏、申愿、送神。具体而言,《贞明开正文科》所记录的仪式过程如下:
1.洒净
仪式先从洒净开始,道师用枝叶沾水喷洒坛场,以此象征涤净日常空间,蠲除不洁不吉因素,使之成为足以供神仙出入的神圣场所。道师口诵:
灭除魔鬼毒难焰,其诸虚妄自然消。借杂金底具押杖,利益童男及童女。发大音声相慰门(《残本》:问),其声猛乱???(《残本》:如雷霆)。魔闻战掉心胆雄,五坑崩塔(笔者:塌)毒山川。民(笔者:明)家因此战得强,遂通善信奏明王,势至便化观音出,直入大明降吉祥。(《道光本》)
接着颂咒,即音译文字为:
阿孚林麻和佛里瑟德徤?弥思佛罗汉嗢持护产祚等绽那嗢持宣读里德徤阿缚阵那度悉丹忽持满陀波引持吥持因那伊伽醢阿而唯悉伴那仡悉?绽阵那愈持纥啰俱吥地罗持?似阿佩耶魔尼呼大浑和里度驮?瑟悉里奥和遮夷旦。(《道光本》)
《贞明开正文科》音译文字“阿孚林……”一段主要功能是洒净,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证实了这个猜想,该抄本开篇奉五佛后,即是“阿孚林”,*本处转引林悟殊《福建霞浦抄本元代天主教赞诗辨释——附:霞浦抄本景教〈吉思呪〉考略》(《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6页)所载《摩尼光佛》抄本图片。从科仪过程看,这条音译文字是作为“洒净真言”使用。在与摩尼教相关的仪式中,两地道坛分别使用同一音译文字作为清、幽两类仪式的洒净真言,说明民间摩尼教科仪、科书并非随意随机,其仪式的持行、科书与仪式前期必不可少的洒净、净坛科法有一定规范性。
2.请神
请神系为道师将各神迎请至坛场。《道光本》详细罗列所请之神:“上来扳迎贞明法院诸真人、合坛列位将帅、师公、吏兵,合场公姐”,道师迎请摩尼教诸神、前代道师,尤其对十天王(科书中称玉皇大帝)、四天大明王、明使等一一称名赞叹迎请:
十天王者梵名阿萨啰沙也,是故道教称为玉皇大帝。
虔恭一心奉请遏素思明使、奈素思明使、那素帝旬思明使、头首大将耶具孚,及悉浑仙末秦皎诸护法。
我今发弘愿,愿此星相轮化,从清静净门,亲见北方佛,北方正主缚逸天王,惟愿渐离宝盖,降临我道场,驱除邪魔,清净坛界。我今发弘愿,此星上(相)轮,化从光明门,亲[见]东方佛,东方正教主弥诃逸天王,惟愿渐离宝盖,降临我佛道场,驱除邪魔悉坛界。我今发弘愿,愿此星上轮,化从大力门,亲见南方佛,南方正教主业啰逸天王,惟愿渐离宝盖,降临我道场,驱除邪魔悉坛界。我今发弘愿,愿此星相轮化从智惠门,亲见西方佛,西方正教主娑婆啰逸天王,惟愿渐离宝界,降临我佛道场,驱除邪魔悉清净坛界。我今发弘愿,愿此星相轮化从中央界,耶俱孚元帅,末秦皎明使,惟愿渐离宝界盖,降临我佛道场,驱除邪魔悉坛界。(《道光本》)
科书迎请四天大明王,分别详细介绍北东南西四大明王,将之与“清静、光明、大力、智惠”对应,还迎请中央界耶俱孚元帅等。
3.申愿
申愿是仪式的核心环节,道师向神上呈正式文书,申明仪式目的,也就是道师将所申之愿,写于纸上,盖法印,成为正式公函,有疏、状奏、牒等不同级别。《道光本》关于申愿的描述非常简略,仅一句“上来一筵,今则道场告结,法事云周,凡人口说无凭,赐有文疏财仪表奉化钱”,道师认为口空所申之愿是无凭无据,没有效力,仪式结束前必须焚化正式“文疏”以及财仪,才能表达对神的敬重,真正达到申愿目的。
降龙村韩姓道坛的另一种摩尼教抄本《贞明开正奏》缺少请神、送神环节,并非独立仪式的科书,“开正奏”也开宗明义说明它是向神敬呈奏文。《贞明开正文科》申愿记载极简,而《贞明开正奏》对于申愿仪式记载非常详细,二抄本内容关系密切,《贞明开正奏》显明是对《贞明开正文科》的补充,是《贞明开正文科》仪式过程专用于申愿的科书。
《贞明开正奏》通篇赞颂诸神、祈求诸神保护,记载申愿各环节,提示性小字有:“奉北斗咒,宣□状子,祈盃、礼塔”。申愿前念“北斗咒”、“宣□状子”即是诵读奏文,科书末页韩法真补写的文字阐述“宣状”意义:“凡情口说无凭,所有情旨恭对诸佛座前,教宣乞蒙朗鉴,情旨宣读已周,所有文状文关,当场宣读,乞垂谛听。”仪式在宣奏后便是“祈杯”,用占卜方式验证道师所申之愿是否得到神的允诺。杯即筶杯,以木、竹、铜、银等材质所制,半月形,凸面为阳,凹面为阴,两只一对。筶杯用于神前投掷,一阴一阳为圣杯,象征神准允所祈之事;两阳为笑杯,有些地方亦以为吉,有些地方认为无效,须重掷;两阴为阴杯,象征神未应所祈之事,需要重新祷告投掷。有些法事,掷一圣即可,有些法事较慎重,要求三、九、十二圣不等,以致道师须长时间投掷。《贞明开正奏》记载道师宣状后,亦需掷筶,获圣杯象征所请诸神应允所呈之状所祈。
在《贞明开正奏》的提示性文字中,祈杯结束,便是礼塔,念诵各种礼塔铭文,《贞明开正奏》礼塔内容:
塔号:顶礼明尊 法聀,顶礼炉登,赦千(忏)救苦,速去阴声,造化天地,速去降阳,明尊贞明电光王佛。
顶礼正具天上,正中、广中、日中、月中,南辰北斗,星辰教主,沙罗王佛。
顶礼崇明圣净、感应威灵,降魔美是□□,有远千灾,惟教主,降魔法师感应驱邪,暘奂大帝,隆相等等……
顶礼临水具化,久济安民,有求感应,无顾不从,敕封顺应夫人,太音等等……
顶礼崇岭地上,寻龙中宫,九天星主,但台圣公,林公师父,无量宝塔。(《贞明开正奏》)
法事结束前,道师礼塔祈神,所拜之塔为“育王塔、观音塔、星辰塔、当境塔、玄帝塔、黄公塔、夫人塔”。韩姓道坛祈福禳灾清吉法事也多有礼塔,如《殄灭三灾九难忏迎百福千祥》记载“宣疏、祈杯、拜塔”,过程与《贞明开正奏》一致。
4.送神
《贞明开正文科》后半部“第三时”,由赞叹、忏悔、送神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明尊、明使、惠明等大部分摩尼教神祇及对村落所供奉的乡神临水夫人、林公等一一称名赞叹。第二部分发露忏悔,祈求“普收我等入明门,永超苦海生死中,圣化神通复本宗。”,夹在抄本中的小字提示为“小字:跪定念忏云,我今忏悔云”,未将忏全文抄出,可能是道师熟知忏文,不再多抄。第三部分简单叙述摩尼降世成神传说:“从真寂下西方拔帝苏怜国,九种现灵祥,末艳氏胸前筵(诞)世无双,十三登正觉,成通大阐扬,化度群生称法王”。最后部分先诵十愿为乡村祝保,然后送神,科文称“再拜拜了香花送,香花送,天乐开间来雍去。步步送,相随孩儿妙渺香(原文如此),礼上通卒,以下为惟孩儿妙妙香通礼,卒陈难舍过。”送神后,宣告庆诞仪式圆满完成。
(二)神像的供奉与摔跤习俗
降龙村村民至今供奉三尊摩尼教神像,日常供奉于村民家中,旧例供于哪家,这一家便须向当年福首*福首主持当年村落祭祀事宜,一般各房轮流充任,每年由几户人负责。交缴若干稻谷,现仍沿旧例,每家每年交15元。近二、三十年来,一般固定供奉于村民韩华清、韩云资、韩云议家中。在村民观念中,三尊神像无大小之别,初一、十五点香供饭,也有村民到他们家中上香拜祭、许愿还愿。*报道人:苏维琴,女,降龙村村民,家中供奉第三尊神像(右像)30余年,访谈时间:2015年2月26日。村民以正月初五为摩尼光佛神诞日,在道坛庆诞仪式阙如的当下,正月初五清晨村民将三尊神像迎请至祠堂公祭。神像出门时,供奉之家的男主人为神像撑伞,众人以香、烛、炮相迎,安放祠堂后供人随意参拜。依旧俗,这一天祠堂地上铺干稻草扎的草垫,无论老幼都可以在草垫其上摔跤、嬉闹,外村客人也会被邀请来摔跤,直至扯碎草垫才告结。俗信以为参与摔跤,能带来一年的好运。当地流传多则传说,其中一条是两位外乡人来做客,村民邀请他们摔跤,其中一人被拉到草垫上推来推去,结果当年发大财;另一个被拉扯很生气,结果一年内发生种种不如意之事,次年他主动参与摔跤,全年顺风顺水。类似的灵验传说,增加了摩尼光佛的神秘性,也增强了民众的信仰心理。
摩尼光佛日常供奉为素供,一茶三酒以及米饭、供菜、水果、花生、冰糖等,旧俗在正月初五还要供奉鸭子形的米粿,道师行持完庆诞仪式后,由村民分带回家,认为是神物,吃了之后可以获得神的保佑。降龙村的素供习俗与晋江苏内村类似,苏内村村民祭供摩尼教诸神时,用素菜、水果、蜜饯,村民称之为“菜佛”。*郭志超:《作为民间信仰的摩尼教》,http://ent.sina.com.cn/x/2007-08-26/13511689761.shtml,2007年。降龙村村民非常信仰摩尼光佛,正月初五,家家必至祠堂拜祭,邻村村民也在这一天前来参拜。也就是说,降龙村是邻近村落摩尼光佛信仰的中心。
三、降龙村及周边区域摩尼光佛信仰的延展
区别于降龙村供奉三尊神像之庄严以及道坛庆诞仪轨之神圣,在降龙村及周边区域,摩尼光佛还以喜欢恶作剧的顽童形象出现在民众日常活动中,由此产生一些生产生活禁忌。这一信仰并非局限于降龙村,而是区域性的,周边地区也存在类似传说与禁忌。
(一)降龙村“闽清佛”信仰禁忌与习俗

对于每年正月初五村民在祠堂为摩尼光佛庆诞摔跤的习俗,村民的解释是“闽清佛是小孩佛,喜欢打闹玩乐”。综合传说与灵验故事,在村民观念中,闽清佛不再和临水夫人、五显大帝一样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个喜欢开玩笑、爱恶作剧的孩童佛,但也能保佑家宅平安、生意兴隆,其神职功能与村里供奉的五显灵官、大圣王、临水夫人等既合一,又有身为“孩童佛”的特点。外村人称其“暴目佛”,生活中常以“暴目佛”指斥好动的孩子,对这尊神的态度又尊敬又嫌弃。
(二)周边区域“万岁佛”信仰
降龙村邻县周宁县咸村镇一带有“万岁佛”“鼓岁佛”信仰,系指村落供奉的儿童神像,信仰禁忌习俗与降龙村类似。咸村镇上坂村神像为三位儿童造像(见彩页图7),村民称其“万岁佛”,宫庙签诗称“茅洋万岁佛”。村民回忆旧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毁,亦为三身儿童坐像,穿古代儿童服装,面目慈祥,表情文静,有点象佛像,现在所供三尊新像执兵器、着战袍,与旧像差异颇大。*报道人:林秉定,男,90岁左右,周宁县咸村镇下板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4月4日。村民已无法说清神的来源,也不了解“茅洋”究竟在何处,村落流传着万岁佛信仰缘起故事:皇帝封神时,万岁佛是小孩,夹在人群中,因为个子矮未受封。所有人封完后,他也求受封,皇帝说:“那就与我一样当个皇帝”,因此称“万岁佛”。*报道人:林美,男,85岁,周宁县咸村镇下坂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4月3日。咸村镇光夏村也供奉一尊儿童神像,村民称其“鼓岁佛”,为手中持小鼓的儿童(见彩页图8),村民认为系从上坂村分灵而来。“鼓岁佛”的命名应与“万岁佛”有关,又因神像持鼓而将“鼓”与“万岁”合称“鼓岁”。两村村民都说万岁佛(鼓岁佛)是小孩,喜欢动手动脚,好恶作剧。和降龙村一样,咸村镇广泛流传孵小鸡、酿酒、做麦芽糖、挑粪、缠麻线时万岁佛捣乱的传说。光夏村村民做麦芽糖时,旧俗须取二只鸡蛋放在锅灶旁边,供鼓岁佛玩耍,以免他捣乱,做不成麦芽糖。*报道人:叶银秀,女,59岁,周宁县咸村镇光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4月3日。当地人生产生活,婚寿吉庆时,与降龙村一样,忌讳来自供奉万岁佛(鼓岁佛)的上板村、光夏村民。认为万岁佛(鼓岁佛)每天清晨会跟随第一个路过宫庙,走出上坂村(光夏村)的村民,四处捣乱。村民已记不清上板村万岁佛生日是五月初五还是七月初七,村里从未有庆诞活动,光夏村的鼓岁佛生日在农历七月,村民延请道师在七月择日打清醮。从上坂村到光夏村,万岁佛成为鼓岁佛,神像从三尊儿童,变成一尊手持小鼓的儿童,如果两村之神存在分炉关系,它们的传承应当较为久远。
周宁县咸村镇万岁佛(鼓岁佛)的捣乱、灵验传说及禁忌,与屏南县降龙村闽清佛属于同一种信仰。两地民间对于摩尼光佛的命名也有共同的规律,本村人用敬称,外村人用鄙称。降龙村民称“闽清佛”,外村人称“[bmu]佛”,意为“暴目佛”或“白目佛”;咸村镇上坂村称“万岁佛”、光夏村称“鼓岁佛”,外村人称“大目佛”“大目[k]”。“闽清佛”是一个不带情感色彩的命名,“万岁佛”是个崇敬的命名;外村人所称“暴目”“大目”是大眼、突眼之意,是民间社会对高鼻突眼外来人种的称名,晋江民间称摩尼光佛为“番仔佛”*粘良图:《闽南晋江与闽东霞浦两地明教史迹比较》“东石玉井蔡氏开设船行商号,通商台湾、南洋,听说摩尼光佛是‘番仔佛’”,《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福建方言以“番”称呼外国,如外国银币称“番银”,外国人称“番仔”。“暴目佛”“大目[k]”“番仔佛”无疑是福建民间对摩尼光佛这一外国神的命名。以外貌特征称呼摩尼光佛,带着私下命名的随意与不敬意味,而咸村镇所称“大目[k]”中的“[k]”在方言中有鄙称之意,“[k]”与“大目”并用,鄙视色彩略显浓厚。咸村镇亦有视“大目[k]”为恶鬼,用来吓唬哭闹的孩子,村民也以“大目[k]”斥责或指称爱捣乱的孩子。*报道人:孙徐菊,女,1928年生,周宁县咸村镇村宝坑村村民,访谈时间2015年4月3日。。与降龙村对摩尼光佛的崇敬不同,作为奉祀神像的本村人,上板村村民对万岁佛敬而远之,虽然有庙专祀,旧例无人上供,以上莫不表现出民众对这种信仰又敬又畏的心理,可能与中国历史上摩尼教数度遭禁,信仰者、传播者莫不隐秘行事有关。何以屏南县降龙村的摩尼光佛神像是成年人,输入传说是孩童,信仰禁忌指向孩童好动好恶剧的个性?多种文献记载摩尼四岁追随父亲修行,十三岁获启示,霞浦文书《吉祥道场门书》称“四岁出家,十三岁成道降摩,天人稽首太上摩尼光佛。”*本文所引霞浦文书,转引自元文琪、陈进国、马小鹤、林悟殊、杨富学等先生相关研究文章及霞浦县柏洋乡龚为民先生提供的部份科书、家谱图片,特此说明并致谢。福建地方摩尼教文献中,“四岁出家”成为一个关键词,降龙村视摩尼光佛为孩童也许是对摩尼四岁出家的呼应和信仰的衍化延伸。
四、相关讨论
摩尼教在唐代借回鹘之力,由国家推行得以广泛传播,会昌法难时,受严厉打击,呼禄法师到福建福清、福州、泉州一带传教。元明以后摩尼教日渐与民间巫、道、佛教传统结合,转入下层,依附民间道坛发展,何乔元《闽书》所谓“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呪,名师氏,法不甚显云”*(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志”,校点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成为民间道师稻粮谋方式之一,存续至今未歇。屏南为福州十邑之一,与福州、福清属同一文化圈,共同的方言、习俗,为摩尼光佛信仰传入屏南提供了条件。关于摩尼光佛信仰传入屏南降龙村的缘起,村落有两说,一说摩尼光佛信仰源于闽清县,村民因此称“闽清佛”,2013年所修《韩姓宗谱》详细记载这一传说:
先祖德斌*据《高阳韩氏正谱》,韩德斌生于清乾隆丁卯年(1747),寿八十四,追赠“耆宾”,是一位有德年高之人。其孙韩大岸号步云,曾议修家谱未成,留下一些韩氏源流考证,步云曾孙韩世明于清光绪年间修《高阳韩氏正谱》。公于乾隆年间常在闽清一带经商。有一次满载一船货物准备返乡,忽见下游有三位神童坐在一根一米多长的木头上,忽隐忽现的在江中玩水。见其景,先祖觉得十分奇怪,即向天祷告,若是神灵,就请到我村作为神主,为一方黎庶消灾解难保平安。祷毕只见此木头即逆水而上,到船边停下。先祖即带回乡请雕刻师傅把木头刻成三个佛像,尊称为“摩尼光佛灵相尊公”。因是从闽清江中请来的,故又称为“闽清佛。”*降龙村《韩氏宗谱》编委会:《韩氏宗谱·屏南县降龙村财什公脉系》,2013年12月,第77-78页。
基层民众出于崇敬而将自己奉祀之神的来源神异化,是常见现象。摩尼光佛信仰源于闽清江中三位神童的传说也有同样特质,剥离踵事增华的神迹,从“闽清佛”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命名看,降龙村摩尼光佛信仰源头可能在闽清县。从地理位置看,闽清也有可能作为摩尼光佛信仰传播的二传手,闽清县与屏南县相距约80公里,与福州相距约50多公里,位于福州通往屏南的道路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猜测,降龙村村民出于某种因缘将闽清的摩尼光佛信仰携回村庄。但是韩姓先祖的迁徙史,似乎又指向另一种可能,这是降龙村关于摩尼光佛信仰来源的第二种传说:
相传,明天顺二年,韩氏肇基始祖财什公由前墘村迁徙到降龙时,带来了两尊佛像,名曰摩尼光佛灵相尊公,一尊文身,一尊武身。*韩荣耀、陈孝眷:《屏南降龙:摩尼文化研究又有新发现》,http://www.todaypn.cn/Item/6818.aspx.
这一传说仅始于降龙村开基祖财什公,然而财什公所携的摩尼光佛又从何而来?不得而知。降龙村韩氏家谱记载前代先祖神光、神迎二公曾在梨村(位于周宁县礼门乡)分姓,一姓何、一姓韩。然而韩、何二姓家谱对始祖入闽、传承脉络记载不甚一致。清光绪年间降龙村韩世明所修《高阳韩姓正谱》记载了韩姓先祖一段不太合常理的迁徙:韩姓于宋代入闽,栖于福州乌石山,“直至神光、神迎二公,志奋功名……一则官拜漳州刺史,一则官授监粮司库。历久不便,因此遂辞。”*(清)韩世明修:《高阳韩姓正谱》“考疑”,光绪三十一年(1905),手抄本。此后兄弟二人不断搬迁,先到河阳(据称在周宁县,周宁县查无此地名),置产业、建庐舍。“未几,复迁于古之长溪县,即今之宁德辖地名咸村,注下赀用白镪、黄麻,购得汤、李二家,买成咸、渺两处。伐其大树,辟厥丕基。”不数年,又搬迁到梨村,韩氏兄弟在此分姓,长姓韩、次姓何。明洪武十一年(1378)韩姓一支迁屏南县寿山乡前墘洋尾坮(距梨村6、7公里),明天顺二年(1458),韩姓后人财什公迁降龙村(距前墘洋尾坮相距3、4公里),财什公即降龙村开基祖。梨村祠堂至今并祀韩、何两姓先祖,《高阳韩姓正谱》称“梨村水尾祠堂,现有韩公本相,历年正月迎请”,此俗延续至今,降龙村韩姓后人每年仍到梨村祠堂请香接火。
韩氏兄弟频频迁徙的蹊跷之处在于:其一从闽南繁华大邑漳州迁往闽东崇山峻岭之间的小村落,周宁县山高路险,历史以来较少受官府辖制,晚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才建县;其二短时间内频繁迁徙,刚刚建房置业又很快搬迁;其三最后落脚梨村,兄弟分姓,一姓韩、一姓何,兄长将郡望“南阳郡”改为“高阳郡”,“长则易郡,次则易姓”。兄弟二人何以逃命般地迁徙?何以要分姓、改郡?家谱记载的原因是“官漳州刺史,后任江州刺史,弃官逃粮焉,迁居梨村。”“古老云:韩、何二公,因失粮逃难”。*(清)韩世明修:《高阳韩姓正谱》“附记”及神光公祖图。唐代漳州设刺史,宋代设知府,没有刺史一职,“弃官逃粮”“失粮逃难”之说,语焉不详,颇为含混难解。
降龙村韩姓前代家谱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被烧失传,村里仅存草谱,光绪年间修谱人韩世明担心草谱抄自何姓,对之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何家古无正谱,不过在后慕(募)集而成,故彼村言他村之谱不实,他支言许支之谱无稽。”*(清)韩世明修:《高阳韩姓正谱》“考疑”。因此修谱时,他不用以上两种成谱,而采用自己曾祖步云公考稽之事,撰写《高阳韩姓正谱》。修谱人的态度说明何谱、草谱甚至光绪年的韩谱恐均非信史,仅凭家谱难以解决疑问,也难以证实猜想。韩世明同时也在家谱《考疑》一文罗列何姓谱系及迁徙路径:始祖递公为大唐至德大夫-第六代震、辉、炤兄弟三人“俱住与河洋”-第八代调馆“住在咸、渺”-第十代神聚、神光、神迎三兄弟-第十一代文达“居梨村”。
两姓家谱关于时代、传承脉络、迁徙人的记载差异甚大,但迁徙路径却一致,都是先迁河洋,再迁咸村、里渺(现名“川中”),最后到达梨村。《高阳韩姓正谱》记载韩姓先人到达咸村及川中村*川中、上坂、外表三村均属咸村镇管辖。川中村古名里渺,又称里表,与上板村相距不到2公里;外表村旧名外渺,与上坂村相距约7公里,与川中村(即里渺)相距约5公里。外表村以林姓为主,因此韩姓家谱所说“咸、渺”中的“渺”更可能指原称为“里渺”的川中村,而非相距较远的外渺村。,曾买下汤、李两家产业。汤、李二姓很早便分别迁入川中村、咸村,唐宣宗大中年间,进士汤耳迁居川中。汤姓至今仍为川中村主姓,李姓后人不繁,但咸村至今仍存李姓住户。因此韩姓先祖曾迁入咸村、川中一带的记载应该较为可信。
梨村、前墘两地均无摩尼光佛信仰,但是咸村镇一带却有与降龙村同样的“万岁佛”信仰。降龙村摩尼光佛信仰输入传说之一,以三位儿童为主角,神像却是成年男子,咸村镇上坂、光夏两村神像依然为儿童。两地信仰禁忌与习俗何以雷同?究其渊源,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地缘。降龙村虽属屏南县管辖,但与宁德县霍童镇交通便利,村民常到霍童一带打工、经商,霍童与咸村曾同属宁德县管辖,相距仅10公里左右,地域相近、方言同音。问题是仅降龙及咸村上坂、光夏两村有祀神,而周边村落尚未见祀神。其二可能与韩姓先祖频繁迁徙中,曾在咸村短暂停留有关,但韩姓居住时间更长的梨村、前墘也未见祀神。
在降龙村,摩尼光佛的信仰流传较为隐讳,一是神像不公开供奉于宫庙,而是供奉于民家,每年仅正月初五迎请至祠堂拜祭。二是神榜、科书之外,未见称“摩尼光佛”,民众称“闽清佛”“暴目佛”,对之又敬又畏。三是两种科书的请神、送神辞,对区域内供奉或未供奉诸神直接称呼谒请,如“顶礼临水具化、久济安民、有求感应、无顾不从、敕封顺应(懿)夫人”“林公师父”等,但是对于“摩尼光佛”,未直接称名谒请,而是含糊以“贞明法院诸真人”统括,道坛其他科书也未提及摩尼光佛。四是清光绪年间所修《高阳韩姓正谱》中《灵坛地界记》详细记载村落宗祠、神庙及戏台、亭、桥、楼、路情况,也记载祖公、祖婆,五显帝,陈林李三夫人及其神班黄杨二将、三十六宫婆姐、虎马将军等大小神神像初刻及重塑时间、祭祀情况,还有土主祭典等,巨细无遗,却无一字提及“摩尼光佛、灵相尊公”神像及祭祀情况。降龙村摩尼光佛信仰的隐讳与韩氏兄弟的频繁搬迁是否有关?与降龙村开基祖财什公的迁居是否有关?咸村镇“万岁佛”信仰与韩氏兄弟的停留是否有关?咸村镇视万岁佛为鬼,对之又敬又畏,与摩尼教屡屡被禁、被取缔是否有关?以上问题尚待更多资料才能厘清。
屏南摩尼光佛信仰是福建摩尼教孓遗之一,与福州、霞浦、泉州等地摩尼教信仰息息相关,与霞浦摩尼教关系尤其密切,同样都依托于民间道坛而得以保存,两地科书紧密关联,仪式也都呈现出道坛仪式为表、摩尼教义为里的特征,在宣念摩尼教教义、咒语,对摩尼教神诸神称名赞叹的同时,也掺入佛、道、民间信仰神及相关经咒。在教主或神职人物的祭祀活动中,有职业仪式执行者行持庆诞仪式。霞浦县上万村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林瞪诞日前后,林氏宗族有盛大的祭祀活动,将林瞪塑像迎请到林氏宗祠,并有演戏酬神、福首拜谱、移交文物等仪式。与霞浦等地摩尼教信仰不同的是,屏南摩尼教不仅仅依存于民间道坛,对摩尼光佛的信仰也不仅仅停留于许愿还愿、上香上供以及庆诞祭祀,这一信仰还向民众日常生活延展,衍生出摩尼光佛作为孩童佛的信仰,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相应禁忌与习俗,流传至今。这是一项独特的、沉潜入民间社会肌理的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在方言中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指称意义的词——用“暴目佛”“大目[k]”指称顽童,这是外来者对在地如鱼得水式的衍变,也是在地者对外来者开放无间的接纳,是摩尼教中国化及长期流播民间社会,由圣而俗,从而深度在地化、民间化的难得范例。
[责任编辑]刘晓春
张帆(1972-),女,福建周宁人,文学硕士,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福建 福州,350001)
K890
A
1674-0890(2017)03-08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