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莫迪亚诺相遇的黄昏
○徐 江
与莫迪亚诺相遇的黄昏
○徐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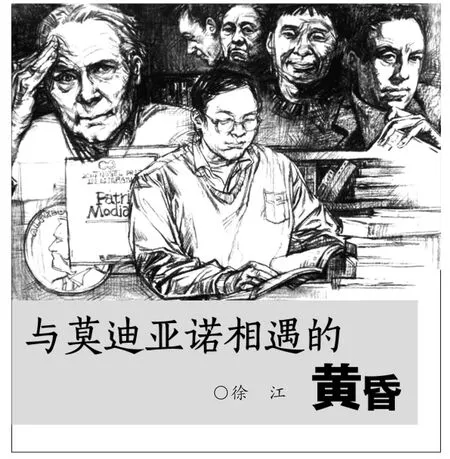
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读者的相遇,是存在着某种缘分的。正如一个作者与一个题材之间,存在着某种缘分。而一个作者,与另一作为其读者的作者,他们精神之间的相遇,也是有着种种巧合与机缘的。
我在大学课堂和同学面前,从未听到过阿尔贝·加缪的名字,但有一次我从北京的铁狮子坟步行至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去买老师推荐的卡夫卡小说,一眼瞅见了郭宏安译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加缪不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的巨擘,他也曾是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竭力推荐当时并不出名的卡夫卡小说的人。多年以后,卡夫卡以他在中国的盛名,把陌生的加缪作品引到了我这个年轻的亚洲读者面前。而当时,无论是对卡夫卡还是加缪,抑或二者作品间的渊源,我都一无所知。吸引我的是《局外人》开头的译文: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在一个灿烂的冬日上午,无知的我囊中羞涩,正在为要不要买下加缪的这本小说集而犯愁——多年后,我开始翻阅莫迪亚诺《暗店街》的一个译本,译文一上来的开头是:“我什么也不是”,便可引来描述我当时的心境。我最后掏钱买下了那本书,它的作者,将是我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导师之一,一个对我造成的影响比鲁迅更深刻的作家。
类似的温馨巧合尚有:在我当年坐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期刊室里,贪婪地试图从《外国文学动态》或其他评介法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刊物中,捕捞关于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小说的译介,甚至只言片语时,我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会看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记者面前对莫氏小说作出如此评语——“他就是当代的普鲁斯特”。我为这句话激赏。因为基于对莫迪亚诺的阅读,我认为莫迪亚诺小说的所有主人公,都不是多么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家的写作志不在此,与其说他是想塑造一个个人物,不如说他是在呈现人类在险恶环境下的精神状态、逃无可逃的宿命,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来自弱者的不甘和追问”。在过去的文学中,这些工作是小说家通过成功塑造人物,进而让研究者探索寓意来完成的,而莫迪亚诺尽可能地撇开了这些,他让人物和寓意直接合成了一个有机体。
我个人认为莫迪亚诺是人类自有文学以来,四位不以具体的人物作为描写目标的小说家之一。另外的三位分别是:
1.普鲁斯特——他所描写的目标是人类的记忆与时间。人物不过是他完成任务的道具。
2.塞林格——他所描写的目标是人类在由少年期转入青年期之际的敏感状态。塞林格小说的每个主人公(除了《献给艾斯美》里面的那个讲述者),都可以换成同样的名字,只不过转变和早熟发生的时间节点不同而已。
3.索尔仁尼琴——他晚年所著的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史诗性小说《红轮》,所描写的目标竟是“苏维埃治下的近百年”!
这三位小说家中,直接影响了莫迪亚诺小说叙事的就是普鲁斯特。曾几何时,大家也许嘲笑过那些模仿《百年孤独》开头的中国作家。但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打开莫迪亚诺刚被翻译过来的《夜的草》时,这样的开头令我了然了:
“可我不是在做梦呀。有时候,不经意间,我听见自己在大街上说这句话,可声音却像是从别人的嘴里发出来的。有些失真的声音。一些名字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一些面孔,一些细节……”
是啊,一个作者,一生中又能有几次成功避开那些撞击过他的伟大名著的魅影呢?而关于普鲁斯特,我的另一个温馨的回忆是在高三:在中学借阅的一份杂志上,我读到关于他写作《追忆流水年华》(那篇文章是这么翻译书名的)的介绍,那些缩微了的小说梗概,那个犹太哮喘病人用一部书对抗巴尔扎克整个《人间喜剧》王国的传奇故事,开启了我对普鲁斯特小说译本近十年的渴慕。而又过了这些年,我神奇地发现,我在人生不同时段迷恋的那些精神碎片,原来都出自于同一个大陆板块!
不久前,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被问及,怎么看村上春树落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当时一个关联性疑问曾在我的脑际一闪:“如果我没有在村上春树的作品被引进中国之前接触莫迪亚诺的作品,我会那么轻易地接受村上春树的小说吗?”
村上春树与莫迪亚诺近似的一点便是,他俩都擅长氛围营造和对心理状况的呈现,相对忽视戏剧性情节的描写。莫迪亚诺文笔的跳跃性更大,有时类似新浪潮电影场景的切换。而村上春树,更像是某个深深植根于青春的都市歌手,为回不去的往昔或偶尔发现的历史黑洞忧伤、迷惘和战栗。我同样喜欢村上春树,一来《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大学毕业前后的时代背景,与我个人的经历颇为吻合,渡边君也和我一样,都是赫尔曼·黑塞作品的爱好者;二来我知道《舞!舞!舞!》的灵感里显然有着来自诗歌《沉重的时刻》的滋养:
此刻有谁在世上无缘无故哭,哭着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无缘无故笑,笑着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无缘无故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无缘无故死,望着我。
在我看来,一个关于莫迪亚诺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或者他和村上春树、莫言三者究竟谁更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远远比不上讨论“过往三十多年来,几代中国读者与作者,通过当代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探求心灵之旅的通道”来得更靠近文学的本质,更贴近当代知识分子挣扎的心灵,同时也更接汉语文学生长的地气。
(插图:杨雪琳)

当“心灵”成为关键词时,文学的本质才得以拨开迷雾。获奖是什么?诺贝尔奖又是什么?作者用“远远比不上”来使没有意义的讨论成为侧面烘托的载体,目的就是无限强调心灵对于文学、知识分子及汉语的重要性。用文学的本质来对抗功利的写作目的,大约就是徐江写作这篇读书笔记的最终用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