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州评弹传承体系的构建
刘晓海 王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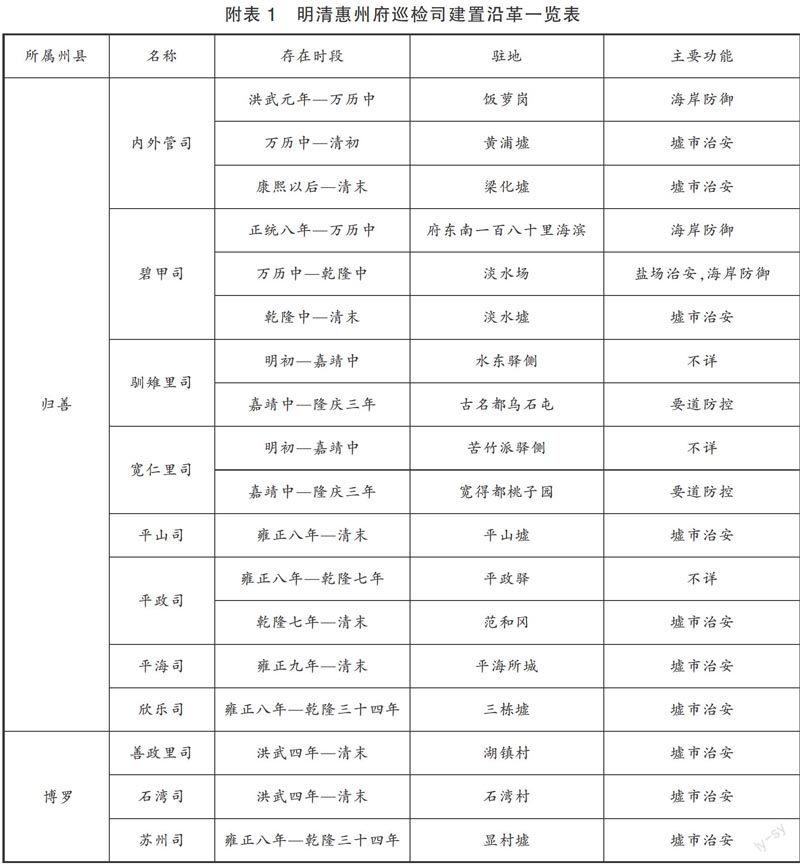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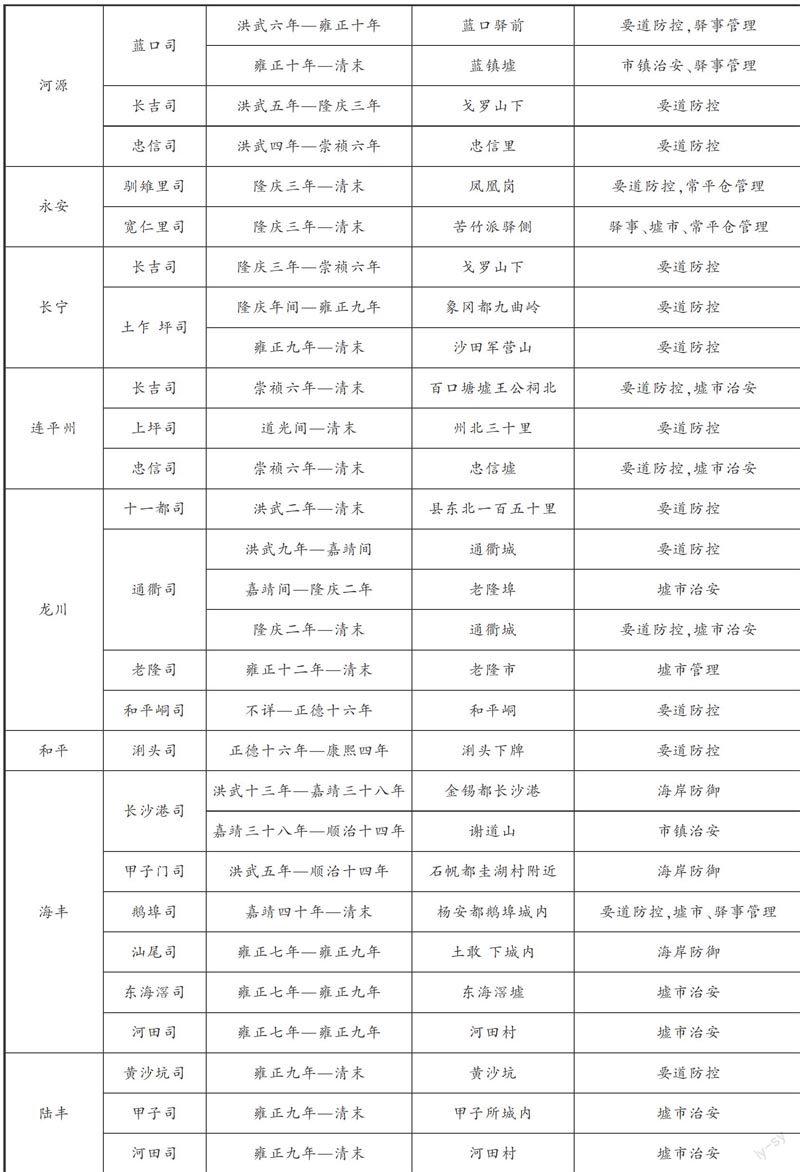
[摘要]评弹传承自古有之,但评弹传承的规范化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光裕社重建后才真正开始。光裕社在学艺对象、学艺流程、师承谱系、师徒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对评弹传承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传承的规范化推动了评弹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伴随着社会变迁,光裕社对于评弹传承的限制性规定越来越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最终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促成学艺者性别、地域等限制的取消,从而促使评弹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苏州评弹;光裕社;传承
中图分类号:I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1-0021-06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的合称,流行于江南区域,是吴语区最为知名的曲艺形式。苏州评弹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留存与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传承与创新。自晚清以来,伴随着江南地区剧烈的社会变动,苏州评弹艺人不断对传承体系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适,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使得艺术的传承从未中断。对近代苏州评弹传承体系建构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曲艺形式长期存在的内在因素。
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评弹传承概况
跟师学习是评弹自产生以来便采用的传承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师承关系及传承方式自古以来就是明确而规范的。明末的柳敬亭被视为说书业的祖师,其地位受到苏州评弹、扬州评话等多门曲艺界的认可。柳敬亭因说书得到士大夫阶层赏识,在他们的文献中保留了一些有关他说书情况的记载。柳敬亭最初并没有跟师学艺的经历,他自称“吾无师也”。①在江南地区演出的时候,因为得到了松江人莫后光在说书技艺上的指点,遂称“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②这一时期,说书并没有成为较为正式的行业,内部也没有一系列的规范,没有任何同业组织以凝聚力量,故其具体传承的历史亦付之阙如。
苏州评弹最早的艺人是乾隆年间活跃于书台的王周士。后辈艺人常常讲述他为乾隆演出的“御前弹唱”故事。王周士之所以能够得到后辈评弹艺人的追棒与记录,不仅是因为他有着为皇帝演出的故事,还因为他首创了评弹艺人的同业公会——光裕社。③但是,从传承的角度而言,王周士所生活的清中期,评弹业内的传承情况仍然不明确。人们普遍认为王周士所说书目为《落金扇》,“但他的《落金扇》从何而来,又传给谁,都不详。后来,传唱弹词《落金扇》的,知名的,最早为清咸丰年间的艺人,其间是否有传承关系,不明”。④
评弹传承体系真正确立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如飞重建光裕社之时。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在清军的打击之下撤离苏州,清政府在重新获得江南地区控制权后,开始进行社会重建。评弹艺人马如飞等从苏州评弹行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号召苏州评弹艺人合力重建在战火中毁坏的光裕社。“同治四年(1865),(光裕)公所司事马如飞、许殿华、姚士章、赵湘洲、王石泉等人募捐把小日晖桥南堍的关帝庙修理一下,暂作公所”。①光裕社作为传统时代产生的行会组织,对外一致压制非行会成员,对内则约束行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期保证最大限度地保护行会成员的利益。光裕社作为多数评弹艺人,特别是著名评弹艺人集体参与的行会组织,将苏州这一市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控制苏州这一中心,光裕社进而把控了评弹行业的主流。
二、光裕社对评弹传承体系的建构
光裕社在马如飞重建之后不断发展、完善,在行会制度建设方面,曾出台《光裕公所改良章程》等行会规章。在《光裕公所改良章程》中,光裕社对于评弹的传承有着较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首先,是对传艺的对象有着明确的限制。章程第一条规定“凡同业勿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2}光裕社作为男性评弹艺人的行业组织,为了维护男性评弹艺人的利益,极力压制女性艺人,从而达到排斥异性竞争的目的;男女拼档或传授女徒容易产生流言蜚语,也是光裕社反对女艺人的原因之一。组织艺人重建光裕社的马如飞,十分反对女性从事评弹行业,他曾表示:“所可耻者,夫妻无五伦之义,雌雄有双档之称。同一谋生,何必命妻女出乖露丑,同一糊口,何必累儿孙蒙耻含羞。窃思随园女弟子,儒林间此日犹评野史,女先生市井中至今亦诮。所虑者持口角而争雄,逞心思而斗巧,登台以秽语诙谐,先伤雅道,到处则大言狂妄,易惹祸殃。”{3}马如飞认为走官塘、跑码头抛头露面的评弹行业,不能让应该恪守妇道的女性参与,即使艺人自己的女儿也不可以继承父辈艺术。
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为了整饬社会风俗,发布禁令禁淫词、禁淫书、禁女性入茶馆,他认为“即使地方日渐饶裕,而四民各有专业,亦当勿荒于嬉;至因此而演唱淫词,男女杂沓,伤风败俗,更无论已”。{4}丁日昌的禁演政令使得评弹艺人难以为生,后来经过苏州地方士人及马如飞的请求,丁日昌才允许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书目演出。但是禁止女性进入茶馆这一政令并没有取消,女性评弹艺人自然也不能进入茶馆演出,这使得评弹女艺人失去了苏州等地的“生存空间”,只得进入禁令难以染指的上海租界。此时的光裕社利用丁日昌禁令,掌握了评弹行业发展的主流,将女性成功排除出评弹传承体系。
光裕社在限制评弹传承对象的同时,不断试图构建评弹传承的文化谱系,其最为明显的便是评弹行业共同的祖师信仰的确立。传统时代的尊祖思想在很多较为成熟的行业均有所体现,绝大多数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寻找一位行业祖师,作为行业从業人员形成业缘联系的基础。苏州作为明清时代东南都会,社会经济高度繁荣,许多行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行业神即祖师信仰十分普遍。这种工商行业的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评弹行业。在评弹行业之中,光裕社很早便确立了“三皇祖师”的信仰,但是对于这一行业祖师的实际身份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从众说不一到归为同一的漫长过程,最终确立的评弹行业祖师是吴泰伯,吴泰伯的画像或牌位在学徒学艺的重要节点都会出现。
为了将传承掌控在行会组织手中,光裕社对具体传承过程及师徒关系也有着一系列的规定。首先在师徒关系构建方面,光裕社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拜师仪式是师徒关系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马如飞的父亲马春帆所作弹词开篇《要孩儿》中,以简明的唱词描述了拜师仪式,“香一柱,烛一双,封贽仪,写关书。至诚问道先生处,终身受教浑如父。四拜趋奉总是师,南词评话随人志”,{1}除了开篇中所提到的香烛等仪式工具外,评弹祖师的画像也是拜师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严肃的拜师仪式,往往在初入评弹界的学子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天跟师学艺的张君谋,因为听书位置与书场听客发生争吵,师父王柏荫站起来问他:“倷阿让?!”此时,张君谋的脑中想到的是“拜师时在红毡毯上叩过头”,听师父这样一问便害怕了,马上退让。{2}
师父传授评弹技艺往往要收取数量可观的拜师金,光裕社并没有明确规定拜师金的数额,往往根据师父自身的艺术水平而定,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行业标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唐耿良向评话名家唐再良拜师学艺时,拜师金的行情大体如下:“拜先生要付一笔拜师金,当时的行情是100块银元,打八折也要80元。请一席酒6元,师母的盘礼3元,介绍人荐送费2元。跟先生出码头的川资、饭金、早晨点心零用都得花钱。”{3}在学艺期间,一般学生都会跟随老师生活,但是各种花销需要自己承担。不仅如此,老师的生活起居均要求学生予以照顾,徐云志在跟随夏莲生学艺期间,如“扫地、倒便壶、买小菜等事都要做,而饭却要回家去吃”。{4}
光裕社对于艺徒学艺是否能够出师也有着自己的审定标准。按照光裕社的规定,学徒正式登台说书前需经过“出道”的程序:
出道最初有三个步骤,即出茶道、出道、出大道。出茶道比较简单,艺徒由业师带到茶会上,介绍与同道认识,为同道付一次合堂茶资就完事。艺徒出了茶道,便有资格上茶会,进公所和在苏州演出。这时如果艺徒的贽金尚未付清,就得与业师拼档演出一个时期,收入归业师,这叫做“树上开花”;之后便可以自行演出,收入归自己。出道比较复杂,必须得到业师的同意,由业师“领”出道,因而要孝敬业师一笔钱(一般要二三桌酒席的代价),并向公所交付出道费七千二百文,然后由业师带领遍谒同道。出道后,公所的小牌上有了名字,就有资格收艺徒和在苏州较大的书场演出。再过若干年,就出大道,办几桌酒请出过大道的人吃,他的名字便从小牌移到大牌上。后来出道和出大道合二为一,统名出道。出道者须摆三桌“关书酒”,请出过道的人吃,并向公所交付一笔出道费,其数目先为10元,后来改为20元,最后改为30元。但对艺人的子弟出道,有优待的规定:艺人自授的,免去“关书酒”,出道费减半;投拜其它同道的,仍摆“关书酒”,但出道费仍然减半。出道后,名字先在公所小牌上,过了三年再移到大牌上,但是不再出钱。大牌和小牌,演出业务是不同的,一般场方请艺人,总是先请登大牌的人,所以名登大牌的人演出业务较好,很少有空档,收入自然也较多了。至于未曾履行出道手续的人,即使他的书艺很好,在听众中声望很高,也只能算作“道童”,在公所里没有地位,既不准收徒也不准在大书场演出。⑤
通过以上这段文字,可见光裕社名下学艺的青年艺人如果希望获得登台演出的资格,付出的代价并不小。虽然出茶道的花销并不高,但演出的地点往往限制在外埠或苏州的小型书场。传统书场演出收入分配,较为普遍实行的是拆账制,即艺人与场方根据书场听客数量,按比例分享营业收入。苏州的大型书场往往一次可容纳一百至两百名客人,如果客满,一天演出收入对艺人来讲便已十分丰厚。而小型书场,特别是乡镇的茶馆书场,往往一次只能容纳十几位听客,艺人演出收入很低。评话艺人唐耿良刚刚出师时,曾去过农村集市的一家小书场说书,第一天日夜两场总共仅有34位客人,而且统统是欠账。⑥对于刚刚出道、艺术上并未成熟的说书人,光裕社和师父在出道时对青年艺人在经济上进行二次盘剥,对青年艺人的发展造成了限制。而行会组织对于出道的要求以及师父收取数目可观的拜师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人群体的规模,很多有志于学习评弹的贫寒子弟,面对这种经济压力只能放弃学艺,或者仅仅满足于在乡镇书场演出。行会在艺人规模上的限制使得评弹行业从业者竞争压力减少,从而间接维护了光裕社艺人的利益。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即使是已经学成出道的艺人,也要尊重自己的授业师傅。《光裕公所改良章程》中对此亦有明确的规定:“凡弟子勿犯师长,生意在附近,勿得任做,以尽师生之礼,违者议罚。”①授业之时,师父是以自身演出书目作为授业内容的,徒弟所学的内容与师父相同,必然会在演出过程中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出于尊师重道以及维护师父利益的考虑,这一规定也无可厚非。1944年,评话名家杨莲青在苏州阊门外的龙园书场说书,而龙园书场对面的雅乐书场为了竞争生意,聘请了杨莲青的学生顾宏伯前来演出,“照道理老师在对面书场做,已经出道的学生应该回避的,可是当时顾宏伯没有遵守行业规矩,与杨莲青成为了‘敌档。当时顾宏伯年富力强,名气正盛,对杨莲青产生不小的压力”,②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使得师徒二人产生矛盾。
除了通过经济手段对学艺者规模加以限制外,光裕社对于传授艺术的内容也进行了约束,从而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门派之别。《光裕公所改良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凡同业各系宗支,勿得越做他书。前事一概不究,迨后不准,犯者重罚”。③评弹艺人演出往往依靠一部长篇书目,一旦被他人偷学,则必然使得竞争加剧,从而影响自己生意。“艺人之间不能互相去其他艺人的书场听书,这是被视为偷艺的不耻行为。说同一部书的人,一般情况下彼此猜忌,不能互相切磋进步。”④正因为此,不同师承的艺徒也不能去轻易向其他艺人学习,“沈俭安的门生绝对不能去听钟笑侬的书,如非是笑侬特许的,否则笑侬可责问”。⑤不同师承谱系之下的艺人之间自然产生了门派之别,即使是说同一书目的艺人,也可能因为所使用书目来源不同而全无交流沟通。
当然,马如飞等光裕社艺人对传艺范围加以限制的同时,也希望评弹艺术水准能够不断提高,以得到官绅等社会主流人士的认可。在《光裕公所改良章程》中,就要求“凡登台演唱或苏地、或他方,宜衬托忠孝,劝人为善,切勿讥诮时事,形容官长,违者议罚”。⑥马如飞之所以有着这样明确的“衬托忠孝、劝人为善”的规定,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势,尤其是丁日昌所力推的整饬风俗的禁令。如果光裕社的艺人肆意违反,则会如同女艺人一样被禁绝,从而失去生计。除了对说书的主题思想加以限制外,马如飞也将前辈及同辈艺人对于评弹艺术规律的经验总结加以记载,从而间接为学艺之人提供了帮助。如马如飞所记述的王周士的《书品》一文,指出评弹演出时应该“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⑦而马如飞所记述的陈瑞庭说书五诀有“理、味、趣、细、技耳。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頤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功夫也”。⑧这些对于评弹艺术规律的总结,对于评弹艺徒对于艺术本体的认识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正是因为晚清光裕社对评弹传承作出了一系列规定,才使得传承体系得以明确。这一体系涵盖了师承关系网络、师徒之间权利与义务、学艺出师的流程、传艺的资质等等。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时期评弹传承体系也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冲击了光裕社所建构的评弹传承体系。
三、民国时期评弹传承体系的变迁
近代以来,上海逐渐发展为远东著名的大都会,在上海的崛起的同时,有“天堂”之称的苏州则相对衰弱了。伴随着苏南人口向上海集聚,评弹也进入了上海大都会,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评弹艺人逐渐以进入上海演出为奋斗目标,“评弹艺人都争来上海露一露面,争一争,把进上海说书看成是前途攸关的大事”。①
以苏州为根据地的光裕社,面对上海快速发展的庞大演出市场,并不能真正掌控。对光裕社社规不满的退社艺人和在苏州受到光裕社排挤的外道艺人,汇集于上海,这些艺人在清末组建了润余社,“无师承转业艺人程鸿飞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成立润余社非但在联系业务上可以摆脱外道接不到大码头的窘境,也可以在艺术上进行探讨和研究,提高艺术水平,与光裕社争衡”。②润余社在演出上与光裕社争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光裕社对于评弹传承体系的规定,最为明显地是突破了光裕社由来已久的门派之别。不同于光裕社各家各派之间互相防范、不准染指他人之书的闭门造车的方式,润余社成立之初,艺人们即互通有无,在书目创作上互相帮助,“润余社的几位创始人,编新书近乎集体创作,根据记载,朱少卿编《张文祥刺马》,是得到郭少梅、程鸿飞、李文彬的帮助,李文彬编《杨乃武与小白菜》,得到郭少梅、程鸿飞、朱少卿的帮助”。③而润余社成立的本身,就给了学艺之人的另外一种选择。拜于润余社名下的艺人,自然不必理会光裕社的种种规章制度,学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成长空间。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艺人群体逐渐庞大,除了润余社之外,还有很多自学成才者走上书台演出评弹,这些人往往被称为“外打进”。面对逐渐扩张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艺人群体,光裕社的规章制度逐渐难以维持,即使光裕社社员也通过各种方式突破社规的限制。“过去光裕社定章:凡无师承者,不准入社行业。故由票友下海,俗称半路上出家之说书人,因无师门可入,不敢贸然隶场登台,免讨没趣,为之彷徨无计。擅说《金台传》之金筱棣生前,以在道中辈份较高,于是大开方便之门,广收挂名艺徒,因有‘通天教主外号。”④金筱棣作为光裕社社员,却利用社规的漏洞吸收“外打进”艺人进入评弹行业。这种“挂名”方式,使得无师承的艺人也能够获得演出资格,评弹传统传承体系“徒必有师”的规矩受到了破坏,光裕社逐渐失去了对评弹传承体系的掌控能力。
在应对润余社不断挑战的同时,最令光裕社难以接受的评弹女艺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新出现在江浙沪的书台之上,使得光裕社更加疲于应付。“女子有天赋的歌喉,而表情又细腻,对于弹唱女儿私情为对象的脚本是再切合不过的,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已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一般捧角朋友更是扩大吹嘘。”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光裕社的王燕语、钱景章、林筱芳等人,携带妻女上台演出以挽救自己的生意,“王燕语便教会了爱人三只开篇,在乌镇上台,当夜就告客满”。⑥虽然演出取得了成功,但因为触犯了光裕社社规,这些与妻女拼档演出的评弹艺人不得不退出光裕社。但是“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传统茶馆书场,依然控制在光裕社手中,对女弹词采取‘关门主义”,⑦没有社团依靠的他们,很难进入光裕社所控制的书场。光裕社为了彻底消除女艺人的威胁,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光裕社“当时就通过了种种关系门路,居然有公事下来,命令将外道所演出的场子中所有的书台全部拆光。当时普余社犹未成立,牌子上只挂‘南方乾坤弹词,有些小场子见风使舵,认为乾坤弹词已失势,也有将招牌除下来的”。①面对这种窘境,王燕语、钱景章等艺人申请成立男女评弹艺人共同参与的社团,最终“女艺人说书取得合法地位……唯一受到的限制是‘男女不得拼档弹唱,即可以有男双档、女双档……部分男、女艺人于1935年,在苏州成立了一个新的行会组织——普余社”。②普余社的成立,为女性评弹艺人的演出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保证。而在普余社内部,光裕社禁收女徒的规定再也不能起到约束作用,王燕语、钱景章等人开始收纳女徒,女性开始大规模进入评弹传承体系之中,一批表现卓越的女艺人受到追捧。抗日战争时期,评弹失去了来自行政层面的约束,加之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男女拼档大量出现在书台之上。“1945年抗战胜利后,沪苏两地国民党当局借口同一行业不得有两个團体的规定,勒令光裕、润余、普余三社合并。三社各派代表协商,遵令合并。”③三个行会组织“谈判结果,一切依照光裕社的规定,加上一条‘男女一律平等”。④自此以后,女艺人的地位得到了整个评弹行业的认可,女性拜师学艺乃至女艺人开山立派变得顺理成章,光裕社为评弹传承所设置的性别门槛被彻底打破,评弹的发展局面为之一新。
四、结 语
综上,评弹传承自评弹诞生起便已经存在,但评弹传承的规范化却是在晚清光裕社重建之后。光裕社在师承谱系、师徒之间权利与义务、学艺出师的流程乃至艺术经验等等诸多方面的规定,为评弹传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使得评弹技艺与书目能够不断发展完善。当然,伴随着近代社会的不断变迁,光裕社对于评弹传承限制性规定不能适应艺术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最终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趋于解体。学艺者性别、出身等限制的取消,为之后评弹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迎来最为辉煌的时期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吴启琳)
Abstract: Pingtan inheritance from ancient times, Specification of Pingtan heritage until nineteenth Century 60s, Guangyu guild really began to rebuild. Guangyu guild learned from the object, a process, from the pedigree, mentor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Pingtan heritage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rules. Standardized inheritance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pingtan.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the Guangyu guild was for the restrictive provisions of Pingtan inheritance more and more from two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Finally in twentieth Century 40s a gender and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prompting Pingtan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zhou Pingtan; The Guangyu Guild; Inheri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