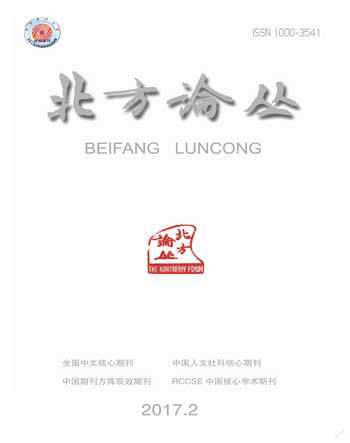金代藏书家叙论
顾文若
[摘要]金统治者重视搜集典藏图书,弘扬文治,努力程度不逊于以往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金朝在官府、学校、寺观之外出现很多藏书家。上自贵族,下至学者、平民,藏书风气很浓,藏书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金代文化教育及出版业的发展。很多文学家族通过收藏图书使文化在子孙辈得以延续和传承,特别是河东南路平阳府,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图书出版的兴盛与藏书风气相辅相成。金代藏书家对保存、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金代;藏书家;图书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83-03
Abstract:Jin Dynasty rulers pay attention to collect books, the effort is not inferior to the former Central Plains Han nationality established feudal dynasty. Except in the official, school, temple , emerged of a lot of bibliophiles. From the aristocracy, down to the scholars, civilians, collection of books is very strong,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in turn promote the Jin culture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Many literary family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so that the culture i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eneration to be extended and heritage, especially the Pingyang became the North engraved book center. The prosperity of book publishing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Jin Dynasty collection of books played a role can not be ignored on the preservation,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Key words:Jin Dynasty;bibliophile;books
金代是北方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取得政权初期便积极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使得其一代艺文,灿然可观。金代的图书出版业非常兴盛,特别是河东南路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出版的繁荣促进图书的流通,也促使藏书的风气炽盛。金朝在官府、学校、寺观之外出现很多藏书家。孔天监《藏书记》形容当时藏书盛况为“家置书楼,人畜文库。”考察金代私人藏书情况,可使我们对金代文化有更生动的具体认识。
一、 金代藏书家类别
(一)贵族藏书家
金初,一些女真贵族中有识之士唯书是好。完颜勖,为金穆宗第五子,金史卷六十六记载其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曾受太宗派遣南下受宋帝降,至军中,金银财宝都不要,载书数车而还。后来,越来越多的女真权贵喜好读书,结交文士。如赵秉文《宝墨堂记》中描绘的参知正事蒲散公,便“平生无所嗜好,独于法书名刻,宝之不啻珠玉,千金购求”[1](p.185)。完颜璹,金世宗之孙,博学有俊才,擅绘画,工书法,尤喜读书,曾读《资治通鉴》三十余遍。起藏书楼为“樗轩”。与赵秉文、杨云翼、雷源、元好问、李汾等文士交善,《归潜志》卷一记载:
密国公璹,字仲宝,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诗,工书,自号樗轩居士……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后因造其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后余适陈,送以二诗,甚佳。又为予先子集作后序。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
贵族女性藏书家耶律氏,漆水郡夫人尤为可贵。据刘长言《大金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墓志銘》记载其“好学问”“藏书万卷”[2](p.182)。并且采用“部居分别”的方式收藏,便于查找。
(二)官吏及文士藏书家
元好问祖辈几代读书积文,家学渊源深远,富于藏书。后来在战乱中丧失大半,《遗山集》卷三十七《故物谱》详细记载其家族文物字画和书籍的收藏情况。雷渊至宁元年(1213年)考中词赋进士甲科,调任泾州录事。后因牵连入狱,出狱后改官东平,授徐州观察判官。《归潜志》卷一载其好收古人书画与碑刻。刘祖谦,承安五年(1200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右司都事除武胜军节度使、翰林修撰等职。家富藏书,尤多金石遗文,善鉴裁书。《中州集》卷五载其家藏书甚富。一时名士如雷御史渊、李内翰献能、王右司渥皆逰其门。解节亨。程文海《雪楼集》卷十三《东庵书院记》记:“解氏世以儒术起家。历宋金多名进士。家藏书万数千卷。而君于书无不读。”
商衡,历任尚书省令史、监察御史等职。《遗山集》卷三十九《曹南商氏千秋录》载:“性嗜学,藏书数千巻,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捄世之学自名髙者阔略而无所统,纪下者或屑屑于米盐簿书之间。公天资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优为之,茍可以利物则死生祸福不复计,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
张行简,大定十九年(1179年),中词赋科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官至太子太傅。张氏为日照世家大族。黄久约《朝散大夫镇西军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记载:“老犹笃学,手不释卷,儿时所诵,终身不忘。家多藏书,部里完洁,绳头细字,往往手自抄写,观者已倦,而公终日伏纸挥翰而已。”[3](p.1364)
(三)金朝民间藏书家
范仲淹四世孙范季霑。家许昌。聚书3万卷[4](p.669)。宁知微,宿州人,博学识广,《归潜志》卷三载其“尤长于史事。剧谈古今治乱或诸家文章,历历不可穷。援笔为诗文亦敏赡可喜。举经义,连不中。迁居淮阳,与余游二载。家积书万卷,载以行。”曹恒,应州(今山西应县)人。《归潜志》卷三载:“曹恒君章……好收古人书画、器物,蔼然有士君子风。遭乱病殁。有子之谦,擢第。”
张傃,北燕(今河北涿鹿)人。《秋涧集》卷十七《哭张总判并序》记载:“行甫公讳傃……姿蕴藉,好宾客,官至平阳府通判官。诗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者也。家藏书数千卷,后以累落职。”
杨奂之母程氏。杨奂《还山遗稿》(附录)载赵复撰《程夫人墓碑》曰:“夫人姓程氏其先阌乡人故奉天杨府君振之妻,今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奂之母也……家所蔵书数千卷,皆奁具易之……夫人姿淑媛有识,度课诸子读书,必盈约始听休舍,尤善援引故实,因事指诲诸子侍立,至夜分莫敢跛倚。奂自蚤岁缉学,晚为通儒,及再抵燕不变于俗,学而德业益富。”
胡景崧,武安人。元好问《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记载:
公讳景崧……祖益,家累巨万。其父课之读书,涉猎经史,工于书翰,轻财好施,不责报偿。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岁以为常。赵魏闲称积德者,莫不以胡氏为称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从军,载国子监书以归。因之起“万卷堂”,延致儒士,门不绝宾;儒素起宗,实兆于此。后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赠宣武将军。考仲溶,嗜读书,不以世务萦怀[3](pp.2903-2907)。
李夏卿。元好问《顺安县令赵公墓碑》记载,其家“文籍甚富”。县学中藏书不足,妨碍学生学习,有人建议县簿从其家“假借用之,宜无不从。”
吴莘。杨子益《题吴莘老万卷堂》:“随分虀盐不力珍,一堂书史日相亲。五经尚说无痴子,万卷于今见古人。既有邺侯籖满架,更知工部笔如神。阶前兰玉十才子,指日鹓行列缙绅。”[5](p.3073)王术同题诗曰:“好收书史贮新堂,岂羡珠玑夸润屋。文字本为子孙藏,子孙能勤文字熟。撑肠各有五千卷,插架更盈一万轴。” [5](p.3059)
二、金朝藏书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一)对家族文化的兴盛至关重要
金代家族文化十分兴盛,与私人藏书风气关系密切。很多杰出的文学家其父族辈都是爱好读书,有藏书习惯的人。其后代往继承其父祖藏书的传统,成为文士,或走入仕途。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载:“吴希尹。石州人。父永。广蓄书,颜其堂曰‘万卷以为家塾。希尹力学知名当世,大定间登进士第,官至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子章亦举进士,仕至翰林学士,元遗山尝受学焉”。杨奂之所以为“通儒”,为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与其父母喜藏书、善教导有直接关系。
前述藏书家曹恒之子曹之谦,为河汾诸老之一,金末元初文学家、理学家;胡景崧,其孙胡祗遹为元初著名文士,大臣。著有诗文集《紫山大全集》;商衡为曹南世家大族,其孙商挺为元初大臣,文学家,著作有《藏春集》;雷渊子雷膺,入元后出仕,历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西蜀四川按察司参议、陕西五路转运司谘议、承务郎、同知恩州事、监察御史等职; 张行简出身于礼学世家,其祖父张莘卿曾任礼部郎中。其父张暐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礼乐家法为世族仪表。幼时张行简听父亲讲授经史,成人后又经常听父亲讲诵古今,不但喜好藏书,也成为金代著名文士和官员;王天铎子王恽,为元初著名文士,有《秋涧集》传世。
私人藏书通过代际传承,导致家族文化的兴盛。正如王天铎所言:“吾老矣,为子孙计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荣保其爵禄,不知一失足赤吾之族:知富宝其金玉,不知一慢藏已为盗所目也,何若保书之为宝乎!若子若孙由是而之焉,为卿相,为牧守,为善人,为君子,上以致君泽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于是矣。”[6](卷四十一)将读书视为改变人生与家族命运的普遍認知,激发了社会士庶的读书藏书热情。
(二)藏书、读书风气促进了金朝出版业发展
藏书风气的形成和金代出版业发展相互促进。《秋涧集》卷六十《故赵州宁晋县善士荆君墓碣铭》所载金代出版家荆佑事迹很有代表性。荆佑在金末战乱之际,将重要经典版刻藏于墟圹中,乱后悉力补购,随复为完部。有人问荆佑为何这样做,荆佑回答:“经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韵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其为善己多。”荆祐这样的出版家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出版图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牟利,更重要的是使文化传承下去,不致断绝。而他们选择重点保存的《五经》等刻板,是需求量最大的图书。
金宋易代之际,晋南地区受战争创伤较轻,环境相对安定,黄河以北的雕版应刷中心由汴梁转移到山西平阳,平阳成为金代四大刻书中心之首,金平水本的刻书成为后世称道的珍本。
(三)取阅图书技术的发明
名士杨奂《臂僮记中》,载有金代一种新颖、灵巧、实用的“旋转书橱”,作者认为,这一装置胜于书僮,故称之为“臂僮”:
经史揷架,濈濈如蚕,二三僮子,备朝夕检阅,奈何索甲而得乙,语东而应西,能尽如已意耶?夫器利则事善,固也。独无知者乎?方皇皇间,会黄冠宋鲁班志明为子剏圆转书厨,以便观览。其级也三,象三才也;其隙也六,象六虚也。顶末有枢纽,常居其所而不移,象极星也。拟诸体用之妙,则与天行健无异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书,圜而帙之,终日左探右取,循环而无端,既息呼叫之烦,又绝奔走之冗,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过一引臂而已。因命之曰“臂僮”,所谓用力少而见功多也。今而后吾书其完乎
余论
金代藏书风气在金亡后得到延续。晚年的元好问在家乡山西忻州筑野史亭,潜心著书。后移居冠氏。《学东坡移居八首》写道:“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箱。浑浑商宝鬲,垒垒汉铜章。”[5](p.2425)
贾辅的万卷楼,数十年间收藏各类图书数万卷。张柔他精心保存的《金实录》及金朝地方文献,送归史馆,成为元代修《金史》重要史料来源。另外,李冶金亡不仕,晚年买田封龙山下,教授学徒。家中富于藏书。藏书最终留给封龙山书院。
总之,金代藏书家对保存、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滏水集: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梅宁华,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4]明秀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6]王恽.秋涧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还山遗稿:卷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作者系山西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