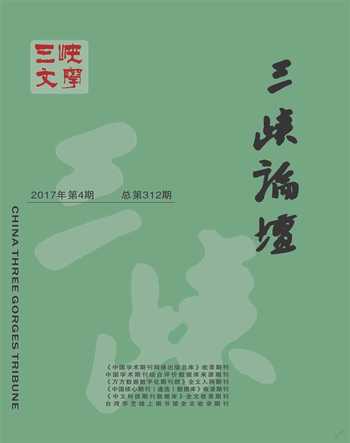清代四川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何绪军 王银田��
摘要: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度减少,为恢复发展四川经济,政府推出移民实川政策。大量湖广地区的移民迁入四川,远离故土,面对陌生环境,他们自发组成移民团体——会馆。会馆自成立开始一直致力于整合湖广移民社会内部,后期又积极展开同土著和其它移民团体交流与融合,同时还和地方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清代中央集权加强与基层社会自我管理机制不断建立与完善的结果。
关键词:
清代;四川;湖广会馆;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K249;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4-0023-08
一、湖广会馆的产生
(一)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社会动荡,人口锐减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连年战争,社会混乱,除了张献忠五次入川,又有残明军抗清,还有三藩之乱等。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定后,才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间的战乱使得四川地区人口损失严重,以致清初“丁户稀若晨星”[1]534如温江县(今四川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2]1b安县(今四川安县)“尽成荒土,鲜有居民。”[3]17a资州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居民“孑遗无几。”[4]637太平(今四川万源市)“经明季兵燹之余,遗黎播迁殆尽。”[5]11b金堂县(今四川金堂县)“遭祸尤惨。兵燹之余,居民靡有孑遗,即间有以土著称者,亦不能尽道先代之轶事,且为数寥寥。”[6]2a严如熤的《三省山内边防论》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居其五。”[7]2917
《中国移民史》推测清初川东地区的土著居民不足5%。[8]77蓝勇教授利用有明确数据统计的几个州县的资料,分析清初四川地区土著居民数量得出平均占比仅为33%。人丁稀少,土地也不多,顺治十八年(1661),全省耕地面积只有118.8万亩,只及万历年间的8.8%。四川地方财政也严重不足,以至于清初需要從外省调拨银两进行支援,显然这对于清朝财政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8]78据上可见,四川地区受到战乱破坏之严重。
四川虽经历了如此重创,但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康熙曾说:“云南四川等处,俱系边疆,殊为紧要。”[9]639清政府认识到四川地位之重要,在应对叛乱时还特意挑选优秀得力的官员前往任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上谕明确提到“四川关系重要,新经恢复,宜简任素有谋勇之人。”[10]417除了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四川地区在经济上也是极富盛名,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明代万历初年,成都平原地区“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11]110就连向称贫瘠的川南荣县,明后期也出现了“井田阡陌,连封数十里”[12]38b的大户。可见明代四川地区的农业面貌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正是由于四川在全国军事、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所以清政府面对已经破败的四川必须采取挽救性措施。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当时四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为了弥补战乱造成的人口巨大损耗,清政府实施了长达近百年的移民实川政策,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二)移民实川
大量移民的涌入,也迫使政府出台相应的应对措施,在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凡外省新旧流民俱编入册籍。”[13]5046到康熙十年(1671)时则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14]2069康熙二十九年(1690),鉴于川省民少而多荒地,凡他省移民在川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14]2069五十一年(1712)议定,嗣后编审人丁按康熙五十年(1711)丁册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5]5025
优惠的政策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移民前往,同时其移民迁出地本身的生存环境也迫使移民迁出,这正是人口学中的“推挽式”假说。 [16]62该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主要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原居住地经济环境趋于恶劣,那么人们便会被排挤,进而被推向另一个有着优惠政策的地区。四川地区在清初时大量湖广人口的迁入,正好是这一模式的最好诠释。
湖广向为我国粮仓,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赞誉,也正是因为如此,引来了大量人口的垦殖,但到后期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突出,且赋税较高,一些贫民生计难以维系基本生活。吴氏入川祖吴玉贤曾说“因田税年年巨整难完,只得弃楚入蜀。”且经过明清战乱,湖广等地也是“城无完堞,世遍蓬蒿”[17]819、901,“弥望千里,绝无人烟”[18]1235。
推拉势力共同作用下,移民入川的浪潮一直持续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时间跨度百余年。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记载“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掾,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屋数板,否则仍徙它处。”[19]21-22这些移民多来自两湖及广东、江西一带,陕西也有部分迁入。大量移民入川,充实了因战乱而损耗的人口,四川地区的人口再增长明显。蓝勇统计了四川各地区移民所占比重,[20]54通过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清代四川各分区乃至全省,移民所占比重非常之大,尤其是楚地即湖广地区移民所占比重更是超过其它地方来的移民。这些不同省份的移民进人四川后,因为语言、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交流存在一定困难。语言方面“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之俗语,各处发音不同。”[21]1b除了语言的不统一外,来川各省民众还保持着原籍的风俗习惯,“操土音而循故俗,从宜异习,纠纷不能齐者,其势然也。”[22]24
(三)会馆的出现
这种移民与移民之间的差异,以及移民与土著居民的差异,使得到四川的湖广移民相互之间需要一种信任和依赖,希望有一种同乡组织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在心理慰藉的同时也为来川的本籍移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上的帮助。在这种互帮互助活动中,大家渐渐认识到同乡间集体力量的强大,进而强化了移民间这种同籍合作的观念,因此大家捐资建立移民会馆便水到渠成,并且在会馆中祭祀原来本籍的地方乡土神。[23]8“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醉为公产建立庙会,各祀其乡之神望。”[24]78a除了称之为“庙会”的,也有称作其它的,“或名曰‘庙,或名曰‘宫,或名曰‘祠,通称会馆。”[25]185
关于四川地区所建会馆的情况,蓝勇在其《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以及《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均有论述,并整理了清代四川会馆统计数据,[20]54-55由其统计可知,在清代四川地区的移民会馆中,不管是分地区(川西南地区除外)还是全省而言,湖广移民会馆所占比重都最大。湖广会馆所占比重和上文中湖广移民所占比重完全相符,也进一步证实了此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四川地区湖广移民会馆数量众多,在移民社会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在湖广移民群体内部起着整合作用,而且在同外部社会的交往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与地方政府也进行良性的权利互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县下基层社会矛盾调解机构。
二、湖广会馆在移民社会中的角色转换
湖广移民会馆有着多种称谓,其中以禹王宫为多,也有简称为“楚馆”的,其它还有寿佛寺、湖广馆、湖广会馆、两湖公所、湖北馆、湖南馆等名称。[20]508本文中所取湖广会馆资料以“禹王宫”为主。会馆建立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同一迁出地移民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借祭祀原居地乡土神来寄托对故乡的思念。
(一)会馆对于移民社会内部的整合
会馆将原籍乡土神作为整合同乡移民的纽带,并建立了以乡土神为中心的会馆,“以联乡谊,即供土神以隆报享”[26]1a。自从移民会馆产生之后,“每届春秋,令乡节人,少长咸集,泯南北之畛域,叙水木之本源,并回思缔造艰难,务期有基勿坏,上以妥神灵,下以敦乡谊。”[27]24湖广会馆这种组织不仅为移民的故土文化创造了一个保存环境,而且定期的集会又使得“本源”的概念得到重复性的提醒,因而让本地区湖广移民团体的集体记忆得以延续。其中提到的“泯南北之畛域”是针对湖广移民内部,要消除内部的小地域隔阂,其实是湖广会馆的内部整合功能的体现。[28]712通过这种内部整合功能使得湖广移民社会内部凝聚力得到提炼和强化。
关于湖广会馆在寄托鄉愁,心里安慰方面作用的记载,在清代四川地区的方志中非常多见,如宣汉县(今四川宣汉县)“楚人之居蜀者,则特奉禹王神像,建庙崇祀称之曰‘湖广会馆……岁时伏腊会集其中,以联祭梓之情,而慰异乡之感,又恐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许者呼诸神明以为凭然,皆各以其乡之神而祀之。”[29]86b
会馆作为一种移民社会的组织,在移民社会群体中其本身就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还是需要通过一些仪式性活动将这种凝聚作用外化。比如说定期举办的迎神赛会,湖广会馆一般将庆典日子定在正月十三,如大竹(今四川大竹县)“湖广会馆,岁正月十三及六月六日致祭。”[30]335盐源(今四川盐源县)“十三,禹王宫大烛会。”[31]8b潼南(今重庆潼南区)“是月(正月)十三称禹王生日,湖广来侨之民演戏剧而祀。”[32]53a同时仪式的定期举行有助于保持湖广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建禹王宫于东关之外,岁时祭享,无忘明德。”[33]508
除开定期的节日活动外,会馆还建义学,满足同乡人士后代的求学科举要求,如夔州府(今四川、重庆两省市万源、达州、梁平等地)“东里温塘井禹王宫内,义学一所,每年延师束修,钱五十千文,绅士胡洪达、彭厚载二人管理”。“东里榨井坝禹王宫内,义学一所,每年延师,束修钱五十千文,绅士吴大勋、章元亮、张翠山三人管理。”[34]198不仅在会馆内设立义学,还设置专人管理,可见其管理制度较为完备。一些地方也设置了书院或学堂,如遂宁(今四川遂宁市)“宝善书院,在城内禹王宫,楚人自设,故名。”[35]59b涪陵(今重庆涪陵区)“长坝场禹王宫公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陈荣之创设。”[36]19b荣县(今四川荣县)“禹王宫,乾隆三十年建,有学堂。” [37]25a
由此可见,湖广会馆不仅能通过节庆活动增进同乡之间的凝聚力,而且能够通过兴办学堂、学校使移民子女接受教育,实现由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实现移民在四川社会的阶层流动。
窦季良编著的《同乡组织之研究》对于会馆功能的转化,进行了总结。“会馆旧的功能主要包括丧葬、公祭、公庆、公宴、康乐、医疗、济贫、教育,托事以及职业介绍,纠纷(纠纷包括同乡之间的纠纷以及同乡与外乡人的纠纷)调解权益维护等项目。”[38]88会馆作为一种以家乡观念为纽带而建立的组织,它首先应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集中表现,通过这种组织在异域的移民社会中明确了本团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借助会馆展开同土著文化以及别的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 [39]206
(二)会馆与外部移民社会的交流、整合
初到四川,湖广移民势单力薄,需要借助会馆立足,增进移民团体的凝聚力。当发生同土著居民以及其它移民之间的矛盾,而自身又无法解决时,湖广会馆便发挥了它沟通、调解的作用。
1.同当地土著居民
清代,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到四川,他们不仅在城镇,也深入农村。由于这些外来移民多数将经济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同土著居民的矛盾。[39]207土著居民同湖广移民之矛盾在清代史籍中多有记载,而湖广移民占四川外来移民的多数,因此纷争矛盾更是难免,“川省遂大半皆秦楚之民杂处,因而欺隐侵夺,纷争告诘,遂无已时”。[40]860如《清文献通考》载:“湖广入川之人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41]4868此处四川人应指四川地区的土著居民,为了逃避纳粮,只得另谋他处。《隆昌县志》载原籍湖广的董子能应朝廷的号召,前往四川垦殖,“携家入川,路过广安,遇同乡友三十余人,悲啼一处,子能就问曰:尔等生来必得乐土安居矣,何尚仓皇失所如此?众告以报垦斯土,已经栽插一年,忽被豪衿何某者覇占,欲将我辈尽行驱逐,因此含冤未伸。”[42]32a-b同乡人不可能在如此环境中欺诈同乡人,故推测何某应是当地土著,因此该事件应为一土著欺客的典型事例。
移民入川,不仅抢占了四川地区的自然资源,也抢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因朝廷新政,允许入川之民入籍,且在川参加科举。“新政毕举,请弛客民入籍之禁,谓土客相争,每客强土弱,而客民入籍应试,又为土民把持,请土客一体考试,以泯畛域。”[43]15a科举名额上的纷争,使得政府不得不对移民地区的科举取士政策作出调整。
郭沫若在其作品《童年》一文中,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有过生动的描述,其中便提及了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土客矛盾之尖锐。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在地方性的事务上土著杨姓与客籍相互争斗,比如说办学,客籍人办了一个学堂,那么杨姓也会跟着办一个。还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44]251-252客籍与土著做事对着干,客籍人把土著人的悲惨遭遇当做“大快人心”的事,这都可见当时土客矛盾之尖锐,而在同土著势力斗争时,移民的个体力量微不足道,那么移民会馆就自然而然的充当了移民团体一方代言人的角色。
2.同其它移民团体
除开土客之间的矛盾外,客客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雍正二年(1728)管承泽上奏“当时朋名伙垦,原未分界址,今欲立户而相互争讼,甚而始为人田种,久之窥目间主人荒余田地私行报垦,交相控告。”[45]767虽然会馆成立之初是以乡情为纽带的组织,它的首要职能是同乡内部的整合,但是移民社会发展到后期,会馆仅仅发挥其内部整合功能是显然不够的。清代四川是移民集中区域,因此形成了“县属风习,乡市显异”[46]43的局面,因利益分配问题所引发的各移民集团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发展到后期,会馆组织便需要处理同其它移民团体的关系,从而为构建整体的社会而努力。
会馆设立客长,总管日常事务。“客有客长,邑之商贾湖广、江西二省人居多,各照省立长。”[47]12a除开“客长”的称呼外,还有称呼“值年”或“会首”的,而四川本地的首领则称“乡约”。清代四川有“麻乡约”的组织,推测可能是湖广麻城籍移民会馆首领的称呼。[48]31
清后期多数会馆都出现了合作的迹象,通过会馆之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移民社会外部的挑战。当居民发生矛盾时,会馆客长会出面调停。如邛崃县“客籍居久人多,建五省会馆,立五省客长……湖广会馆在城隍庙前……号三楚公所,主祀夏禹王……凡铺户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五省客长,四街街保评议是非。”[49]20a-b“街保”为乡里组织,而会长是移民团体组织会馆的代言人,可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在处理乡村社会的矛盾时正在趋向合作。
各省移民还会以会馆为单位共同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如德阳五省会馆在节庆时共同举行庆祝活动,“立春先一日,迎春东郊。五省会馆各醵钱,扮故事一台,名曰社火。共五台,台各两人。”[50]13b到了中元节,“六省会馆各雇浮屠,设孟兰会,扮铁围城,血河诸像,使礼佛者合掌唱佛偈绕行其中,谓之破血河城。”[50]19a
还有如合作办学,金堂县(今四川金堂县)“安怀书院,在县治东淮口镇,同治四年举人邓林,监生唐世丰等协议创设,每年五省会馆各捐钱五千。[51]26a邛崃县(今四川邛崃市)“高场公立国民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开办……设常年经费……五省会馆帮款。”[52]16b奉节县(今重庆奉节县)“敬梓义学、东来义学,在城内,二学系五省客长……等公设。”[53]4a
除合作办学外,还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如绵阳“育婴局有二,一系淸光绪十六年州牧刘南任内创始,开办仅四十名,局设城隍庙内,由城隍火神庙及五省会馆分担。”[54]14a蓬州(今四川蓬安县)“一养济院地基,系楚省各会首等,具禀捐施案存工房。”[55]29b
在清后期,随着各会馆为代表的移民团体彼此交往的增多,四川各会馆逐渐趋向联合。在大竹县原有楚、湘、粤、赣、闽五籍之人,开始时各建会馆,互不统属,而到了光绪五年(1879)则设立“五馆公所”,“立五馆公所,以团结之,公所职员由五馆举人充当,地方公务即由公所职员各就本馆举人充当,藉资聯络,而昭平允。”[56]183成立五馆公所之后,各省间隔阂渐消除“成立五馆公所,省界畛域藉以消融。”[57]599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开始也是会馆林立,同样发展到后来总称为“七省会馆”,“所谓七省会馆,是旧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58]2b
经过长期的整合,移民社会呈现出比较融洽的氛围。如民国时期的中江县(今四川中江县)“先至者或态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也。”[59]13b在清初大足县(今重庆大足区)移民开始时也是各从其俗,但是到了后来“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60]337
经济利益一方面是移民团体矛盾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促成彼此走向合作与融合的动力。经济与社会的力量无时不在削弱各种地缘组织原有的畛域观念,共同的经济利益促成超地缘的业缘结合,长期的全面接触促成土客、客客之间的社会同化。[61]114而移民会馆后期的彼此整合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经济利益更大化的考虑。
(三)与政府权利互动
会馆的逐渐融合,不仅是移民社会内部和外部的整合,到了清末,融合之后的会馆逐渐取代了政府在县以下基层政区的行政管理职能。[62]329会馆的客长与地方的团总、保甲一起构成了地方的县下治理体系。当会馆的功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时,会馆组织便会被统治者们所利用,将其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统治工具。 [63]104面对移民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原有的封建管理体制收效甚微,而会馆这一自发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组织,不但不会威胁到政府统治,反而能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整合效力,这种趋势在后期愈发的显著。不用额外的付出,却能获得如此大的效益,这是当时政府所喜闻乐见的。鉴于此,政府与湖广会馆的关系相处融洽,且逐渐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是体现在会馆对政府政策、行为的支持,而以此途径获得政府支持,这也是会馆能够存在的前提。四川巴县(今四川巴中市)有一名叫江宗海的湖广人,因为声誉显著,他被推举为两湖会长,凭借会长身份督办团练,“宗海治商有声誉,被推为两湖客长,太平军兴蜀接湘鄂,亦汲汲谋防堵,宗海以客长奉令督办川东团练。”[64]25a还如天全州(今四川天全县)移民“客长”的权威十分重要,“凡有命案重件……客长权柄最大,胥吏往拿案犯,非客长同去不能得手。”[48]35可见客长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地方官吏,成为乡村社会治安的主导力量。
其次,地方政府,尤其是原籍湖广但游宦四川的地方官员也帮助会馆发展。荣县湖广会馆最初在城东南隅,为雍正时期刘宗贤所创,乾隆中由武陵县令曾承谟将会馆迁移到另一处,但是修建不及时,到嘉庆七年(1802)楚人许源莅任时还未竣工。许源说:“公余率众乡人往谒之”,但见其“空殿数楹,香烟冷落,阶前荆蔓丛生”,甚是寥落。八年(1803)春,许源“捐俸为倡”,会馆终于得以落成。[65]51同样的情形也见达县(今四川达州市)的禹王宫,嘉庆年间,该馆因“庙后楼过高”被下令拆除。道光初,楚籍县令胡氏“目睹未完情形,力劝城乡。乡人踊跃输将,汲汲动工”。同治年间,另有两位湖广籍知县先后“勸募寄籍绅士,筹款募捐,培修之”。[27]24在清代四川地区修建湖广会馆时,多由当地官员做碑文记载此事。如石柱厅同知王萦绪做“大禹庙碑记”[66]11-12a、铜梁县县令韩清桂做“虎峰场禹庙碑记”[67]76b-78a、渠县邑侯王蔺三做“琅琊场补修禹庙碑记一首”。[68]1244
再次,地方官帮助修缮会馆不仅是因为部分官员受乡情的驱使,更是出于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考虑。如屏山县(今四川屏山县)的栗沱禹王宫,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知县张九章重修,一方面是鉴于大禹是被列入官方正祀,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屏山是少数民族地区,治理困难的缘故。修缮后的会馆“每岁藉此作赏夷公所用,塞其耳目。因凭禹之神灵,俾边氓共和,神奸不逢。”[69]25这样一来,禹王宫就由“私祀”变成了“官祀”。
地方官对会馆的祭祀和朝贺在其它地区也存在,如越雋厅(今四川越西县)禹王宫“嘉庆二年(1797)重修,有碑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六日,同知孙锵,率绅民行礼于此。”[70]227从“国家”与“地方”关系角度考虑,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乡土神所具有的相对稳固的地域性社会根基,从而使得地域性神祇的地位得以提升。而另一方面,随着它们被纳入官方祭祀范围,中央政府也得以在象征性层面上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这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弱化了乡土神的地域色彩,使其兼具超地域的可能。[71]109
三、小结
湖广会馆是明末清初伴随湖广移民移居四川而创设的,是湖广人士在移居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公馆或者商业性会馆,在正史中少有论及,而在明清地方文献中则保存较为完整。
会馆作为民间自发性组织能够在不同时期调整和转换自身的角色,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这根源于会馆本身的属性以及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从会馆本身而言,会馆的创立者们多把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的结果既可为自己带来政治经济利益,也切合政府对社会稳定的愿望,因而会馆的自发设立既具备了内驱力,又有外在的合理、合法性。传统的封建社会管理体制,仅适用于管辖安分守己的民众和户籍严明的稳定社会,且行政体制的完善仅限于县级及其以上政区,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要通过氏族、宗庙等势力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在一般情况下还能收效,但就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明清之际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不能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管理出现了危机,同时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的社会人口流动又倒逼着政府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思考管理社会的新的有效途径。[62]347-348
此时,地域性的会馆成为对流动人口实行有效管理的最佳社会组织。它不仅仅能凝聚同乡情谊,整合同乡移民内部,而且能够整合本乡民众同土著以及其它移民团体之间的矛盾,甚或逐渐担当起基层管理者的角色。
总而言之,湖广会馆是伴随明末清初移民浪潮而产生的特殊社会组织,它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调节器”角色,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变迁和演进程度的表征。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包含了移民团体、封建官绅、商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对变迁社会的逐渐适应,也见证了基层有序社会的自觉构建以及专制政权之外的自立自治精神的逐步形成。
注 释:
[1] 《四川通志·户口》(卷五上),《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
[2] 《温江县志·民政·户口》(卷三), 温江县图书馆藏本,1921年。
[3] 《安县志·食货·户口》(卷二十六), 石印本,1933年。
[4] 《资州直隶州志·食货志·户口》(卷七),《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5] 《太平县志·户口》(卷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6] 《金堂县续志·食货志·户口》(卷三),1921年。
[7] (清)《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十三·山防·三省山内边防论三·安流民》(卷八十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87年。
[8]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9] (清)《东华录·康熙四十九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十六辑),文海出版社,2006年。
[10] (清)《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明)王世性:《广志绎·西南诸省》(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
[12] 《嘉定府志·艺文志》(卷四十五),同治三年(1864)刻本。
[13] (清)《文献通考·职役考》(卷二十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 (清)《清通典·食货》(卷九),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
[15] (清)《文献通考·户口考》(卷十九),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
[16] 王笛:《走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0)》,中华书局,2001年。
[1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
[18] (清)《皇朝经世文编·户政九·垦荒与屯梳》(卷三十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87年。
[19] (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
[20]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 《安县志·礼俗·声音清浊》(卷五十六),石印本,1933年。
[22] (清)《乐至县志·地理志·风俗》(卷三),《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十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23] 劉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4] 《富顺县志·坛庙》(卷四),1921年刻本。
[25] 《大足县志·方舆下》(卷二),成文出版社,1976年。
[26] 《重修什邡县志·礼俗·会馆主神》(卷七下),1929年重印。
[27] 《达县志·礼俗门·庙祠·知县易崇阶重建禹王宫序》(卷十),1938年铅印本。
[28] 谭红主编:《四川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
[29] (清)《城口厅志·艺文志·禹王碑记》(卷二十),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30] 《大竹县志·祠祀志》(卷三),成文出版社,1976年。
[31] (清)《盐源县志·风俗》(卷十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32] 《潼南县志·杂记志第十·风俗》(卷六),1915年刻本。
[33] (明)《内江县志·艺文志下》(卷四十八),《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34] (清)《夔州府志·学校》(卷十七),《中国地方志集成》,据道光七年(1827)刻本影印。
[35] (清)《遂宁县志·学校》(卷二),光绪五年(1879)刻本。
[36]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建置志·书院》(卷五),1928年铅印本。
[37] 《荣县志·社祀》(卷十一),1929年刻本。
[38] 窦季良编著:《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36年。
[39] 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
[40]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辑),故宫博物院,1978年。
[41] (清)《文献通考·田赋二》(卷二),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
[42] 《隆昌县志·艺文·传》(卷三十六),同治元年(1862)刻本。
[43] 《绵阳县志·人物》(卷七),1932年刻本。
[44] 杨芳选编:《郭沫若作品精选·我的童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4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第九辑),故宫博物院,1978年。
[46] 《重修广元县志稿·礼俗志二·风俗》(第四编第十五卷),1940年铅印本。
[47] 《峨眉县志·保甲》(卷三),乾隆五年(1740)刻本。
[48] 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 《邛崃县志·建置志上·庙祀篇四》(卷二),1922年铅印本。
[50] 《德阳县志·风俗》(卷十八),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51] 《续金堂县志·政事部上·学校志》(卷七),同治六年(1867)刻本。其中“会”推断应为“费”。斗是和市都是古代计量单位。岁修指每年有计划的维修。
[52] 《邛崃县图志·学校志·国民学校》(卷四),1922年铅印本。
[53] 《奉节县志·学校》(卷十八),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54] 《绵阳县志·建置·公署》(卷二),1932年。
[55] 《蓬州志·艺文篇·洪运开养济院碑文》(卷十五),光绪二十七年(1897)刻本。
[56] 《大竹县志·建置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76年。
[57] 《大竹县志·职官志》(卷七),成文出版社,1976年。
[58] 《灌县志·礼俗志》(卷十六),1933年铅印本。
[59] 《中江县志·风俗》(卷二), 1936年铅印本。
[60] 《大足县志·风俗》(卷三),成文出版社,1976年。
[61]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1966年。
[62]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63] 王日根:《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64] 《巴县志·人物》(卷十),1939年刻本。
[65] 《荣县志·艺文志》(卷三十四),光绪三年(1877)刻本。
[66] 《补辑石柱厅新志·艺文志》(卷十),道光十三年(1843)刻本。
[67] 《铜梁县志·艺文志二》(卷十二),光绪元年(1875)刻本。
[68] 《渠县志·碑志类上》(卷十二),成文出版社,1976年。
[69] 《屏山县志·祠祭志·私祀》(卷下),1931年铅印本。
[70] 《越雋厅全志·寺观志》(卷二十),成文出版社,1968年。
[71] 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夏雪
作者简介:
何绪军(1992-),男,四川营山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王银田(1957-),男,山西大同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汉唐考古、辽宋金考古、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