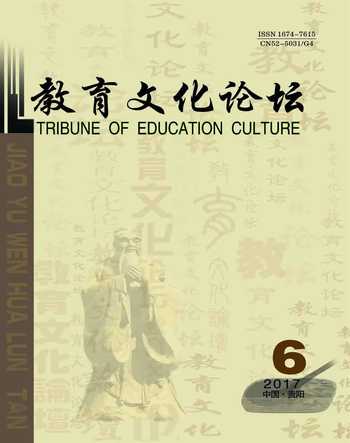李端棻《普通学说》课程思想论析
戴岳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获罪发配西域,但他初衷不改,因病赦归故里后,受邀主讲贵州经世大学堂,仍继续倡导西方新学,实践自己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构想。他编纂《普通学说》推行新文化的传播,为贵州培养有用的新式人才。《普通学说》中蕴含着关于课程目的、课程内容、课程用书等的思想见解,对贵州近代教育的课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李端棻;普通学说;课程;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114-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4
课程是教育和教学的核心,课程论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在我国虽然只有简短的历史,但是有关这一领域的论述却源远流长。审视中国近代教育,李端棻不但最早提出并设计了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的方案,而且在其后期亲身的教育实践中也萌生着课程意识,在其讲稿《普通学说》中闪烁着关于课程的智慧。
“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以“保荐罪人”的罪名被革职发往新疆,1901年因年老多病被赦回原籍贵阳。回归故里,李端棻并没有遵从封建王朝历来“大臣废退,当闭门思过”的不成文规则,放弃自己力求变法维新、强国富民的主张,反而意气不减当年。1902年李端棻受贵州巡抚邓华熙邀请主持贵州经世学堂,面对家乡如此落后、闭塞,对于如何讲学,选择什么作为讲学的内容,李端棻有着深入的思考,其诗《应经世学堂聘》记载:“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表明李端棻已经萌生课程意識,具有了课程设置的思考。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任主讲时所著的讲稿《普通学说》,对课程目的、课程内容发表了重要的见解,课程设置思路相当清晰,而且体现在其教学内容和教育实践中。《普通学说》不但介绍了大量的新学科目,拓宽了贵州士人的眼界,而且也为贵州近代教育的课程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对当前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课程的目的
《普通学说》开篇发文,“睹吾乡人士未尝不思为学,而或蔽或偏,莫能自拔。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著之于编,以求众览。”李端棻指出,家乡人士并非不想学习新知,不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由于贵州地处偏陋,无法获得良好的增加见闻的条件和途径,所以他愿意竭其所知帮助学子共求进取之途。当时的贵州教育极为落后,李端棻忧心人才匮乏的严重。《普通学说》封面蒲藏锋的题字,即记载有“泌园李尚书之新作也。时李公主精世学堂讲席,感时势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黔处僻邑,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2]尽管当时官方教育制度也较前有了变化,“然国计艰难,普及之教育未能遽成,则学校所收容或有限。”[3]面对时局的巨变,为了让地处僻邑的贵州跟上形势的变化,李端棻决心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开通民智为己任。《普通学说》清楚地表明了李端棻的课程目的,“乃作是说以示之的”,“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兹之所言,不过与校外诸君于自修自习之时,代辟蹊径”[4],李端棻希望通过《普通学说》普及教育,帮助那些想学而又缺乏条件的家乡人士自修自习,为贵州大量培养更多的掌握新知的时用人才。
《普通学说》提出的课程目的,是李端棻教育思想的体现和发展。重视人才培养,强调新教育的普及,一直是李端棻关注的重要问题,他始终把变法、人才、教育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从时局变化的现实提出改革封建教育,培养人才以济世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编著《普通学说》的七年前,李端棻作为刑部左侍郎给清廷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即陈述了人才在国家中的重要性,“窃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5]。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他明确地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6],将培养人才的意义提到强国御侮的位置。对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强调,既是李端棻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也是他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对洋务运动反思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后,泰西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就击碎了清王朝自认为“天下第一”的幻觉,强虏入侵,中华民族带来奇耻大辱与无尽的灾难。为了强国富民,洋务派在19世纪60~90年代开始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然而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中国的再次惨败,让“天朝帝国”濒临崩溃,堂堂的泱泱大国不及东瀛弹丸岛国,民族危亡势若累卵。一批从沉重屈辱悲愤中觉醒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药方”,力主变法维新。通过对普鲁士战胜法国及日本等列强战胜中国的反思和比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和日本之所以强盛主要在于发展教育,洋务运动失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人才,在于旧教育体制的落后。作为支持维新运动的中坚力量,李端棻也深深地感到,国家的兴盛主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又在于推行新教育,他慨叹“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李端棻认为这是教育制度的弊端造成的,“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批评之前的洋务教育尽管搞了二三十年,京城设立了同文馆,各省设立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都是讲中外学术结合在一起讲授、学习,各地都有,但是各馆设立以来,已经二十余年,国家却没有得到一个有奇才异能的人,究其原因,是当时的教育制度在教学内容、教授知识、教学方法、科举取士制度阻滞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可以说,洋务教育是旨在造就少数的专用人才,而无意建立普及教育的近代化国民教育体制,结果完全不能适应当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李端棻认为“育人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法,当遍于率土”[2],他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理论,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按府州县学、省学、京师大学三级学堂分别选地方俊秀子弟,诸生员、举人、贡生、监生符合年龄者入学。
《普通学说》所反映的观点、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请推广学校折》所提出的思想认识和教育主张是一致的。尽管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封建教育改革方案,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在当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其余都不了了之。不过李端棻并没有悲观失望,即便“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因“滥行保荐”罪名被革职以及后来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李端棻也未叹老嗟悲,对改革的初衷仍然未改,依然继续力倡西学,坚持推行新式教育。贵州地瘠民贫,百废待兴,李端棻将发展教育事业和选派留学生作为开户民智,振兴实业的手段,他认为必须通过民智开发与物力开发并举,才能改变贵州的落后面貌。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主持贵州新经世学堂讲席,李端棻开始亲身参与新式教育实践活动,得以将自己的教育主张落实到实际。尽管此时李端棻的身份已不同于过去,但是他依然强调为国家培养时用人才的主张,指出“今日人才患其无,尤患其少”,特别是贵州地处僻邑,人们对新学缺乏认识,虽“自严范孙编修督学以来,人始知学”[2],但是“于於今日空疏如故”,所以他提出“今之为学者,当求实际,不可流於空论”[3],要求“号称士子者固应人人自奋於学界之中,以求供当时之用”[4]。李端棻认为,人心的希望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了希望,今日的中国就会如同百年以前,但是“所希望所构成者皆东南士大夫之力,我野人士无与者焉,是可大忧也。使就人之所希望所构成者,而我黔人士不惟无与,又不能因之以自致于学,则尤可忧也”,他感叹所希望所构成者都是东南一代的人士,而贵州人士却无法参与,甚至不能因之而自学。他认为这是非常惭愧的事情,“同为一国之人而相去如此,有志之士自居何等?”正因为如此,他编著了这本《普通学说》,是希望“请得与诸君勉力赴之”,为贵州培养有用的新式人才。可以说,《普通学说》是对《请推广学校折》教育目的的延续,不同的是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只是提出一种教育改革的主张,而在编著《普通学说》时已经亲身参与到教育实践。上书《请推广学校折》时李端棻是作为维新官僚,站在了整个国家的全局上,而编著《普通学说》时李端棻已经告老还乡,针对的只是贵州一隅。《请推广学校折》中勾画出一个宏观的教育改革方案,而《普通学说》则落实到具体教学的课程中,但在强调教育的普及、重视人才培养的思想上两者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关于课程的内容
李端棻以普通学说作为育人的基础,让学生接受人类的各种知识,《普通学说》中关于课程的内容便是以课程目的为依据。从教育普及的需要,李端棻认为学习应从基础知识开始,他指出:“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西人谓之文学、质学。质学,东人又谓之科学,凡人类应有之智识悉具于是。”他强调学习普通学的重要性,“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强调坚实、丰富的基础知识对求学的重要性。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对认为应该掌握的普通学逐一进行了介绍、分析和阐述,并概括说:“普通学之最不可少者,曰算术,曰几何,曰代数,曰中国地理,曰中国历史,曰外国地理,曰外国历史,曰地文,曰地质,曰理化,曰生理,曰博物,曰政治,曰法制,曰经济,曰伦理,凡十六科,如上所列。”[2]
从《普通学说》所列的课程内容来看,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相比此前的洋务教育,此时李端棻对“新学”内容的认识,已大大超出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也积极创办各类洋务学堂,清政府在鸦片战争遭受的惨败,让洋务派亲身感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从而认识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在洋务派的眼里,西方的“长技”只是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之类实用的东西,洋务派把中国的自强寄希望于学习外国利器,李鸿章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3],在中央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也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4],他们都把关注点集中到制造武器的机器上。但是只要接触到机器生产,那么与机器生产紧密连带的科学技术就必然成为洋务派首先遇到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洋务派后来建立一系列的近代化军事工业,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就更加突出。为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洋务派创立学堂进行培养,但是创办的学堂主要是以技术学校为主,尤其是军事技术人才占了多半。洋务派认为,西方学术的长处主要在于算学、格致、天文、军事技术、制械技术方面,而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经史诸学才是最完美的,因此几乎所有的洋务学堂都将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以及经史诸学置于课程的首位,而西学的课程则基本限于语言学习以及自然科技的范畴。对洋务运动所办的学堂,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已经进行了批评,“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2],“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3],从学习内容、学科设置、教学方法上对洋务运动时期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不足进行了分析,李端棻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人才乏绝的原因,是教育法方法的未尽如人意。这些看法很有見地,说明李端棻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洋务派在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在《普通学说》课程的设置中,李端棻倡导加强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自然地理等普通知识,他清楚地认识科学技术在西方国家的强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强调政治的重要性,“西学以来,先有普通学后有政治,与吾人自习应有之次序亦正同”[4]。比起洋务派,李端棻对西学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他指出“此外如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或未普及于学校。至如农工与商,又为实业之学,其本亦在博物、理化、经济之中。自此之外悉为专门之学,实业与专门皆普通学成后之一步,故不繁列”,比起洋务派,李端棻对西学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
李端棻在普通学中所列的课程,较之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列课程也有较大的进步。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按章程规定分为两类:溥通学和专门学。前者为每个学生必修,后者是学生学完溥通学之后,要选修其中的一两门,“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5]。溥通学是所有学生必修的内容,其中包含了10门课程,可以看出在这10门课程中,属于“中学”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这是“中学为体”的课程思想在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学宗旨。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议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对各类学堂的选拔对象、入学年龄、入学条件、课程内容作了规定,对于府州县学,选拔对象是年龄十二至二十的民间俊秀弟子,也允许诸生以上功名的人入学,学习课程是“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代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对于省学,是选诸生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入学,也允许那些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入学,学习课程是“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2];对于京师大学堂,是选举人、贡生、监生中三十以下的人入学,也允许那些京官中愿意学习的人入学,学习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3]。可见李端棻已经认识到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学业水平来安排不同的课程内容,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即便李端棻倡导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也仍然主张的是以学习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为主,而以西学为辅。从《京师大学堂章程》可以看出,尽管课程设置尽管已经接受了近代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模式,但仍然没有摆脱以经史子集为中心的封建传统的课程。而到了《普通学说》,李端棻则剔除了梁启超“参以中学”而罗列的“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等内容,成为一个更为彻底的西方普通学课程表。
尽管删掉了经学、诸子学等内容,但《普通学说》的课程内容也并非全盘西化。对于学习本国的地理、历史,李端棻也极其重视,他认为本国的地理、历史知识应“为本国人特别应有之智识,较切于人类普通应有之智识也”[4]。他慨叹“我国读书人往往有并此不知者,是可叹也”[5],并用孩童的例子来说明了解我国地理、历史的重要性,“今有十龄外学童异性之人,见之问其居址何处不能答,问其宅之大小不能答,问其家有何人、具何物、执何业而皆不能答。若是者,人必以愚騃视之。读书人而不说本国之地理与历史,何以异此?”[6]《普通学说》不仅阐明了学习本国地理,历史的重要性,而且批评了当时封建教育对学习本国地理、历史的不重视,指出其产生的后果,李端棻认为当时国人没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其原因并非是国人不爱国,而是他们不知道我国有可爱之处,“爱国之心甚薄,非不爱也,不知我国有可爱者在也”[7]。他认为本国地理、历史是爱国之心的种子,主张通过学习我国地理、历史来培养国人的爱国之心。学习本国地理、历史,让国人了解到我国便利的地理位置、温和的气候条件、富饶的物产、几千年的文明史、广袤土地和丰富人口,感受到我国的可爱之处,可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从而“以爱家之心爱国,则国盛矣”。反之,“然使不知之则遂淡焉、漠焉,不知此国为何人之国,亦似无与于我也者。故本国地理、历史亟应知之,职是之故”,如果国人不知道我国的地理、历史,就会出现淡漠,对国家缺乏感情,所以应该让国人都了解本国地理、历史,这是教育的职责。可见《普通学说》的课程内容虽然主要是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但李端棻便没有忽视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学习,他抛弃的是封建教育中的迂腐、落后的部分,其对西学的倡导,实质是强国、救国的爱国情怀的反映。
三、关于课程的用书
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课程用书是学校教育的物质基础,是实现课程目的与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课程用书的主要形式是教科书,教科书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主要工具。教科书是教育制度的反映,并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而发生变化。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教科书的改革更是其关键所在。晚清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教科书的作用,教科书对于教育就好像“锄犁之于耕、炮械之于战;无锄犁不可言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2]。兴学之要“全以教科书为胜败”,没有新式教科书,就无法进行新式教育。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才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现各处学堂皆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3]。而在当时的贵州,地处僻邑,人们对新学缺乏认识,还没有教科书的概念,在《普通学说》中李端棻介绍了教科书、以及教科书的特点和作用,“学校用者谓之教科书,程度之高低,则随学校之大小而异”,“何等学堂应用何等教科有一定之程,故其书特便教授。”[4]
不同于我国封建教育中的教科书主要是包括大量启蒙读物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科考用书,近代新式教科书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为满足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需求,从国外引进的。晚清新政后,各省纷纷设立新式学堂,但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缺乏合适的教科书,“为教习者,亦未深通新学之理、教授之法,以及功课书则粗笨不和”,一方面关于中学的经史子集浩繁庞杂,在内容与编写体例方面很难适应近代教育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关“西学”、“西艺”的自然科学课程都没有现成的中文教科书,目前“农、工、商、兵之学,中国专书不尽适用,或且无之。” “当今直省督抚,亦纷纷渐知立学堂矣,然学堂以何物教之,尚未计及也。”[2]如何保证教科书的质量,李端棻很重视教科书的翻译,他认为,兴学育才,“首在译书”,“唯有译书之一法,最为便捷。”“若不借资外国,其学虚立,不能成就”,“今日方议采西法,而不能翻译各国书籍,是犹无米之炊”。[3]但是当时对西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谈西学往往是东抄西录,断章取义。李端棻认为,洋务学堂之所以未能培养出适用的人才,就是由于没有编译出合适的教科书。《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洋务时期所编译的教科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载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4]。为此李端棻提出,应在“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5]
相比过去学习西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西方的书籍,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更强调引进日本的教科书,使用日文翻译的西学之书,“西学之书,前此多由西文译出,而由英文来者尤夥。甲午以后,始有译东文之说,其极盛亦只在此一二年间也。”[1]他认为对于普通学的学习,“若为寻常致用及寻常教习之学,则日本之中学教科书亦已足用”。究其原因,李端棻解释,“西人之书以理解胜,大致浑朴类我国三代两汉时。东人则抉择最精当,体例极严整,读之较省脑力而所得亦较多。不知由东文来者,果有胜于由西文来者耶,抑东入与我同文,其修辞之学较便于我国人之领受也”,他认为日文与中文相近,日文翻译的西学之书,抉择精当,体例严整,读起来更省脑力而且收获较多,因为日文与中文同问,修辞之学更易于国人领受。这说明李端棻对国情和日本的历史状况是很了解的,中国与日本社会性质相近,“同文”、“同种”,风俗相似,文字易懂,有利学习,他的這个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普通学说》不仅重视对西学的翻译,更强调对中国历史、地理所用之书的编撰。李端棻认为本国的地理、历史知识“应较他学为稍深乃能足用,以此为本国人特别应有之智识,较切于人类普通应有之智识也”[2],但是当时地理、历史所用之书太过于陈旧,反而不如外国代纂的书,“本国地理、历史所用之书,自应以本国人所纂述者为最相宜。然今日而为是学则旧时之书,反不若外人代纂之书,此无容为讳也。”[3]他认为,其原因在于我国交通不发达,编纂者的视野、境界不开阔,“以前之史学家尚未有交通之智识,其所著书犹执其一偏之见,以剪裁天下之事,读之可以记事绩,而不足穷理趣。”[4]他慨叹学者读旧书十年所得的收获,还不及日本人撰写的一卷中国历史书籍,“今日之为是学者读旧书十年,其所得不过数千年之所云云,及读一卷东人代纂之书,顿觉天地易色,接于目触于脑者悉非向日之所有,而又非本来之所无”[5]。李端棻不仅批评当时历史教科书编写上的弊端,更指出了地理教科书编写上存在的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先进的测绘知识和丰富的地理知识,在我国地图的绘本上极其落后,造成“然沿海溯江,西人之所测固已远胜旧图矣,故外人之所已知者,中人则尚未知之”,只能使中国在发展上处处吃亏,其结果是我国“办海军、开航路,亦须求本国之图于外人,而士子之为学更无论矣”。李端棻非常痛心我国地图绘本落后造成在处理实际边疆事务时的极大损失,“边疆偶有划界之役,其图样例须由外人绘出,膏腴险要任其割取,而执事懵然莫能与争,尤属痛心之事。”[6]李端棻把中国地理、历史书籍的编纂放在了民族利益、国家的荣辱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观点。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李端棻继承了士大夫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待意识。所以尽管到了垂暮之年,但仍然志气尚如少年。他同家乡人士“共求进取之途”,并“与诸君勉力赴之”,坚持推行新式教育,亲自主讲新思想新知识,开启了贵州近代的新式学风。
参考文献:
[1]李端棻.普通学说[M].贵阳: 武庙铅字活版所,光绪二十九年.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3]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A]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262.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1.
[5]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28.
[6]论国定教科书[N].大公报,1907,4,3.
[7]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A]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35.
[8]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93,31.
[9]郑鹤声.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A].黎难秋,等.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