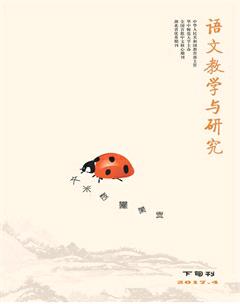国学的焦灼
佚名
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一百六十多年。到了国力日益强盛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民族的复兴。而一个渴望复兴的古老的民族面对现实和外来的焦灼心态,也日趋明显。从1840年至今,我们每个人所能创造出的文化资源,必然受到西方外来文化以及1840年以后本土新思潮二者的影响。按一些激进国学家的安排,纯然依照孔孟之道来认识社会、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而一旦接受了外来与新生,又害怕失去本民族的特色,成为了没有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殖民地。现在特定语境当中的“国学”观念与理论,所折射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焦灼。
此外,在“国学热”当中,有种论调颇有代表性:“我们天天在要求现代化,现代化不就是西化吗?把整个的思想按西方的观点来大卸八块,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复兴,反而越发地死得快……”
以上的观点说白了,就是将“从西方传入”当成了本质上的“西方”,与中华文化不可调和的“西方”,而忽视了一些社会基础性价值的普适性,也忽视了文化的包容性和交流。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活力的水域不是娃哈哈公司的纯净水储存池,而是有污泥、有毒菌、有浊浪,时时刻刻被海洋生物代谢物污染着的大海。一个文明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动力不是一种精神洁癖,那种洁癖只能说明一个文明已经虚弱到了免疫机能低下的地步。而在相当数目的国学家眼里,西方传来的文化与思想就只能起到破坏和摧毁中华文明的作用。这其间折射出的对自我民族的不自信,也是颇值得玩味的。
而事实证明,1840年以来,本土新创造的文化都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中华传统,但其中却不乏优秀杰出的成果,以至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在文学成就还是思想成就上,都创造了令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而其思想的创造仍然植根于中国,属于中国。很多2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胡适、李大钊等,自然是鼓吹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观念”的代表,但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爱弥儿》相比,《尝试集》与《神曲》相比,《庶民的胜利》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相比,在精神内核和社会效果上,真的能一致?就像黑格尔说的,“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膚!”
往者不可谏,学习西方也没什么丢脸的。日本从1865年就一心一意地跟着西方闹革命,到头来,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张嘴都能从一堆黄皮肤黑头发的人里冒出来。
以日本为鉴,以中国现代思想史为鉴,担心成为西方的精神殖民地这样虚弱的焦灼心态,不仅是一部分“国学家”对自我民族不自信的体现,也是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节选自《现代交际·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