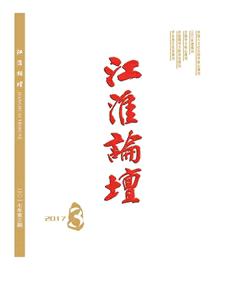社会法上的积极国家及其法理分析
余少祥
摘要:由于私法和市场经济不能自动消除贫困、失业、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不能自发地实现社会公正,必须由国家介入才能解决,由此催生了社会法“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相结合”的法律机制。作为积极国家法律实践的产物,社会法行政执法机制的理论来源是积极自由、积极权利和人权学说,与其他法律部门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国家给付、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积极执法与消极执法相结合。
关键词:社会法;行政执法;积极国家;机制;特性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88-007
近代民法和私法是适应市场机制的法律,它要求国家对市民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干涉。因此,私法上的“人”舍弃了无数市民的个体特征,是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特殊性、完全中立、没有任何偏见的抽象的个人。[1]事实上,作为私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富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与此相反,社会法上的人是具体的人,他们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上获得基本生存资源,或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也就是行为主义经济学所谓“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有限的自利”。[2]因此,社会法上的“人”需要国家和社会施以援手,通过行政执法保障其基本生活权利,防止强势主体利用其缺陷,导致有违社会公平。其基本特征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进入原本不干预的私人领域,履行对特定对象的给付或其他义务。这是社会法与传统法律部门最显著的区别之一,由此形成了社会法特殊的行政执法机制,在法律领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社会法执法中的积极国家
(一)私法机制及其不足
根据传统私法理念,个人是国家的本原和基础,是法律的目的,国家只是他的外在保障。在价值取向上,国家是中立的,当不同的“善”观念发生冲突时,“国家或政府必须在其公民之间是严格中立的”。[3]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和诺奇克所倡导的“最低限度的国家”,也就是消极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国家的目的不是追求“至善”,而是惩戒和避免“恶行”,其合法性在于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为个人实现理想提供条件。在执行法律时,除了违反公法的行为要受到国家主动追究外,一律实行“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国家作为“执造两端”的仲裁者和居中调节者,不主动追究私法上的违法行为,不主动介入私人领域和私人事务,国家也不构成私法上的义务主体和当事人。
因此,无论是以实现公共利益还是其他崇高理想为名,国家都不得干涉个人选择,不得干预个人生活。比如,国家不干预私人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对于雇主拥有的解雇自由,不能予以限制。由于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祸害”,需要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使国家权力避免过于强大。同时,要防止国家权力误用和滥用,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得以实现,使个人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国家能力亦不能随意加强,要用“自由主义的剃刀”将国家身上多余的能力剃掉。正是在这种“消极国家观”的指导下,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私法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造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合法掠夺”。
(二)社会法机制及其实质
1.社会法机制的产生
由于民生问题恶化,慈善、互助和施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改良主义者开始考虑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强调国家干预以帮助穷人摆脱困境的必要性。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大量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规制私人契约(1),“以解决与经济生活相关之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藉以安定社会并修正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負面影响,”[4]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就是今天我们指称的“社会基准法”。由于社会基准法大量出现,最终导致社会法和“积极国家”的产生。所谓社会基准法,就是将社会弱者的利益,抽象提升到社会宏观层面,以法律的普遍意志代替弱者的个别意志,从而实现对其利益的特殊保护。[5]社会基准法克服了弱者交易能力差、其利益常被民法“意思自治”方式剥夺的局限,可以节约大量的个体交易成本和社会司法成本[6],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社会自治可能存在的民间秩序失衡与社会权力的恃强凌弱[7],改变了强弱主体之间的力量不均衡状态,有利于保护弱势一方主体的利益。
由于社会基准法的确立,社会法中既有强制性规范,也有任意性规范。其中,社会基准法就是一种强制性规范,任何团体或个人契约都不能与之相违背,或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同时,社会法不像行政法完全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是在基准法之上为各方“保留了一定的约定自由权利”。[8]以劳动合同法为例,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双方约定的工资数额仍然有效。在社会基准之上,当事人如何约定,国家并不干预,只要不违反基准法的“底线”,个体和团体契约可以继续发挥作用[6],这是社会法执法机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积极国家及其表现形式
社会基准法是积极国家的由来和实践依据。按照社会基准法的要求,国家进入某些私人领域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须的。国家是有能力的国家,政府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9]通过积极实施和执行社会基准法、履行给付义务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水准。比如,个人和家庭没有生活来源,过去国家是不管的,现在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不仅如此,很多国家还对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规定了详尽的、具体的津贴制度,有些国家的法律如德国甚至规定了以实际收入损失为补偿基础的双亲育婴假和补贴制度,引导男性分担家庭责任。这些都是“积极国家”表现形式。因此,在社会法中,公民不仅有“要求公权者消极不作为的权利”[10]225,还有“要求公权者积极作为的权利”[10]223。以残疾人权益保护法为例,由于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功能等缺乏或弱化,只有通过政府对残疾人所缺乏或弱化的那部分功能进行积极补偿或帮助,才能使他们克服来自市场和社会的风险,这是“使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分享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实现自身生存发展权利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水准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