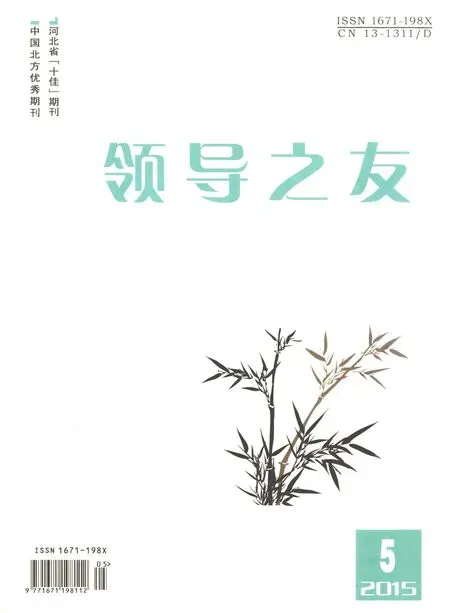市场决定性作用下的政府行为矫正
张岩鸿
(深圳行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教研部,广东 深圳 518040)
市场决定性作用下的政府行为矫正
张岩鸿
(深圳行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教研部,广东 深圳 518040)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而转型就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代表先进产能的企业能够不断成长壮大,让代表落后产能的企业不得不退出转行,进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实力及质量的全面提升和不断改进。但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由于政府干预行为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偏离较远而亟待矫正。矫正行为主要包括四大类:要废除一切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干预行为;要纠正一切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误导行为;要加强各类影响市场机制规范运行的监管行为;要完善各类影响市场机制有序运行的维护行为。
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政府行为;矫正
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各类市场参与主体能够通过自主决策自由进出市场,通过公平竞争自发引导供求均衡,最后通过均衡价格自动配置资源流向和实现市场参与主体的盈亏存亡。因此,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成为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三大基本机制。而市场参与主体的进退留去关键就取决于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的生产成本或生产资料购进成本与最终成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之间是否存在正向价差以及这一正向价差的数额大小。正向价差越大,表明其赢利能力越高,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可能因遭受亏损而需要奋力改进实现升级,或需要关门结业退出市场。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际上就应该通过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代表先进产能的企业能够不断成长壮大,让代表落后产能的企业不得不退出转行,进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实力及质量的全面提升和不断改进。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研究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实践理论的美国学者。市场机制设计就是以“市场机制”为主要对象的机制设计,目的是通过对市场微观机制进行设计从而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结果更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基本需求的目标。[1]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背景下,构筑市场机制任务极为迫切和重要,各级政府必须提升到转变政府职能高度,全力做好。
一、废除一切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是价格机制能够自发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机制是一个并非人们有意创造的、自然形成的、叹为观止的制度安排。[2]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行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市场参与主体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其二,市场价格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波动;其三,市场参与主体退出市场不存在人为障碍。基于此,我国在构筑完善的市场机制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且尽快地废除一切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干预行为。
(一)破除行政壁垒,制定平等进入的公平规则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且运行时间不长,因此,从理念上、制度上直至行为上,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并未从根本上切实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转变思维模式及管理方式。不少沿袭计划经济体制思维范式及效率安排的审批式管理模式依旧广泛存在,这也是一轮轮的行政审批改革进行多年仍然未能实现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融相合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隐藏于这一原因背后的深层根源是审批经济所内含的利益捆绑,这种利益捆绑所涉及的利益既含纯粹的个人或部门的狭隘私利,也含由中央政府制度安排所鼓励引导出的能够归结为大公无私的地方公共利益。实践中,这两种利益追求虽然从主观动机上迥异,但从客观效果上说,都因设置了重重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流程而影响了市场参与主体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进入成本和进入效率,且由于不少地区对当地地方国企及一些拥有背景企业宠爱有加而有违公开要求、公平原则和公正理念。未来,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各相关职能部门应该以开放为目标,以公平为准则,以提效优质为任务,破除一切阻滞、割据市场效率和市场规模的行政壁垒,分行业制定并实施平等进入市场的公平规则,特别是对于地方国企要改变管理理念和管理思路,营造让其在市场竞争中与其他所有制主体平等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二)减少行政干预,建立自发作用的价格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主管部门到业务主管部门的价格管理机构体系,形成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价格管理形式[3]。但目前我国一部分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商品价格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能源价格、矿产价格、土地价格、金融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房地产价格等等。不科学、不合理、不完善的价格机制,造成的问题很多,既包括直接影响市场参与主体成本核算和赢利计算的微观生存态势,也包括间接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资源流向规模和速度的宏观健康程度。现实中,各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仍然有意无意进行的价格干预行为形式多样,比如限制价格、给予价格补贴、减税、奖励、税收返还、信贷优惠、限制竞争性同类商品进入等等。各式各样的价格行政干预行为,扭曲了价格信号,误导了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人为造就了超越市场自发调节水平以外的更大的产能过剩或不足,还导致了一部分落后产能长期大而不倒,持续地浪费着资源,不停地污染着环境。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长期倡导但效果不佳的根本性原因。未来,我国若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在更大范围中、更多要素市场上建立起能够不受干扰自发作用的价格机制。各地方政府应该努力放弃行政性干预价格机制的冲动并通过法律法规进行限权,努力将职能重心切实转到社会管理和民生问题上。并非偶然的是,政府卷入经济活动,往往会同生产力成反比,[4](P149)该观点不仅国外大量学者持有,国内认同的学者亦不少,比如周其仁、李义平等。
(三)消除行政救助,引导劣汰企业顺利退出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中迄今为止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无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劣者必被淘汰的铁律,一方面鞭策着优胜者不能因自满而停下创新创造的步伐;另一方面激励着失败者重拾信心,卷土重来。当然,亦有不少失败者可能再也无法重现辉煌。不能想象,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机制不再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发生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效率优势还能存在。而我国,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下,公众见到的媒体新闻中经常出现政府救助企业,尤其是效率低下国企的相关报道。来自《烟台晚报》2014年9月22日的《要闻经济》中报道,有统计显示,93家上市公司2014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大于其净利润。过去的3年半中,278家公司依赖政府补贴扭亏为盈,一些公司甚至借此躲过退市厄运。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补贴过亿元的58家上市公司中,40家为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占比近七成。[5]而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为绩差公司提供补贴,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新股发行虽然实行核准制,但实际上却依然采用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而且退市机制日趋严格。于是,为了保住宝贵的壳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便不惜通过补贴方式来为上市公司打造可以过关的财务报表。低效劣势企业由于政府救助而无法退出的这种做法,既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纳税人应享有的公共福利权益,更导致了越来越稀缺的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低效使用。毋庸赘述,切实将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转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并尽可能移走其偏好直接调度资源的经济调节职能,是阻断地方政府继续保护劣汰企业(主要是地方国企)的治本之策。
二、纠正一切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误导行为
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是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确实反映了市场供求状况、要素稀缺程度及其要素使用的社会成本,包括企业成本和企业外部成本两部分之和。各市场参与主体能够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下进行生产经营并展开竞争。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运行时间短、运行经验少、运行理念尚待明确、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重及传统官本位意识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有些制度安排及政府行为明显有违市场原则和市场规律,没有体现平等精神、法治理念及对社会公众的权益保障。
(一)还原生产要素真实成本,扭转赢利背离价值创造现实
实践证明,不经约束修正的市场经济,资本对劳动者的强势会导致垄断、负外部性、公共物品短缺、收入分配不公及“金钱暴君”[6](P34)等一系列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作为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除了存在资本偏向造就劳动者权利的削弱及等级分化外,同时叠加出了政府主导造就市场权利的扭曲及异化、城市倾向造就农村农民农业的边缘及弱势、经济导向造就公众社会权利的减弱乃至丧失等问题,[7]表现在现实经济层面便出现了不少企业获得的各类生产要素成本远没有反映其真实社会成本,便宜的土地价格、廉价的农民工报酬、优惠的能源使用费用、低廉的环境污染成本、鼓励性的出口退税政策等等,使企业错误计算了自身的生产经营成本,导致不应运营的收不抵支企业不仅能够继续经营,甚至可以不断扩大规模,造成的畸形后果即是以公共利益损失为代价的个体或特殊群体利益能够不断增长膨胀。
(二)回归政府职能本位,确立商品定价话语权的市场决定地位
目前,我国企业生产的大多数商品,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中定价话语权地位差异迥然。国际市场上,我国企业面向出口的大多数商品,由于产品品质、科技含量或创意设计处于相对低端层次,且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日益严峻,导致商品的定价话语权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企业若想赢利,大多只能倾向于向寻求成本更低方向用力。对于不少企业来说,若无政府的出口退税及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企业很可能无法实现赢利。实际上,这些年来,我国牺牲了环境、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而为国际消费者们提供了巨量福利。国内市场上,改革开放后,资本优势地位使企业获得了商品定价权的强势地位,一些企业,尤其是那些身处受政府保护的垄断行业企业,即使所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低品质、低科技含量或低创意设计,照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虽然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拥有不同地位的定价话语权,但无论弱势还是强势,它们都不是基于纯粹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而取得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各类政策措施发挥了很强的介入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明确界定央地政府的职能限度,即中央政府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负责“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因此,各级政府就应该回归自身职能本位,逐步调整纠正所有影响企业商品定价权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朝“国际市场促使企业提高商品国际竞争力和国内市场倒逼企业最大化国内消费者权益保护”目标迈进。
(三)强化制度设计的正向激励,树立唯创新创造方可致富氛围
有学者提出,现实经济中,企业推动升级的最大动力也几乎是唯一动力就是产业升级后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8]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一直不力、不严、不刚,由是,企业经过千难万险,通过科技研发而开发的产品即使最终赢得市场消费者青睐,接踵而至的也很可能是低成本的假冒商品。若打击不力、应对不奏效,致力于研发转型的企业面临的前景只可能是:谁投入研发谁受损,而不是谁赚取到超额利润。毋庸置疑,如果我国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完善及执法效力,以“低”制胜的生产经营模式就仍将大行其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就仍将任重道远。同样,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设计,一度成为了让某些上市者短期暴富并圈钱离场的提款机。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质上都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设计中出现了令市场参与者成本核算和赢利空间计算失常且短期化的制度性、基础性误导信号,只有坚决纠正才可能让我国的市场机制真正实现有效运行。
三、加强各类影响市场机制规范运行的监管行为
市场经济下,利益动机的强大诱惑力使各类市场参与主体会在既定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下尽最大可能千方百计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种行为动机的广泛存在和强劲驱策力,政府及社会公众本无须大惊小怪,因为它原本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势的源泉所在。当然,如果一国市场参与主体整体上拥有较为高尚的道德感和较为崇高的伦理意识,确实能够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大大提升消费者乃至全体公众的幸福指数,但实现这点却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如果约束市场参与主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合理、不科学、不可操作,或者健全、合理、科学且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力,都将使市场参与主体的背德行为更为泛滥、放纵、不可控甚至无底线。
(一)全面清理既有法律法规,根据监管难度配置监管资源
目前我国出现的广受社会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公共设施安全问题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律法规及其执行力度难以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强烈的趋利动机、逐利行为及信仰弱化实际相适宜,应该是核心症结。不容否认,导致这种现象出现也与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更加偏重经济发展、重视GDP增长、强调资本优势地位的政绩导向高度相关。因此,由相应机构统筹,适当增加监管资源配置,逐个领域、逐个行业,分门别类清理我国既有影响市场机制规范运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修正其不合理、不具威慑力或不具操作性条款,并加大执法宣传查处力度,无疑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当然,清理并修改完善全国性的监管法律法规责任更加重大。
(二)强化执法力度,根据实效平衡加强监管与放松管制之间的关系
市场需要加强监管的领域很多,横向、纵向分类皆可。横向分类可以从行业领域进行,比如金融监管、食品监管、药品监管、物流监管等等;纵向分类可以从市场进入、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环节进行,比如资质资格监管、商品质量监管、安全生产监管、价格监管、市场秩序监管等等。对于价格监管,政府固然应该尽量不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实施行政性干预,但对于由市场参与主体自身进行的价格操纵及价格垄断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进行纠正和处罚;对于资质资格监管,政府对于市场参与主体进入市场的行政性壁垒要精减简化,但对于某些专业性强或质量安全要求高领域的资质资格监管却不仅不能减少降低,而且必须加强提高。根据莫里斯·克雷纳和阿兰·克鲁格的研究,美国国内的从业资格认证体系涵盖的职业种类不断增加,20世纪50年代约有5%的劳动力需要取得从业资格,而到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9%。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经济改革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大规模撤销工业和贸易活动所需的执业许可。[9](P140)该研究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监管不仅不是单方向的放松管制,恰恰相反,因为科技的发展、专业分工的细密和社会公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整体性提升,政府反而需要做的是加强监管。
(三)树立正确监管理念,根据目的防范行政干预变相复归
加强市场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市场主体设置障碍、增添麻烦,更不是为了给监管机构部门或其内的某些个人提供经济利益或其他非货币收益,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保护市场主体正当权益。当然,地方政府在加强市场监管过程中,也要注意防范三个不当倾向:一是防止监管权限滥用,使其成为地方政府保护本地落后生产方式或个别企业的工具;二是防止将市场监管演变成为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三是防止出现不公平,地方政府应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制定相应的规制标准,尽量避免采用按照企业规模、所有制、行业类型等设定标准。[10]
四、完善各类影响市场机制有序运行的维护行为
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而且其弊端表现是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干预介入逐渐加深拓广的缘由所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1949年后为克服市场经济体制弊端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的计划经济体制,两极分化等不公平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却接踵而至。为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我国确立并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升,民族开始振兴,人民生活走向富裕。但是,过度强调效率、经济发展之后,今天的我国公平问题开始凸显。实际上,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中一对重要且难以处理的关系。过度强调效率,可能因市场经济下各市场主体强烈且难以自抑的利益最大化冲动及其行为而损伤社会公平。过度强调公平,又可能因忽视且弱化能力、技能或体力智力付出更多的市场主体的贡献而减损整体市场效率。只有政府与市场分工合理,协调合作,市场机制才可能有序运行。实践中,各级政府完善各类影响市场机制有序运行的维护行为应包括以下几类:
(一)营造良法善治环境,夯实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严格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多姆霍夫指出:“与市场是自由的这一宣称相反,市场是历史建构而成的制度,依赖于政府对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认可与执行。”[11](P324)我国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要强化产权保护制度。只有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实现资本创造功能;只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创业创造热情;只有顺畅的契约遵从习惯才能保证规模日益扩大市场中各市场主体交易的低成本长期有序运行。深圳近年来创新创业型企业扎堆集聚且高速发展,契约执行程度相对较高功不可没。
(二)打造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平台,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建立起了体系相对完整、结构相对合理、规模不断壮大的多种市场平台,尤其是相对完善统一的商品市场,但受改革的渐进性、认知的成长性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性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平台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12]中指出,中国目前在经济、社会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均是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外在表现。事实上,生产要素市场的不成熟、不健全及扭曲,一方面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且低端化、低效化长期固化;另一方面,使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内需不足、环境破坏、正义缺失问题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和谐稳定乃至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的根本性桎梏。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已成为新常态下实现我国经济新跃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举措。未来,各级政府必须要下大力气确立生产要素市场平台的市场性特质,有序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平台的现实性建设。
(三)完善信息开放制度,拓展市场主体决策的质量空间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为主的经济体制。分散决策质量高低与空间广狭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能够获取信息的数量、准确程度及扩散的速度和范围。互联网时代,是否拥有大数据思维和善用大数据工具已成为各市场主体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然而,相对于市场上海量信息获取渠道与数量的井喷式增长,我国各级政府所掌握信息的开放程度相对滞后。当然,涉及国家机密和公民隐私的信息必须处于严格的保护之下,但除此之外的信息,很多其实可以更加有效地助力市场主体降低成本、正确决策及拓展市场空间。放眼国外,美国第一任国家首席技术官安尼什·乔普拉在《国家创新》中就给出了美国不少政府部门因为开放数据而促成产业繁荣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内观国内,我国各级政府在信息开放领域其实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转变信息部门观念、消除信息割据状态、标准化信息存储格式、开放信息下载权限等等,这些对于提高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及拓宽创新创造空间无疑将大有裨益。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安全网络
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取得离不开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激励。各级政府应健全并提高全体国民或地方区域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种类及水准,从而为全体公民或地方区域居民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大胆创新创造
提供安全保障。2015年,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导、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办的《一人二十元 健康保一年》的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就是地方政府筑牢社会保障网络的创新之举。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所指出的,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并不是市场经济的负担,而是它的必要补充;[13](P167)竞争原则需要由社会保障原则来补充。[13](P135)只有各级政府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维护工作,市场机制才可能实现有序且高效率运行这一理想目标。
[1]安宇宏.市场机制设计[J].宏观经济管理,2013,(1).
[2]李义平.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2).
[3]于长胜.新中国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历史回顾与前瞻[J].中外企业家,2014,(3).
[4]【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新华社.近九成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N].烟台晚报,2014-09-22(A26).
[6]张岩鸿.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规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张岩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弊端及政府责任[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4).
[8]沈坤荣,徐礼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展、阻力与对策[J].学海,2014,(1).
[9]【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0]张群,孙志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着力转变政府职能[J].经济纵横,2013,(6).
[11]【美】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2]陆宇.要素市场改革的进度表和路线图[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01-03(6).
[13]【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责任编校:张立新]
Rectification of Government Behavior Under the Decisive Function of the Market
ZHANG Yan-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s,Shenzhe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enzhen 518040,China)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This makes it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In order to achiev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th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by the market mechanism,which will make the enterprises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on capacity grow and make the enterprises represent the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 collapse.Because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market mechanism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far away from the reform goal which is to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ehavior needs to be rectified urgently.The rectified behaviors of gover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The government should eliminate all interference 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government should correct all misleading action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all kinds of regulatory actions that affect the normativ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all kinds of maintenance activities that affect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market economy;market mechanism;government behavior;rectify
张岩鸿(1968—),女,山东青岛人,深圳行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F043
A
1671-198X(2017)03-0033-06
2016-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