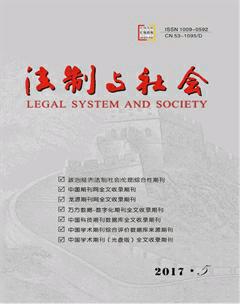《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前后对比研究
时颖臻 王新 李泽旸
摘 要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年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将就家庭暴力的范围存在争议(性暴力、经济控制、情侣关系、离异配偶)、人身保护令不规范、《反家庭暴力法》适用较少三个方面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关键词 《反家庭暴力法》 家庭暴力 范围 人身保护令
基金项目:合肥工业大学2016-2017年学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6CXCY271。
作者简介:时颖臻、王新、李泽旸,合肥工业大学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122
一、《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的范围确定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即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适用范围上《反家庭暴力法》强调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应参照该法规定执行,这就意味着同居者(现实中存在婚前同居、离婚不离家的同居)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也被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之中。此外,因扶养赡养关系、监护关系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也在家暴范围之中。在施暴方式上《反家庭暴力法》明文规定了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两类家庭暴力,并使用“等”字对其他家暴形式加以概括,有利于对新的家庭暴力形式予以规制,保障受暴者的合法权益。
反观现实,很多人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已不局限于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认识相对比较全面,但是并不明确了解法律颁布后家庭暴力的范围。在我调查研究小组的调查结果中,认为殴打、关押禁闭、因生育问题受到虐待、强迫性生活等行为属于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较多,较多人认为辱骂、训斥对方和不理睬对方不属于家庭暴力行为,这反映出很多人不了解精神暴力行为,对家暴行为内容的认知大多仍局限于身体暴力行为,这与法律宣传力度不够和公民法律意识不高也不无关系;超过60%的人认为情侣之间及离异配偶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不属于家庭暴力行为,我国法律将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同性恋人之间的同居关系以及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情况排除在家庭暴力范围之外,笔者认为,在我国,同性恋以及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情况本身与一般的家庭意义大相径庭,不受法律保护,关系本身是不正当的,在这些范围内产生的暴力行为也就不属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范围,不受《反家庭暴力法》调整。
在施暴方式上《反家庭暴力法》也未将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这两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行为的人数的比例并不是最少的,这也侧面体现了相关法律将此纳入家庭暴力范围的必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法》在家庭暴力的范围确定上存在不足。
(二)人身保护令
不可否认《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使得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批准、执行和效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问题,调查小组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分别为:一是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清;二是代为申请人范围、权利较小。下面将进行详细论述。
1.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清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由人民法院实行,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妇联辅助执行,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人员等问题法院并没有承担主要的执行责任,多由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妇联等机构对人身保护令的执行进行落实。但是由于《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各機构的职责,就造成各机构的相互推诿,使人身保护令难以落到实处。
2.代为申请人范围、权利较小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受害人的近亲属、相关组织和国家机关包括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村)委会、庇护所、妇联组织、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都可以作为代受害人申请人身保护令。虽然规定了较多的机构,但家庭暴力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如果不是受害人主动要求这些机构代为申请人身保护令,都是难以发现受害人遭受了家庭暴力的,此项规定的立法目的就难以实现。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只有在受害人客观情况不能申请的情况下,其他机构才能代为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本身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丑”不愿意申请人身保护令,其他机构是不够强制为其申请的。这就违背了《反家庭暴力法》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初衷。
(三)《反家庭暴力法》司法使用度低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反家庭暴力法》的使用度比较低,大多数法院在新法实施的一年中未使用过一次新法,除了新法实施时间较短、家庭暴力本身的隐秘性和受害者本身认为是“家丑”的原因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1.新法宣传不够
这里所说的宣传指三个方面:
(1)在新法出台后具有宣传职责的机构(如:群众自治组织、妇联、网络、新闻媒体等)对《反家庭暴力法》进行宣传。笔者了解到这些机构虽然进行了宣传但只是流于形式,效果并不显著。在所有被调查的人中有44.22%的人不知道《反家庭暴力法》的存在,并且其中大多数被调查人的信息来源于网络或媒体。有43.54%的被调查者所在地区没有进行《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有39.46%的被调查者不清楚所在地区是否进行过宣传。由此可知,对于新法的宣传,特别是基层组织所做的宣传工作并不到位,将宣传流于形式。
(2)进行长期、定期的宣传。庐阳区法官刘晓莉在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在法令刚出台的一段时间内,媒体关注度比较高,各方宣传也较多,公众知晓度也较高,但常态宣传没有跟上,时间久了,公众就淡忘了。在实践中本身各机构对于《反家庭暴力法》的首次宣传就流于形式,同时后期也没有进行补充性的宣传,必然使得公众的知情率不断下降,令《反家庭暴力法》无人问津。
(3)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创新点进行重点宣传。在问卷调查中以《反家庭暴力法》将冷暴力列入家庭暴力范围为例,在知道《反家庭暴力法》的55.78%的被调查者中只有43.9%的被调查认为“长期不理睬对方”(冷暴力)属于家庭暴力。由此可知,对于《反家庭暴力法》内容的宣传不到位。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工作存在较大的问题,如果公众本身对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并不了解或者根本不知道法律存在,这样的法律也只能被搁置。所以应当重视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才能使其发挥真正的作用。
2.公众的观念本质上没有改变
通过问卷从表面上看有97%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违法或者犯罪,也会在遭受家庭暴力后选择报警或者向妇联或居委会(村委会)寻求帮助,只有0.68%的被调查者依然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务事。这证明公众对于家庭暴力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本质上公众任然不愿意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合肥市逍遥津派出所为例,他们2016年共调解事件1000余件,其中家庭暴力占26%。但调解人员发现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接受调解之后,往往会放弃追责,多数受害人只是想给施暴人“一个教训”,而非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占每年调解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七成以上。受害人本身不愿施暴人受到法律的惩罚,不仅会使得家庭暴力反复发生还令调解人員只能充当“和事佬”,对家庭暴力的解决难以起到作用。
二、问题解决建议
(一)家庭暴力范围的确定
笔者认为情侣之间或离异配偶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反家庭暴力法》所调整的范围,不受《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但经济控制和性暴力应当列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受到《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1.将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是在与国际接轨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1993)第一条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系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国际上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是包括性暴力的,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经济控制,但笔者认为家庭成员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严格的经济控制无疑是对受害人精神上(自尊、自信)人格上的伤害。将家庭暴力的概念与国际接轨,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的交流。
2.中国对性暴力、经济控制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本身就是认可的
在2008年的《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提到家庭暴力的概念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由此可知我国将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有理论基础和可能性。
3.现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性暴力
在《审理指南》中将性暴力定义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笔者认为性器官属于自然人身体的一部分,性暴力属于对受害人身体的残害的一种方式,即使法律没有明确写出性暴力属于家庭暴力,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将其列入家庭暴力的一部分。
(二)人身保护令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将实践中人身保护令存在的问题其总结为二个方面,分别为:一是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清;二是代为申请人范围、权利较小。笔者针对这二点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1.将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机构作为人身保护令的主要执行机构,原因在于其距离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最近,联系最为密切,可以及时有效的监督被申请人的行为,关注申请人的生活情况,给予准确及时的帮助。同时还应该明确居委会(村委会)、公安机关等执行机构的具体职责。例如定期的回访、对被申请人的监督等。具体职责的确定不仅有助于执行机构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明确了《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界定,杜绝各执行机构之间相互推诿,将人身保护令落到实处。
2.将医疗机构纳入代为申请保护令的待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多数情况下是会选择就医,医生的专业知识可以判断受害人伤痕形成的原因,所以在医疗机构中家庭暴力的暴露的几率会增大,鉴于此将医疗机构纳入代为申请保护令的代申请人具有较大的可实施性。
为避免受害人本身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丑”不愿意申请人身保护令,笔者认为除了扩大代为申请人的范围,还应当扩大代为申请的权利,允许其强制为被害人申请人身保护令。
参考文献:
[1]夏凡.《反家庭暴力法》中的救济机制研究.安徽大学.2016.
[2]孙晓飞.家庭暴力防治中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研究.河北经贸大学.2016.
[3]薛宁兰.反家庭暴力法若干规定的学理解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