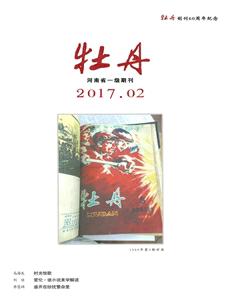《大漠祭》中的西部人文精神观照
尹顺民
《大漠祭》作为一部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反映西部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获得了世人太多的关注和赞誉。雪漠在中国西部生活了几十年,他已谙熟甘肃凉州地区的乡土乡情、民风民俗以及一草一木。在《大漠祭》中,他忠实地记录了西部农民的狩猎民俗、民间信仰、婚姻民俗、饮食民俗以及民歌民谣等生活风景、风俗、风情,还原了西部乡土文化的原始面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化世界。雪漠看似平静地述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但本质上是在深刻思考西部的乡土文化和西部的人文精神。这种深掘人文的思考在理性上赋予了西部人文精神世界以生动的意蕴,其存在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中国西部神秘文化的“符咒”。
《大漠祭》是一部表现当代西部农村生活题材的长篇乡土小说。雪漠自小受到凉州文化的浸润,在《大漠祭》中透露了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文化情结,他用史诗般的笔触抒写了中国西部农民在酸甜苦辣的生活百态中表现最直观的感知和最深切的感叹。雪漠所处的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境以及大漠边陲的放牧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假如说西部寂寥困苦的生活锻造了雪漠自身的韧性和坚强,那么那片踏满他足迹的黄土地则是他洞穿整个西部的聚焦镜。通过这样的黄天厚土,流淌在雪漠身上的人文细胞充满激情而急剧扩张;依靠着这片黄土地,雪漠破解着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人类战天斗地的命运;诚然,也就是这片黄土地,塑造了雪漠和他不朽的小说《大漠祭》。雪漠对于西部黄土地的真情实感、西部人文精神的探索、宗教文化的感悟,促其定位在本质上探究一个时期的西部农民生活的片段甚或整体而耕耘不辍,恰似行走在戈壁沙漠,用粗犷悲惋的歌声咏叹西部农民特有的磅礴豪放和朴素睿智。
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雪漠《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
《大漠祭》以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为写作特定的背景环境,描写中西部农民在偏远、狭陋、贫瘠、落后的地域中的生存状态。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农民无不为生活的艰辛唏嘘与哀婉,无不为这里同胞的生生死死挣扎落泪与思索,一生中充满着战天斗地的倔强。西部农民在战天斗地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期颐能过上衣食保暖甚至于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虽然生活总是十有八九不如意,天灾人祸也总是在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时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像老顺一家这样在贫穷的生活重压下苦苦挣扎的西部农民,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心中理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神奇的西北风情以及浩瀚的大漠風光,有点矛盾的邻里邻居的生活冲突,形形色色的西部文化和特色人文精神,繁重辛劳而又艰苦的生活现实,加上雪漠入木三分的生活情感体验、对命运的个性化本真化的领悟,使小说《大漠祭》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感人魅力。这样西部农民生活的景象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他们的生活现状应当是:在沙漠边缘生活着一群战天斗地的农民,他们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这种情形好像沙漠一样呈现着浑厚的、酷厉的景象——那是一种沉寂和荒寥,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固有的沉寂和荒寥,那是没有声音和生命迹象,却能人感到涌动的生命力的雄浑和苍劲。从内容看,正如雪漠《从“名人”谈起》(自序)中说到的情景,他想创作和描写的,恰恰就是西部沙漠边缘一户农民一年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生活,他的家庭苦难的一年何尝又不是他们全家人度日如年的一百年。其生活场景或小说的基本组成无非就是训练兔鹰、捕捉野兔、煮(炖)吃山药、喧谎谝话、捕打狐狸、田间劳作、偷情骂俏、祭神捉鬼等;换句话来说,雪漠写的无非是爱情的幸福和甜蜜、生活的艰苦和寂寥、病痛的无助和凄婉、生死的无奈和绝望而已。但是纵观历史长河,这无疑是西部农民生活中小而又小的生活琐事,然而正是这些琐事构成了西部农民的整个人生。这些只言片语中裹挟着西部农民生活独有的黄土地气息,倾注了雪漠浓烈的乡土意识,以怜悯慈悲的胸怀,关注着为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的西部农民群体,抒写了一段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西部农民战天斗地的历史,也毫无掩饰地倾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小说家应有的胸襟。正如雪漠所说:他只是想平静、祥和地告诉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有一群西部农民他们似乎很坦然、很幸福,但又很无奈、很艰辛地活着。《大漠祭》带着黄土地泥土清香的信天游似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气息,喷薄而出的是中国西部最普通的农民形象。自得其乐的鲜活生活场景,明白晓畅的个性化语言,显示出雪漠常年扎根乡土而汲取深厚西部人文资源的精神情怀,亦向众生传达了中国西部独有的乡土乡情以及粗犷而又淳朴的人文风貌。
文化是土地之魂,土地是文化之魄。与时俱进,直指人心,文化趋向大善,土地趋于大美。
——雪漠《光明大手印:智慧人生》
所谓“西部”,这里特指中国的西部,是文化传承的西部和人文精神的西部。有了“西部”这样一个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区域划定,人们就明确了文化研究的地域范围和空间对象。中国西部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不必言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伏羲,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身伏羲之妹风姓女娲,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等,其足迹不仅遍及中国西部,更是开创了中华优秀文化之光。曾经大到中国西部,小到甘肃,就有实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祖籍在甘肃,也有历史文化名人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诗仙”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祖籍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唐代散文家、哲学家李翱,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著有《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唐代著名传奇的作家李朝威,祖籍陇西( 今甘肃东南部 ),与李复言、李公佐合称“陇西三李”;也有被钱谦益称其“诗不操秦声,风流婉转,得江左清华之致”(《列朝诗集》)的明代散曲家金銮亦是祖籍陇西(今属甘肃)等。这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那里以石窟及壁画而闻名天下,有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敦煌。这些厚重的黄土地孕育的人类先进文化和先贤智者,历久弥新地影响着历史、影响着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时代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以及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孕育人才以及文化作品的重要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没有这个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理论上很难产生出非常优秀的人才及文化作品。如果这个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非常肥沃,那么遇上适宜的气候,并在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滋养下,加之健康的种子,就会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及文化作品。其中,很有可能长出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文化巨人、文化大师,当然必然会产生出泽被后世的鸿篇巨著。
这大概就是《大漠祭》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的原因吧。一方面,中国西部就是雪漠生长的肥沃土壤,他也是遇上适宜的气候,在播下健康种子后成为了优秀乡土文化、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另一方面,雪漠虽说《大漠祭》“是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动笔时,我才25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但这也理所当然成为雪漠在十年如一日辛勤耕作中遇上适宜的气候,播下并收获的健康种子。他在这样广袤无垠的文化土壤里寻觅、耕作,就一定会将近似原生态的父辈生活写成妇孺老幼皆宜、读来如话家常的名作。这幅作品呈现了一种真实而悲怆的西部农民生存情景——老顺们的悲剧,是经济上的贫困所致,是温饱、生存,乃至人性的问题。贫困和无助、悲哀和沧桑、无奈和辛酸使中国西部农民的生活充满了悲情色彩。然而,作品的基调悲怆而不绝望,老顺的坚忍与乐观,孟八爷的睿智与豁达,都体现出西部农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力与灵动的生存智慧。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可以说《大漠祭》是时代的产物,是雪漠智慧和毅力的结晶,体现了雪漠把握时代律动的敏锐能力,展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也才有了雷达先生所称的《大漠祭》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人们也大概理解了雪漠的“文化不掠夺土地,土地不挤对文化”“文化是土地之魂,土地是文化之魄。与时俱进,直指人心,文化趋向大善,土地趋于大美”的深层次内涵。
在我的心中,每一个小说人物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思想与追求,也有着各自的命运,我不会去干预他们,就像一个母亲不会干预腹中胎儿的成长一样。
——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
雪漠说:“真正的孤独是智慧的觉醒,是感悟生命的易逝、世间的无常和作家想建立的永恒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是独上高峰望八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然,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冷寂。”相对于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小说界,《大漠祭》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亦或文坛对其的高标准评价甚或西部乡土文化对文学界的冲击无疑是强烈的。这种影响源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历史画卷,是平平常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作者将一滴滴生活琐屑,汇聚成了作品的伟大。当人们再次审视《大漠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因素,发现文学界对《大漠祭》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的认为雪漠以其自身的真情实感、叹为观止的叙事状物的笔法,创作出了神奇的西部乡土和民风民情以及沉重的生存现状;有的认为这种真正描写或创作西部黄土地农民原生态的小说,又同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以及视觉冲击力的小说真的是太少了;有的认为《大漠祭》描摹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西部老顺们的生活状态,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切,是对西部人文精神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意义;有的认为《大漠祭》得力于对中国西部农民人文精神品质的深刻探索和挖掘;还有的认为《大漠祭》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西部农民的痛苦蜕变和战天斗地精神的凝练,反映了他们在艰辛的生存境况中,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无论多大或多高的评价,《大漠祭》总是凝结了雪漠的心血,是他花费了二十年的生活经验加之十多年的辛勤孕育,才将其情感和生活原动力欲望发注笔端有感而发之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父老们的“许多情绪”,有悲哀、有无奈、有辛酸,更有希望,“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雪漠语)。在书中,荒凉严酷的自然条件,瑰丽奇幻的大漠风光,老顺们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构成了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风景——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物质与金钱充满人的现实生活的情景下,还能对中国西部农民命运的力透纸背的揭示与关注,在于对中国西部原生态自然风光的抒情化描摹,在于对西部农民整体的人文关怀的深沉呐喊,在于内心深处蕴藏的对老顺们深切的同情与沉重的忧虑。在这一切平静的审美意象与艺术形象的描写中,倾注了雪漠的悲欢离合和哀痛之情,时时处处可以感知到雪漠跳动的脉搏、滚烫的眼泪、温和的笑容、虔诚的祈祷以及救世的宗教心理。雪漠作为大漠世界的一员,拥有这里的一切,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样样有份,他成了这里的“代言人”。《大漠祭》的真实,是它震撼人心的有力武器。雪漠用“大境界、大胸怀、大悲大悯、无缘大悲、同体大悲”的佛家胸怀,将写文与做人结合起来,知道自己一生为什么而活着,知道自己一生要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创作,要做出理智的抉择。乡土文化寫作和日常繁冗生活都是要有所坚守,不能轻而易举地被文化界鱼目混珠的观点和表象所困扰、甚至有所改变,不能趋同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是非不分的观点和主张,用那些观点和主张来约束自己自由的心灵——这就是大智慧,一种智慧的清凉与觉悟,显示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高贵良知,为文化界甚至是时代都增色不少。因此,雪漠的作品承传的是一种十分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和西部特有的人文精神,承传了整个时代文化界甚或小说界对西部特色人文精神的思考,这种情怀、精神与思考,随着雪漠诸多作家的作品一同承传开来,就可能影响中国西部甚至中国的年轻一代人,让他们通过优秀的西部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西部,了解中国西部的人文,了解中国西部憨厚淳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
再来看《大漠祭》。它作为一部用现实主义笔法创作的反映中国西部农村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了鲜活、通俗、简洁、质朴的农村化或农民化的语言,处处彰显着非常有特色的西部民风民俗文化,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奇幻无比而又瑰丽神奇的大漠世界。例如,为了展示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农民独具特色的捕猎场景,雪漠描写了孟八爷教灵官如何分辨狐狸的踪迹——辨踪是一门非常有生活经验但又难以掌握的生存学问。在《大漠祭》第三章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孟八爷先教灵官辨‘踪。‘踪就是狐子在觅食后留下的足印。为了生存,狐不能不觅食。一觅食,猎人便跟‘踪追击。‘踪分三类:夜踪,五更踪,亮踪。夜踪是狐子在半夜之前留的足印。五更踪是五更后留的。亮踪是天亮留的。‘夜踪几乎无用,‘狐颠颠,人三天。狐狸夜里留的踪,没两三天撵,连个狐毛也见不着。有经验的猎人不追‘夜踪。‘五更踪可追,但累,从凌晨追到日落,或能见得狐影。‘亮踪最佳。狐的习性是昼伏夜出。按孟八爷的话,一见太阳,狐狸的头就疼,必须找个地方歇息。一见亮‘踪,不用半日,便能见到在柴棵下歇息的狐子。寻踪易,辨踪难。狐足印似狗,五点梅花,印在蠕蠕细浪上,笔直射向远方。寻常时候,狐很少拐弯。沙湾的猎人中,会寻踪的人多,但真正会辨踪者,只孟八爷一人。孟八爷打狐子,如探囊取物。”
这段充满智慧的“寻踪易,辨踪难”的讲解,给灵官学习辨踪猎狐上了一堂课——对狐狸等沙漠里的动物的活动规律、追踪猎捕的思考和摸索、总结经验及实战运用,是雪漠长期生活在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特定环境的一种真实感悟,也是西部农民在艰苦环境中能够生活的独特生存技艺,是老顺们一辈子狩猎生活知识的积累,更是西部人文精神世界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张扬着西部农民的生存哲学和人文智慧,孟八爷的形象也就成为西部老顺们的一种象征。
再举一二例加以说明。例如,第一章花球和孟八爷猎鹰的一段对白:“花球皱眉道:‘你尽说这些,把人的信心都说没了。孟八爷说:‘这可是好话呀。啥有个够的?有了吃,想穿;有了穿,想富;有了钱,想嫖……哪有个尽头?霸争了天霸争地,临完了,谁都霸争个四块棺板。”土头土脑的花球,在孟八爷的眼里,就是一个无聊时消遣时光的小娃子,但孟八爷看破红尘的几句话,活画出一个被苦难命运磨光了棱角、逆来顺受的“老顺民”的心态,使用着“霸争了天霸争地,临完了,谁都霸争个四块棺板。”这样极普通的字句,却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是西部老顺们的普遍心态,在接二连三的生存打击与命运捉弄面前,老顺们默默承受着一切,雪漠在《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中说:“他没有力量改变贫穷,但却是心灵的富翁。他可以哀叹,可以哭泣,但从不绝望:‘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老天能给是老天的能耐,老子能受是老子的尊严。”这种人格和尊严可看作老顺们这样的农民的强悍坚忍和蛮勇任性的生存观念的精彩勾勒。孟八爷教给花球的生存哲学和人生的智慧,以及无意间流露出苦吃勤做的满足感,代表了西部农民的豁达而又苍凉的生活品质,别一味强调战天斗地,还要顺其自然,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现状,顽强地与命运地抗争。
再如《大漠祭》第二十章憨头得癌将死时的描写:“神婆走后不久,憨头闭上了发涩的眼……思维恍恍惚惚地游荡着。疲惫,极度的疲惫,而又难以入睡。是耗干了精力的清醒,是衰竭的清醒,是清醒的迷糊,是能理性思维却无法摆脱的噩梦……健康消失了,才知道健康真好。健康是最大的幸福。”雪漠在《世界是心的倒影》中说:“无常无法抗拒,但它并不可怕。”《大漠祭》将人的生老病死,唯心地交与神婆和命运之神主宰,这是西部老顺们的生存哲学和普世之道。“健康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世人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更是生活在西部大漠边缘老顺们的所求。雪漠将大众语汇的矿藏加以提炼,不仅让西部人民能看,还让全国读者欣赏,这是“纯洁祖国语言”的神圣职责,更是雪漠极力重视的一个表现。在当今这个太需要精神的钙片的时代,《大漠祭》表现出雪漠对西部农民悲剧命运的发自肺腑的思考和人文精神真谛的哲学化和宗教化的探究,作品中的民间小曲、方言土语的独特性写法,在于从生存状态的意识中和人文精神的视角关注中,洞悉黄土地农民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间,并以此为出发点,达到探究人如何活着和如何活得更好的一种体验,从而挖掘出人为何活着的真实意义和价值。这大概就是有人说《大漠祭》写绝了沙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体印证吧!
我的作品,都是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而不是自己刻意为之的东西。
——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
除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老顺们、真实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贫瘠的土地也生长着快乐的因子。例如,年长者训斥后生小辈规规矩矩生活,不说“豁出我这条老命,和你小子拼了”,而是说“豁出我这张老羊皮,换你一张羔子皮”,这是因为雪漠极其熟悉家乡丰富的民间方言而折射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又如,家庭子女众多,但个个还要老人费神操心,就说成这样“老母牛养了十个牛,事事留不了老母牛”。比喻非常生动形象,语言鲜活明了。再比如,描写青年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话,双富的媳妇这样说:“其实,你心里的嘀咕我知道,你是童子鸡儿,我是二婚头。”猛子笑着说:“啥童子鸡呀,早踩过蛋了!”这种含蓄而又直露、放荡而又风趣的话语,随手拿来,不露任何痕迹,雪漠通过这样的对话将两人描写得淋漓尽致,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当然还有一些民俗民风和乡土乡语,把执行死刑这样恐怖的事情,轻而化之说成“吃铁大豆”,把手铐说成是“罗马表”,把人民币说成是“票老爷”等。这种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对雪漠小说语言特色的评价是非常恰切的。
中国西部的乡土小说蕴含着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元素,积淀了博大而深厚的西部特色文化和人文精神特质。这些文化和特质是将西部乡土小说与其他文学类别区别开来的典型特质,使西部乡土小说展现出极强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张力——西部文化的雄宏与博大、粗犷与平和等。雪漠在中国西部生活了几十年,他已谙熟甘肃凉州的乡土乡情、民风民俗以及一草一木。在《大漠祭》中,雪漠如实地记录了西部农民的狩猎民俗、民间信仰、婚姻民俗、饮食民俗以及民歌民谣等生活风景、风俗、风情,再现了西部乡土文化的原生态面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化世界,而老顺们依然过着艰辛凄凉却与世无争的耕耘收获、繁衍生息的生活。可以这样认为,雪漠是有意识教化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也不要认为乡土文化是愚昧的标志。相反,西部乡土文化以及西部乡土人文精神正是滋养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汪清泉,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净化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人已经渐渐麻木的有个性、有信仰的高贵灵魂,提醒西部农民甚至中国人都应该健康地活著。这种乡土小说的构造和表现,道出了雪漠题记所说:“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
雪漠的《大漠祭》,它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在雪漠看似平静叙说西部特定区域条件下具有特定西部人文精神的老顺们的背后,人们能够深深体会到的是雪漠对西部黄土地文化和西部人文精神的深刻探索和思考,这种探索和思考在人文精神的本质上给予了西部人文精神世界以生动的意蕴,其存在的人文和社会价值,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中国西部神秘文化的“符咒”,也感悟到了雪漠通过了苦苦的挣扎乃至心灵的裂变,传递着西部知识分子和乡土文化母体之间的复杂联系,并将其置身于纯粹、透明乡土文化中,褪去不实和虚妄,回归到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一种因为真实、善良、美好、大度、崇高而变得谦和而灵动的人的生命自然状态。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