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的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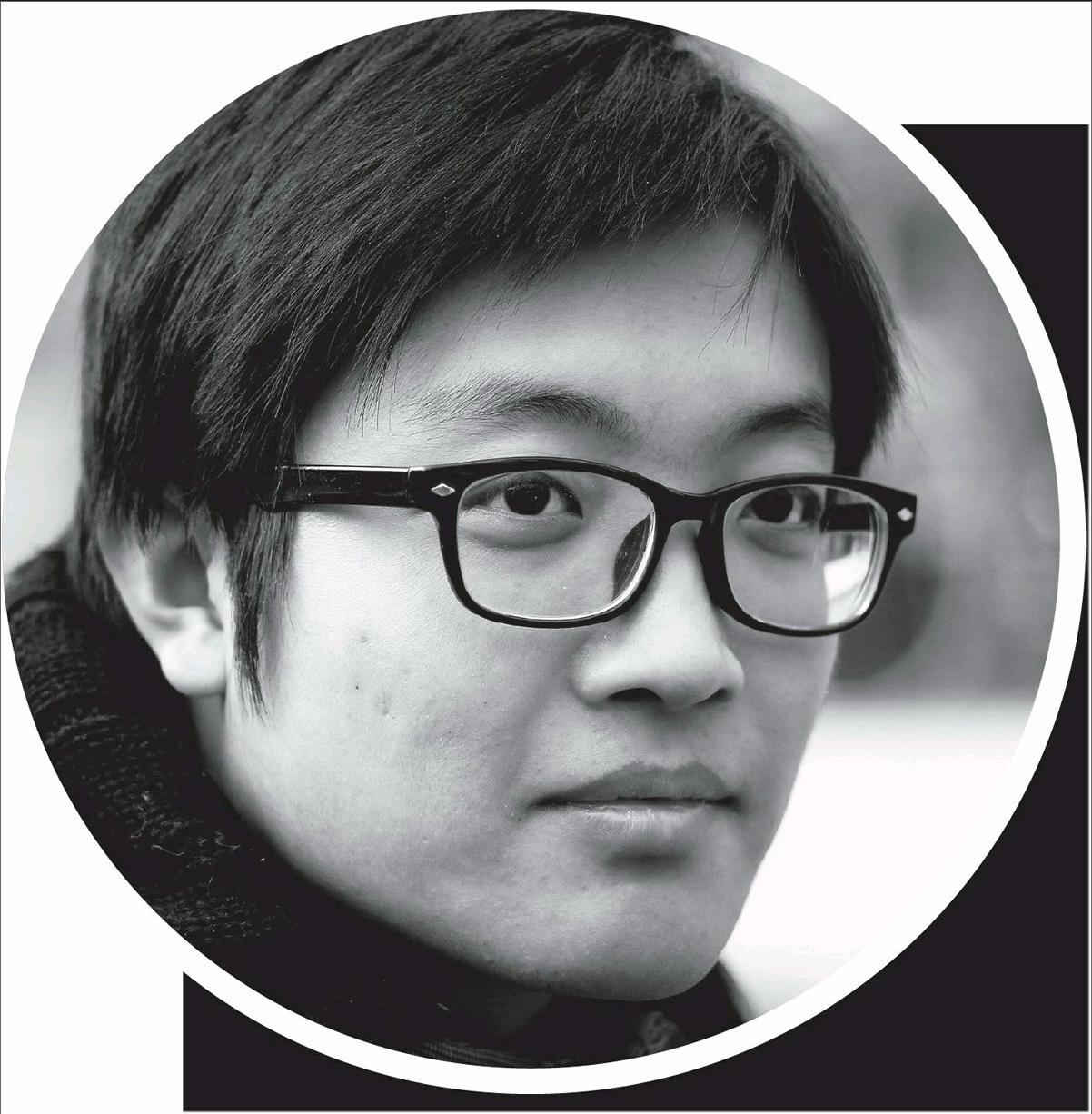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曾有小说发表于《十月》《钟山》《芙蓉》《天南》等。2017年将出版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湖南文艺出版社)。
1
他终于来到这里,一个破旧的剧场。那是一个晚上,他的腿上还带着旧伤。其实不是旧伤,因为他能够感觉出,疼痛的那个地方,依然流着血。月光下,血液凝结,又流出来,然后再次凝固。结痂的地方像是矿藏般闪闪发亮。他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膝盖。安定下来了,回忆便涌现。他行走在一条荒芜的公路上,一条狗也看不见。只有汽车的残骸堆积在一起,似乎这里曾是某个汽车修理厂的旧址。公路两旁刮着干燥的风,灰尘积蓄在他的鼻孔前。他的胡子已经很长了,这是漫长的徒步旅行中不可避免的。其实他还很年轻,他的胡须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外貌,这使他感到安心。
公路的尽头是一片平原。他行走在平原上。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踏上这条路。是为了逃离吗?还是为了追寻什么?道路太漫长了,漫长到他几乎忘记了初衷。这可如何是好。他看到了粗壮、高大的野花,还有沉默的牛,像是岩石一样。羊群慢慢地挪动,却看不到牧羊人的身影。他像是一条细线穿过平原,来到这座城市的郊区。他找到了这个破旧的剧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回忆暂告结束。
城市里正是夏天。即使是在夜晚,炎热仍使他难以入眠。他躺在空荡荡的戏台上,身体的一侧面对着观众席。当然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整齐排列的空座位沉浸在幽暗中。他难以入眠。他呼吸着从自己身上发出的难闻的味道。有时,外面会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呼啸声,伴随着的还有一束急速的灯光,从窗子划过他的脸。每当这时,他会突然惊醒,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片刻,重归寂静。
他没有钱。就在他踏上这条道路没多久,也就是说,刚刚告别了悲伤的父母,离那个叫作“家”的温暖的地方越来越远时,一个傍晚,他被突然打晕了。醒来后天正下着雨,他整个人浸泡在积水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呛醒的。他的行李、证件和钱全丢了。现在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衣服不知穿了多久,早已发臭、肮脏,看上去与一个拾荒者无异。
因此,在他的梦里出现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就不足为奇了。面目模糊的男人手里拿着发蓝的匕首,在追杀他。他在公路上没命地奔跑。望不到尽头的公路,唯一的尽头就是天际。星空旋转着,嘶鸣着。
他醒来时似乎产生了幻觉:观众席上坐满了人,他们统一面目模糊,胳膊放在扶手上,安静地坐着,静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他吓得赶紧闭上了眼。
终于到了白天。剧场开始明亮起来。然而这明亮只进行到一半,突然中止。于是,整座剧场一半被照亮,另一半依然是昏暗不清的。要说明的是,他刻意使自己不喜欢囚禁的感觉,他渴望人群。他走出剧场生锈的大门,融进明确的阳光中。
2
他感觉自己已经老去了。他用一根木棍探索着前方的路,就像伸出一只触角那样。他有时必须靠木棍支撑住身体,因为他的腿依然在流血,因而变得虚弱、柔软,无法扛住他并不算高大的身躯。他走在道路上,留下斑斑点点的血迹。有孩子跟在他身后,尖叫着,欢呼着。就像是闻到血腥气味的秃鹫,他想。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这是一个集市。人很多,两旁是贩卖各种物品的小贩。在城市的中心,有整洁、明亮的购物超市,但人们為什么还聚集在这里呢?这个遍地垃圾、恶臭扑鼻的地方?还不是因为价格便宜嘛。这里的人会更富于同情心吗?他找到一个空位,坐在地上,用木棍敲打着地面。尘土噗噗地被拍打起来。人们来来往往,阳光太炽烈了,他只能看到人们的鞋子。
这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人们大声争辩着,交谈着,用他听不明白的方言,其间似乎还掺杂着咒骂。灰尘扑扑的动物们被主人牵引着,也走在这条路上。最开始是斗志昂扬的鸡鸭,接下来是温顺的绵羊,它们挤成一群,拥挤了道路。它们的毛发已经变得很脏,再也不是那种雪白色了。后面是更大型的动物,例如沉默的老牛,甚至还有骆驼。它们依次走过。阳光越来越浑浊。他几乎要睡着了。梦中他似乎看到了另一些庞然大物从自己面前走过。是大象吗?还有那些似乎比大象还要巨大的东西……他睁开了眼,因为他听到了钱币叮当的响声。没错,是一枚钱币,在他眼前闪烁着。接着还有一些揉成一团的纸币,陆陆续续地,扔到他面前。他只是垂着脸,感觉自己已经老去了。血不停地流。血会有流完的一天吗?大人们匆匆走过,只偶尔有孩子会认真地打量他。
这时,一个女人站到他前面,并且艰难地蹲下身。无疑,这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她的肚子凸起已经很明显了。她用围巾遮着半张脸,手里拿着一个像是试管一样的小玻璃瓶。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柔地挽起他的那只流血的裤腿,将玻璃瓶放在伤口下面。于是血一点一滴地流进玻璃瓶里。
天气很热,苍蝇不时成群聚来。他用木棍轰着苍蝇,叫它们不要来打扰这个女人。不知过了多久,血已经装了半瓶。女人用木塞塞住瓶口,慢慢站起身,扔下几枚钱币,加入到人群中消失不见。他始终没有看到女人的脸。
他记起还在赶路的时候,听闻过一些奇怪的习俗。他还记得自己曾走入过某个类似海市蜃楼的地方。那时他正在费力穿过一个小沙漠。道路两旁长满了带刺的热带植物,然而在类似海市蜃楼的地方,他见到了养在玻璃缸中的鱼,还有一些习惯喃喃自语的人。他还记得有个人曾出来迎接他,对他说:“看见你回来我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一去再也不回来啦。”
那个时候,他记得,太阳正偏西。
3
演员是在午夜时分登场的。不是鬼魂,而是演员。他注意到他们岁数都不小了,而且都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他们的岁数也并不大,可能还没有他岁数大。也就是说,他们处在年轻的末端,皮肤开始变得粗糙,但还没有人承认他们属于老年。
他们之中有人甚至还带着狗。狗在月光中东瞅瞅,西嗅嗅,唯独对他不感兴趣,仿佛他不存在一样,仿佛他才是鬼魂。而他们,同样对他并不在意,就像对这样前来寻找庇护的流浪汉司空见惯。他蜷缩在角落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视觉与听觉里。
演员们纷纷脱下大衣,放在空椅子上,然后聚集在一起,口中念念有词,从内容可以判断是某出戏剧的台词。忽然,他们又分散开,各自为政,在属于各自的角落里喃喃自语,那种感觉,如同在朝着黑暗中看不见的东西祈祷。
离他最近的是一个上了点岁数的胖男人,我们称呼他为甲。甲几乎就挨着他,但对他并不关注,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
“我开始拿定主意……我这一辈子老是拿不定主意。”
说完,甲似乎不满意似的缓慢地摇了摇头,露出痛苦的神情。狗在吠。他盯着甲的一举一动,发现自己的一部分身体正被月光照耀着,于是他稍稍挪动了地方,使自己完全隐没在黑暗中。演员们在舞台上来回走动,模仿着戏剧中的段落,踩得地板嘎嘎直响。
他想起在路途中,曾见过的那些流浪者。他们也总是喜欢这样自言自语。是的,道路漫长,大部分时间里必须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自己跟自己玩,自己与自己做斗争。那些流浪者,完全沉湎于自我意识里,就像是陷入一只泄气的沙发。狗不停地吠。
他回过神来,发现甲正盯着他看。那样子可以称得上目不转睛吧。这时,他可以确定,甲浮肿的脸几乎是一个小老头了。“一个人独自赶路,路就显得特别长。不是吗?”甲露出笑容,然后戴上一顶棕色毡帽,朝大门口走去。演员们跟在甲的身后,鱼贯而出。此后的日子里,他丧失了时间的概念。雨下了又停。道路上曾遇到的各种事件与幻觉,轮流地折磨着他。还得加上梦境。每天晚上,他像是发烧一样地进入睡眠。
贼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早就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家伙,戴着白色口罩。有一天,他蓦地从梦中惊醒,发现那个贼就在身边。有个形容词是怎么说来着,对,四目相对。他思忖自己没什么可偷的,没错,他一无所有。可这仍然令他恐惧。他想,自己一无所有,才可能失去得更多。于是他不再睡觉,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难事,赶路时他经常忘了睡觉。终于在一天晚上,他等到了。先是影子,从月光中探进来。他手里握着一块尖锐的碎玻璃,朝那个影子后面的人刺去。那个人哼也没哼,倒在地上。
他费力地脱下他的皮夹克,还有他的其他衣服,包括口罩。接着,他脱下自己的所有衣服。他换上他的衣服,包括皮夹克还有口罩。然后,他为他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做完这一切后,他将他拖到剧场外面。剩下的,就不是他的事儿了。他抬起头,广阔的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也就是说,今晚即将变成昨晚。
4
那条路,白色的,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当他躺在布满灰尘与脚印的破旧的戏台上,四周没有人,所有的椅子都对着他,椅子上没有人。阳光从窗口一照进来就变浑浊了。现在是白天。悠扬的叫卖声从不远处的集市传来,断断续续仿佛来自他的梦。那种时刻,半睡半醒,梦境还没有从眼睛里褪去,仍保留一枚薄薄的壳。他站起身,望着窗外。阳光太明亮了,他什么也看不到。这倒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就像是逃亡的那段日子。白色的逃亡之路。他的意识时常是模糊的,由于体力不支,也因为太过寂寞。人还是应该与同类接触,否则脑子就会退化。堆积的幽暗将把脑壳里所剩不多的光亮慢慢挤掉。他行走在密林里,行走在旷野之上。他的头顶是大团的云朵。只有道路是永恒的。而且他必须要快,他知道自己的同类在搜捕他,这有什么办法呢。旷野上经常遇到的动物的残骸,被风干,露出的骨头看上去被打磨得很干净。
对于赶路者来说,这样的场景是很常见的。那些骨头与残骸,他可以轻易地辨认出哪些是属于同类的,比如说通过头盖骨与裸露的手臂,手指,苍白的骨骼,很容易分辨。有时则比较困难,因为它们混同于茂盛的野草或荒凉的碎石地。他拾起其中的一截,可能是肋骨或锁骨之类。干燥的风吹拂着它,它依然很坚硬,或许比以前更加坚硬了。
这条路永无止境。比起那个整日推石头的家伙来说,道路要有趣得多。没有景色是重复的,走在道路之中,你可以勇往直前,永远有事物迎接你。然而道路的尽头在哪里?当这个问题产生,就是放弃或死亡的第一步。据说,有些人走上这条路,为的就是死亡的那一刻。他不想死,可作为逃亡者,他也无法停止。
逃亡者终于记起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停留。他的情人在这座城市。于是他走出剧场穿过拥挤的人群。他的情人就住在靠近集市的密集的居民区,那里低矮的四层小楼的屋檐常年往下滴水。“你到这儿多久啦?”她热衷于赤裸身体,身上总是汗涔涔的。天气太热了。她用柔软的手臂缠住他的脖子,温热的小腹靠着他,吮吸他身上的汁液。“咱们现在干什么呢?”逃亡者抚摸她皮肤上细小的颗粒,包裹在温暖肉体中的白色骨頭。他急于分清它们与碎石地里的骨头有何区别。
想要返回剧场,就必须穿越集市。他看到了那个老者,蜷缩在一旁。人们自觉地在他面前排好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漂亮的小玻璃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古老的集市。逃亡者在似乎同样古老的人群中穿梭,试图摆脱掉那个跟踪他的人。请记住这个异乡人:穿着黑色皮夹克,戴着口罩,踉踉跄跄地小跑着。他不想落入同类之手,不想失去自由。他有些紧张,甚至因此放了一个屁,但不会有人听见。
5
大概傍晚的时候,有两个军官闯了进来。外面的夜特别的静,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死去。那两个军官穿着笔挺的深色军装,帽子也是深色的,皮靴锃亮,走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声。在戏台的一角,逃亡者尽量使自己隐藏在更深的黑暗中。事实上,由于剧场里光线太过昏暗,这两个军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们走到戏台中央,站住。其中一个点了一支烟,另外一个则站着不动,像是在沉思什么。
逃亡者注意到,这两个军官的模样很相似,说是双胞胎也并非不可能。
他们手里各自牵着一条锁链,锁链各自拴在一个匍匐着的人的脖子上。其中一个拴着的是个女人,另一个则是个男人,相同点是这两个被锁链拴住脖子的人都一丝不挂,而且他们都很年轻。这两个人安安静静地跪在各自主人的脚边,像是两只听话的宠物。不如称他们为乙和丙。乙是女人,丙是男人。当他们的主人开始走动,拉紧锁链,宠物也挪动身体,只不过他们俩是四肢着地,用双手和膝盖作为支撑点向前爬行。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个抽烟的军官说。
“又一天过去啦。”沉思的军官仍盯着戏台上的某一处,心不在焉地回答。
接着,他们开始交流关于乐器方面的事情。抽烟的军官想买一只小号,他似乎对小号情有独钟。从他的话中可以得知,他最向往的职业似乎是去一家地下酒吧吹小号,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肺部貌似出了些问题,医生建议他还是放弃吹小号的念头。那个沉思的军官则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随口敷衍着,但他无意中透露出了关键的一点:他出自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就练习钢琴和小提琴,尽管他对这两样都深恶痛绝。他还运用了一个很奇特的比喻:“人都是没知识的混蛋,像猴一样见什么学什么。”这句话显然使抽烟的军官有点不高兴,尽管他知道自己同伴的这句话是另有所指。他像是轰蚊子般用手扇了扇弥漫在眼前的烟雾,说:“念念不忘这些往事是没有好处的。”他的语气尽管漫不经心,但仍不失为一种反击。
音乐的话题到此为止。这个过程中,他们脚下的宠物一声不吭,连喘息声都听不到。抽烟的军官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宠物乙,说他每天如何喂她最新鲜的牛奶,以及甜美的果子,就是为了让她能够学会说人话,可是到现在为止她还一句话不会说。
沉思的军官眯着眼睛,伸手抚摸起乙光滑的头发、背脊以及乳房。乙不敢抬头,身体微微战栗着。忽然,抽烟的军官想起了什么,对着同伴耳语起来。沉思的军官不时微笑,并且点头。他们将各自的宠物栓在附近的栏杆上,走下戏台,不知去了何方。
现在,戏台上只剩下乙和丙。他们仍保持着匍匐的姿势,彼此凝视着对方。很快,他们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了变化:眼神变得含情脉脉,开始彼此靠近。很快,丙迫不及待地搂住了乙,疯狂地嗅着她的头发。他们抱在一起,难解难分。眼瞅着丙压在了乙的身上。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乙和丙还没来得及分开,比他们更快的是枪声。这使躲藏在角落里的逃亡者吓了一跳。乙和丙立刻倒在了血泊中。
刚才抽烟的军官很是气急败坏的样子,挥舞着手枪,大喊着什么,似乎是“可耻”之类的词,但并不确定。而沉思的军官则显得很镇定,他望着死去的两个人,自言自语似的说:“……向我瞪了垂死的一眼。”
接着是静默。
几秒钟后,从黑暗的观众席上爆发出掌声与欢呼声。乙和丙微笑着站起身,与两个军官站成一排。这时,乙望向逃亡者隐藏的角落,对他挥了挥手,示意他过来。逃亡者震惊地站起身,跑向后台。他听到身后传来如潮般的笑声。
6
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他已经非常老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这样老去。在一些寂静的日子里,他总是反复凝视自己皮肤松弛的手臂,那上面布满棕色的老年斑,交织纵横的皱纹令人想起渔网。他没有镜子,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何种模样。他依旧住在这座废旧的剧场里。多少年了?三十年,还是四十年?总之,时间已过去很久很久了。他依然会忍不住想起曾经自己作为一名演员的日子。那个时候,剧场要比现在干净很多,当然也要热闹很多。观众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手里拿着他要出演的最新的剧目单,期待着他们最爱的演员登场。从清晨一直到午夜,观众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当最后一批观众恋恋不舍地离去,演员们才有机会松一口气。
当然,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不知从何时起,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占领了这座城市,新一代观众更乐于在荧幕上看那些炫目的场面。相形之下,戏剧变得枯燥无聊,大型的剧场被废弃,只有演出那些幽默小品的小剧场勉强得以生存……然而这一切都不像真的,他总是怀疑这些是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根本没有过高朋满座,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他始终是一个小演员,可有可无,从未单独接受过观众热烈的欢呼。
记忆变得模糊,辨认总是艰难的。他拄着拐杖,缓慢地走上戏台。“在这温柔与平静的帷幕之后……”他喃喃自语,望向幽暗的观众席。他什么也看不清。那里有人吗?他冲观众席喊了一声,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
在剧场的后面,是一片墓地。清晨,当蓝色的雾气弥漫,他喜欢在墓地里散步。有一天,他在一块墓碑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并不惊讶。他手里的拐杖变成了一把铲子。于是他挖开了坟墓,打开棺材。里面是一具完整的骷髅,他背着骷髅回到剧场,把它放在观众席的某个座位上。第二天,他发现棺材里又出现了一具骷髅,他重复了头一天的举动。棺材里的骷髅总会在第二天自动复现。他想,早晚有一天,观众席会重新坐满。
现在,他站在戏台中央。浑身的关节都在嘎吱作响,他知道它们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在戏台左侧,黑色枝丫正在疯狂生长,彼此紧紧缠绕。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旧时剧目单。
一出伟大的戏剧就要开始。在他混沌的余生中,这出戏剧已经过反复排练。观众们屏息凝视。他扔掉拐杖,一束刺目的灯光突然在头顶亮起……
他醒来。
空气里有一种焦煳的味道。黑暗中传来谁的窃窃私语,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男有女。他们手里拿着剧本,一边踱步一边低声默念,似乎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不小心撞在一起也浑然不觉。
他站起身。他很想大声质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是鬼魂吗?可是他们就像洞悉了他的内心一样,忽然停止了默念與踱步,梦游般从大门鱼贯而出。
戏台上,只剩下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顶棕色毡帽,帽子下面压着几页A4大小的稿纸。他慢慢走过去,拿起帽子,左右看了看,然后戴在头上。接着他翻开稿纸,发现这是一部遗失的剧本。开篇的一页上写着:
56岁,作家,战争时期。
他内心滋生着恐惧。戏台愈加昏暗。隐约中,他听见黑暗里的狗吠声。
7
大幕徐徐拉开。他坐在戏台正中央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那只棕色毡帽的帽檐,平放在大腿上。他面无表情,但明显有些疲惫。就在刚才,他送走了一名苦口相劝的朋友。这已经是他今天上午接待的第五名访客了。其中有的是朋友,有的则是不相干的读者,还有他的一名出版商。他知道,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他们都是为了他好,才会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来到他家里,劝说他不要离开。
当他送走最后一名访客时已是中午。他没有吃饭,走出房间,带着那只大黑狗来到外面。此时正是最热的时候,他近些年变得有些臃肿的身体开始大汗淋漓。他喘息着,但没有停下脚步。其实他也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架飞机在头顶轰鸣而过,撒下纷纷扬扬的传单,像是大片雪花。上面无非是对城里的人进行威慑和劝降。他继续往前走,直到他在废弃的剧场前停住脚步,他都没有想好此行的目的地。
剧场和他印象中的差不多。只不过,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荒凉。观众席的座椅上早已积满灰尘,供人行走的通道地面上全是被窃贼敲碎的碎玻璃。如今,连窃贼也不会来这里了。他慢慢地往前走,黑狗乖巧地跟在后面。
他在戏台中央发现了这把椅子。椅子很干净,一看就是刚有人擦过。谁在这里?他有些疑惑。无论如何,有了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他坐到椅子上,摘下帽子,调整有点急促的呼吸。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他想,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大黑狗安静地趴在他的脚边。
这里的一切都是沉寂的。他还记得小时候,这里热闹的场景。那个时候母亲经常带他来这里看戏,观众席上几乎座无虚席。那个时候,戏台上的演员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渴望像他们一样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人们的欢呼。当然,后来他成为一名作家,在很多访谈中,他都会提及童年的这段经历如何成为他写作的启蒙,他总是会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大黑狗突然大声吠叫起来。有人来吗?他警惕地盯着大门口。片刻后,大黑狗平静下来了,并没有人进来。
他盯着戏台上一枚碎掉一半的灯泡,继续陷入沉思。
“我开始拿定主意……我这一辈子老是拿不定主意。”他自言自语地念叨。母亲,我该怎么办?他似乎看见母亲正坐在观众席上,当然这肯定是幻觉,因为他的母亲已经死去两年了。她曾活了很久。
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母亲。他没有子女,也没有恋人。他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他的那些大受欢迎的小说里,主人公总是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去世界各地冒险,去探索未知的秘密。而现实中,他几乎足不出户,母亲禁止他去很远的地方。
与其他孩子不同,他喜欢与母亲待在一起。母亲为他打扫的那间小屋是他所有想象的源头。只有在母亲身边他才会感到平静,才能尽情地发挥他的想象力。但是,那种平静现已不再了。母亲去世,战争的乌云逼近。这些都搅动着他的心。他生平第一次产生离开这座小城的念头,他想要去一个平静的地方,重获安宁的心。
可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朋友与读者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也出奇一致: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作为一种象征曾激励了多少人的心!而现在战争在即,他却要离开这里,不免给人们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并且他的朋友告诉他,有一些阴谋论者开始散播他将要秘密投敌的谣言……无论怎样,这个时候离开,都会使他名声扫地,晚节不保。
8
作家步行来到这个古老的集市。他已经很久没来过这里了。这些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因此除了定期在家附近散散步,他很少去远一点的地方。曾经,母亲时常带他来这里,她似乎很喜欢集市。集市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小物品总是让母亲心情愉悦。他也是愉悦的,尽管他有些害怕集市上的人。他们言语粗鲁,随地吐痰,有时还会爆发冲突。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仿佛只要一松手,他就会淹没在这个充斥着野蛮、算计与陌生的地方。
母亲最喜欢去的是卖毛毯的摊铺。他至今还记得,母亲站在挂满墙面的毛毯前流连忘返的样子。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少有的光彩。她用手轻轻抚摸着毛毯,就像抚摸孩子的脸庞一样。那些毛毯上的图案都是一个上了歲数的女人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作家凭着记忆来到那家商铺前。它还在,跟他记忆中没有两样,只不过现今墙面上的毛毯图案都是用机器编织而成的。店主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店铺里没有别的顾客。
年轻的店主抬起头,一眼就认出了作家,他连忙站起身,略带紧张地叫出了作家的名字,并且非常巧合的是他在阅读的正是作家的某一部小说。他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作家则点着头,但心思明显没在这上面。
小伙子话锋一转,谈到了作家想要出走的传闻。他的话很谨慎,可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怀疑。他旁敲侧击地告诉作家,他从小就开始阅读作家的作品,里面那些对命运永不屈服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影响了他。作家有些不耐烦地听着,告诉小伙子,书中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小说与现实不能混为一谈。显然,作家的一番话使他有些困惑。
所有人都想教训我,作家想。
为了打破尴尬,作家主动问起了以前的店主,也就是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小伙子告诉他,那个女人是他的母亲,现在就躺在里屋的床上,但她已重病多时。作家跟着小伙子来到里屋,看见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正躺在木板床上,与她相比,床铺显得过于空阔了。
作家坐在老太太的床头边,凝视着她。
她闭着眼,不知是入睡还是昏迷了,眼皮不住地抖动着。他深深地陷入回忆中,想到了童年,母亲,还有很多事。这时,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眼皮翕动,艰难地睁开眼。作家站起身,匆忙中撞到了一盏垂下来的灯泡。他快步走出毛毯店。
“你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躲起来。”作家走在集市拥挤的人群中,喃喃自语。身后的大黑狗再次吠叫起来。他看到两个医生模样的人一前一后抬着担架,从一栋楼里走出来。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被白布蒙着,显然已经死了。后面还跟着几个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死者的黑色皮夹克。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作家得知死掉的是一男一女,据说是偷情被捉奸在床,然后双双被杀。一个故事梗概立刻诞生在作家的脑子里,可几乎与此同时,作家厌恶地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去。
黄昏降临了。作家穿过集市,来到了城市边缘。他已经很久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了。前方不远处是一片丛林。他走近丛林。从掩映的树木中,他似乎隐约看到了一排座椅。“你准是看见了幻象。”作家低下头,自言自语。这真像是一场梦啊。
9
他躺在一张大床上。就在戏台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他很饿,他已经饿了很久了。但是他什么也不想吃,见到吃的他就反胃。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躺了多久了,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几十年。在他手边的只有一摞稿纸和一只用了一半的铅笔。当然,还会有铅笔刀,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如果现在有人走进来,会发现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对于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头发总是在掉,其实他的脑壳已基本秃了,但还没有完全秃,几缕稀疏的头发顽强地贴在头皮上。还有那些恼人的皮屑,总是往下掉,不停掉。过不了多久指甲也会脱落的。老了都这样。老去真是一件麻烦事。
他腿脚不好,因此平日里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反复修改这部剧本。他已经忘了这部戏他写了多少年了,或许他就是在写这部戏的过程中变老的。谁知道呢。由于记忆变差的缘故,他时常忘记前面写过的情节和人物,故事因此变得凌乱不堪。往往前面死掉的人物到后面突然活了过来,或是某个重要角色忽然失踪。他在往下写的同时不停地删掉前面的内容,以至于这部戏几乎是一边写一边消失。
剧场的光线很暗。常年生活在这里,使他的听觉变得灵敏。此刻,他微微支撑起身体,伸长脖子,倾听着黑暗中的声音。声音是从观众席中发出的。有叹息,哈欠声,也有窃笑。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到。他随手拾起一只空瓶子,朝观众席扔去。破碎的声响久久回荡在剧场里。你们应该消失,连同这个世界,一起消失。他想。
现在是什么时候啦?他望着窗外晦暗不明的光线思考着。
他久久地做梦,或是陷入幻觉。有一天,当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他的床前。这是一个年轻女孩,非常年轻,十五,还是十六岁?她看上去有点害怕,也有些警觉。因为我太老啦,他想。他问女孩是谁,女孩回答说是他打电话叫她来的。可是他完全没有印象。这种事情确实时有发生。女孩开始一件件脱衣服。她看起来很冷,哆哆嗦嗦的。外面是冬天吗?他已经对季节失去了概念。女孩很快脱得一丝不挂。
“我都呼吸得腻烦了。”他说。声音很嘶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说话了。他伸出手,抚摸着女孩娇嫩的皮肤。女孩轻轻颤抖着。是因为我太老了,还是她有什么伤心事?于是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爱人。她的皮肤总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因为她喜欢去海边。她的身上总是汗涔涔的,总是很湿润。像是一只热带的动物。而眼前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体太苍白了,而且太过瘦弱,仿佛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惹人怜爱。不,现在他已经不会去爱什么了。
在某些清晨或傍晚,天色微明。他感覺身体好一些,就会起身去附近的墓地。墓地遍地都是野花。空气中弥漫着蓝色的雾气。他缓慢地走着。偶尔,他会听到小号声,那是一个战死的军官的鬼魂。也可能是他的幻觉。他长久地徘徊在墓地中。
“思想并不是世间最坏的事。”他累了,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微风吹动他所剩无几的头发。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从前那些勇往直前的日子。可惜的是他已经记不起什么了。他看到灯光在渐渐变亮。他站起身,往回走。“咱们老是想办法证明自己还存在。”他低声说道,然后使劲闻了闻自己的胳肢窝。
责任编辑 周明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