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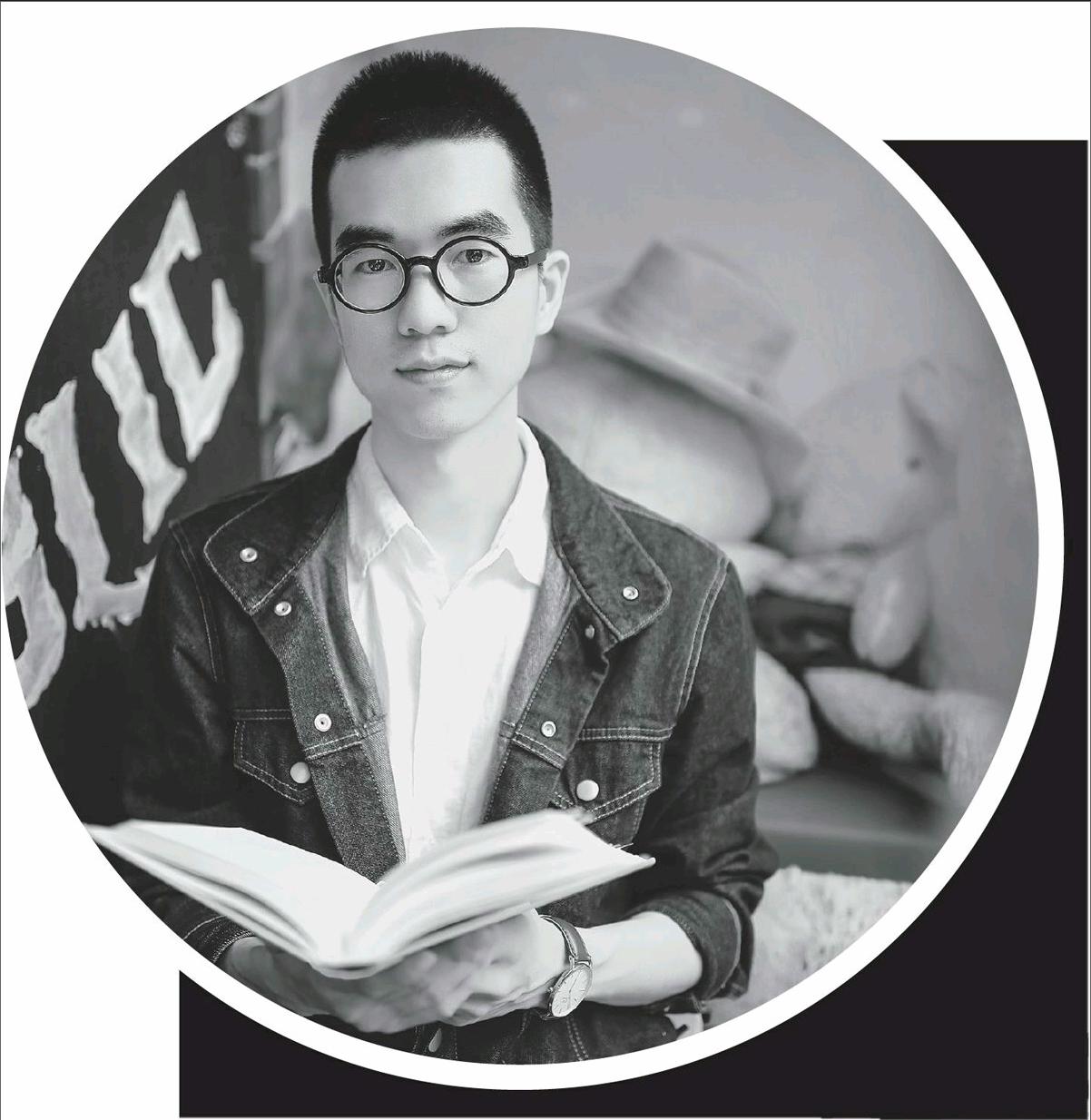
林培源,1987年生,青年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在读。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得主。作品发表于《花城》《山花》《作品》《青年文学》《香港作家》等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2014)、《第三条河岸》(2013)等六部作品。最新长篇小说《以父之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这不是她第一次闯进出租屋了。最初几次,阿喜没能撞见她。她像日影那样溜进来,又悄然隐去。直到那天阿喜回来,发现茶几上的面包不见了,刚买的牛奶少了几罐,他才意识到,屋子遭窃了。他检查了门窗,又打开行李袋,没丢钱,其他贵重物品也还在。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了。他像只焦躁而无助的公鸡,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到了晚上,他躺到床上睡不着。在口岸这带待了这么久,他一直深居简出,活得像个影子,怎么就让人盯上了?一整晚他紧张得头痛,睡着了又醒过来,睁着眼直到天亮。隔天起床后,他给老板张姐打了电话,向她请假。他决定利用一天的时间守株待兔,揪住那个闯入者。
早晨他像往常那样准时出门,走到巷口摊吃了一碗粉,然后绕一圈再折返回家。他一屁股坐到床边,警惕地打量出租屋:一室一厅,带个窄窄的阳台,窗户用报纸糊上了。这一栋农民房,和口岸区的商业楼隔了三个街口,位置不错,入夜后也不吵,每层楼住三户,加上水电费,一个月不过六百来块的房租。在口岸这带,算很低的了。
现在阿喜觉得倒像是一个陌生闯入者。他的视线来回逡巡,掠过客厅陈旧的布艺沙发、堆得乱糟糟的茶几以及歪歪斜斜的塑料鞋架。这些都一再提醒他,他是个异地人,这里没什么是归属他的,粗糙的墙面,铺了廉价瓷砖满是污渍的地板,厨房水龙头漏水不断,还经常有老鼠蟑螂出没……这些无不给他一种寄居在别人生活中的感觉。在他之前,这间屋子还住过哪些人?走私犯?卖淫女?还是和他一样有家不得回的外地人?
阿喜躺在床上胡乱地想着什么,太阳穴突突跳得厉害。昨晚的困乏使他现在抵挡不住倦意,躺着躺着就睡过去了。等到他猛然醒转过来,他心口一阵狂跳,上了发条似的,一起来就直奔客厅。那里什么也没有。也许紧张过头了,他甚至怀疑昨天的失窃只是幻觉。颓然地坐回沙发上,他像苦等猎物而不得的猎手那样,凝视墙上的某个点,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之后他好像受到了什么指示,匍匐在地板上,侧过头。果然,在沙發底下,他瞥见了一只鞋子。他伸长手臂掏出鞋子。是双女式豆豆鞋,鞋底磨破了,大脚趾的位置有个小洞。鞋子很旧,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异味。他检查鞋子,试图找出什么线索,然而除了闯入者的性别之外,再无其他发现。
他不知鞋子是什么时候落下的。一想到那人趁他不在家时躺在沙发上,甚至随意使用厕所,睡他的床,他内心就泛起强烈的嫌恶。她为什么会把鞋子落在这里呢?她一定是摸准了阿喜进出的规律,阿喜前脚刚离开,她后脚就进来,问题是,出租屋楼下有防盗锁,门楼又安有监视器,进出肯定会被拍到,她到底怎么进来的?
阿喜决定到房东那里调看监控录像。
房东住最顶上的六层。阿喜讲明了来意,房东这才一脸不情愿地开门。阿喜把脱下的鞋整整齐齐码在门边,光脚踩进去。房东家地板很干净,阿喜的脚底袭来一阵凉意。
房东调出监控录像,阿喜猫着腰,盯住屏幕看。一连看了十几分钟,也没看出个究竟。站在身后的房东开口了:我说没有嘛,我这里安全的,小偷不敢进来。房东说话带了浓重的桂柳口音。他不是本地人,本地人讲类似粤语的“白话”。阿喜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就在准备放弃时,他瞥见一个背影跑着从屏幕上经过。阿喜的喉咙被什么扼住了,他按下暂停,放大影像。直觉告诉他,那正是他要找的人。身高不高,半长的头发,上身穿了件深灰色的冬衣,脚上穿的似乎就是一对豆豆鞋。屏幕左上方显示时间为前天上午九点零八分,也就是阿喜上班后不久。如果她就是那个闯入者,那么极有可能,她是昨天把鞋子落下的。
房东见阿喜盯得那么入神,问道,找到啦?
阿喜说,还不确定。
房东语重心长说,进出还是要锁好门窗,贵重物品随身带啊。
阿喜向他道谢。从房东家出来,他上了出租屋的天台。这一栋和其他相邻建筑隔着两米左右的距离,一般人想借助其他建筑跨过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想到这里,阿喜更疑惑了,既然这样,门窗也关紧了,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房间有了别人的行迹,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给阿喜造成不小的阴影。他连续好几天寝食不安。那块阴影久久地罩在他心头,他绞尽脑汁想着该如何摆脱。晚上睡下了,一有轻微的动静他就醒来,再也睡不熟。不揪出这个人,他焦灼不已。他估摸着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得安宁,也许还要再搬一次家。
那是几天前的事了。现在,阿喜终于逮住她了。
阿喜关门时她半个身子已经腾到了拉开的窗户外,阿喜冲过去抱住她,粗暴地将她往里拽。她双手扣住窗沿,裹在冬衣下面的单薄腰身差些就要折成两截。两人重重摔在地上,她喘着气蹬了阿喜一脚,从他怀里挣脱了。阿喜疼得骂出声来。眼见再无逃跑的可能,她转身跑进厨房,从灶台上拿了把尖刀,握住刀柄对准阿喜,跟他对峙着。她的脸是青的,目光尖利如同手中的刀。阿喜心里咯噔,他摸不清这个人的脾性,怕万一狠起来,真的会被她一刀捅死。他很害怕,呼吸急促,心脏扑通扑通就要从喉头进出来。他伸手做出安抚的姿势:你把刀放下,有事好商量,我,我不是坏人……
这句话起不到任何抚慰的作用,反而激起她更进一步的敌意。
阿喜只好往后退,一直推到房间门口。
阿喜和她拉开了距离。他在脑海中模拟不同的摆脱危险的方式,甚至设想搏斗起来,自己应该怎么占上风。他紧张地忘了喊救命。这时他看到她抬起右手,抹了抹眼睛。阿喜注意到,她嵌在铁青的眼窝的左眼肿得像颗核桃,泪水涟涟的,不停眨动着。阿喜压低声音说,你把刀放下,你眼睛受伤了,我拿药给你擦。这话在她身上起了些反应,但她还是僵着不动。阿喜后退到房间,摸索着打开床头柜抽屉,找出前些日子买的眼药水。他紧张得手心冒汗,步子有些不稳。女孩握住刀的手怎么也不肯松动。阿喜将眼药水轻轻搁在茶几上,抬起头来看她。眼药水成了诱饵。她举着刀,挪步至茶几边,伸手去拿眼药水。就在这时,阿喜抓起身边的木凳子扔过去,凳子不偏不倚砸到她的右臂,她“啊”地叫了一声,刀应声落地。趁这个当口,阿喜铆足了劲扑过去,将她压在身下。
她本能地踢蹬阿喜,同时双手乱舞着,指甲在阿喜脸颊抠出红印来。阿喜疼得龇牙咧嘴,掐她脖子呵斥道:老实点,信不信我掐死你!他恼羞成怒,用力捏紧她纤瘦的脖颈,腾出另一只手来捂住她的嘴。她咬阿喜的手,因为一时呼吸不过来,枕在地板的头剧烈地晃动着。
阿喜逼近她,鼻息喷在她脸上。她厚实的棉衣扯开一道口子,露出枯瘦的锁骨。阿喜挪开掐住她脖颈的那只断了指的手,摸了摸被抓疼了的半边脸。她挣扎了一阵子,被阿喜死死地锁住。
意识到再无逃脫的可能,她才终于停歇了踢蹬,喉咙深处发出呜呜的兽类般的哭声。阿喜居高临下瞪着她。她那只红肿的眼快要从眼眶鼓出来。她哭了,眼泪鼻涕流出来,糊得阿喜满手都是。
阿喜看见她噙满泪的双眼,她的眼底透着愤怒和绝望,看得阿喜心里发慌。他刚才差点就要掐死她了。她要是死在这里,阿喜无疑就成了杀人犯,往后的日子,等待他不是无止境的逃亡,就是耗尽这辈子也坐不穿的牢底。
你再敢乱动我就报警,警察来了,我就什么也管不了!
这话到底起了些震慑作用,她瞪阿喜的目光没那么犀利了。
阿喜摸不准究竟要不要报警。他不想跟警察打交道,更何况,女孩子的目光深深刺痛了他。
他像钳制一只即将被驯服的野猫似的压住她。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在这间出租屋里,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他将暴力施加于她,而这暴力来得无从循迹。想到自己正在“对付”一个无寸铁的女孩子,而她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抵抗,阿喜被一阵巨大的怜悯迎面击中了。他松了一口气,慢慢放开掐住她脖子的手。
我不想伤害你,你,老实点……
女孩子放弃了抵抗。阿喜起身抱起她,放她到沙发上。她不再挣扎了,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那样,靠在沙发上瑟瑟发抖。阿喜捡起地上的刀,刀刃上闪着锋利的寒光,阿喜想,要是被刺中了,铁定没了命。他拾起眼药水,蹲在女孩子跟前。你的眼睛再不治,会瞎的。女孩子缩起双脚,脸上尽是怀疑和惊恐,半晌,她才低低得应了声“嗯”。阿喜伸手按在她额头往后仰,小心地将眼药水滴在那只肿胀的左眼上。她疼得倒抽一口冷气,嘴里发出“呲呲”声,眼泪滚落下来。
现在回想起这段遭遇,阿喜仍然一阵后怕。那一幕清晰如昨,像挥不去的影子,紧紧贴在他背后。他背井离乡来港口这里,本来是想图个清静,过些安稳日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活会从此跟这个陌生女孩捆绑在一块。
阿喜的脸被她抠出几道血印来,他对着镜子往抓痕擦老虎膏,又找来止血胶布,贴了上去,镜子中的他看起来像毁了容的怪人。
那晚阿喜守着她,她看起来很虚弱,脸色惨白,一直缩在沙发上,抱着手臂不敢看阿喜。阿喜问她,刚才没伤到吧?她摇了摇头。阿喜说,我叫阿喜,你呢,叫什么?
她的声音听起来木讷又迟缓,阿喜听不清。
她的嘴唇开裂了,阿喜倒杯水给她,她咕噜咕噜几口喝完。
阿喜找出纸和笔,示意她写一写。她弯腰趴在茶几上,握笔的手微微发颤,一笔一画写完了名字。张凌霞。阿喜看到上面扭曲的字,就喊你阿霞吧。她怔怔地望着阿喜,左眼还红肿着,右眼清澈透亮。也许她也在疑惑,这个前一分钟还差点掐死她的男人,眼下竟变得这样和善。
阿喜问,你饿了吧?说完他就起身进了厨房,翻出剩下的两包方便面,掰成几块扔进锅里,打了两只鸡蛋,用电磁炉煮了起来。煮面的间隙,阿喜回过头去看,阿霞坐在沙发上,有些不知所措。刚才两个人扭打在一起,而现在阿喜却给她煮起了面,阿喜想,假如他们只是萍水相逢,那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了猜度和对峙,然后相安无事,这让阿喜觉得荒谬。想到这里,他嘴角不禁扬起一丝笑来。
面煮好端上来,阿霞一边吹气一边吃。看来真的饿坏了。阿喜不饿,便把自己的那份也让给她。他说,慢慢吃,不够我再弄点别的。阿霞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阿喜突然发现,她吃面的样子既狼狈又好玩。
阿霞的脸上、脖子和手臂都很脏。不锈钢碗冒着热气,这让她的脸看起来朦胧一片。她那只肿胀的眼不停眨动,阿喜担心热气熏坏了它。她吃得额头冒汗,半长的头发一缕缕缠在一起,乱糟糟的。她裹着一件厚冬衣,可看起来还是那么瘦,胸部很扁,肩膀窄窄的,骨架又小,五官轮廓倒还是鲜明的,尤其是鼻子,挺直,衬着双眸,看上去很立体。
来到港口这么久,除了老板张姐一家,阿喜一直都和其他人保持着距离。他是这个陌生城市的外来者,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到这里躲避,讨生活,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天一个叫阿霞的女孩子会闯进来,截断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之流。
阿喜沉默地看她吃完面,抽出纸巾给她擦嘴。她满足地砸吧着嘴,好像这时才恢复了元气。阿喜于是向她问一些话。她的回答都很简短。她告诉阿喜,她家在里火那边,那一带很偏,在山区的边境线上,翻过山就是越南境内。
说这些话时,阿霞泪眼涟涟,阿喜无从判断她是眼睛难受,还是真的哭了。
阿喜好奇,你怎么会到这里?
阿霞想了想,说,我几个月前想来这边打工,坐大巴的时候钱被偷了,司机把我放到这里,我没地方去,连吃饭的钱也没有……
那你也不能偷东西,换作别人,你早待派出所了。
阿霞听了,一阵脸红。她说,我阿爸几年前死了,我阿妈跟人家跑了,我真的没地方去。
阿霞低垂着眼,讲得很慢。阿喜辨不出她话里的真假,他有许多疑问,比如她拢共闯进来几次,为什么偏偏挑中他这里。但是话到了喉咙,就给咽了下去。他从行李袋搜出一条布裤和一件法兰绒衬衣,又拿了条浴巾给阿霞,说,你冲个澡吧,不能这么脏下去。
阿霞抬起头,表情愣愣的。
阿喜说,将就一下,改天带你买衣服去。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他已经够仁慈的了,让阿霞进来,又给了她吃的,接着就应该让她走人。
阿霞的目光如此呆滞,像在努力冥想什么。
阿喜提了只水桶放在浴室给她放换掉的衣物,帮她开了热水器。热水器的喷头搁在地上,水冒出来,很快浴室就热气腾腾的。
阿喜说,去冲个澡吧。
阿霞抱起衣服,踮着腳走进浴室。阿喜吩咐她从里面闩好门锁。放心洗吧,没人偷看的。阿霞的背影停在浴室门口,头也没回,只从喉咙发出一个“嗯”。阿喜的思绪飘远了。他想起刚才惊险的一幕,觉得很不真实。待阿霞进了浴室,他起身收拾碗筷。他伸手去摸脸上的抓痕,止血胶布贴着,摸起来像长出了一层新的皮肤。他听见门闩的响动,听见水哗啦啦淋在地板。
阿霞在浴室洗了很久。阿喜收拾完碗筷,担心她会不会煤气中毒,便去敲浴室的门。你没事吧?阿喜在外面问。阿霞关掉热水,说,没事没事,就好了。隔着门板,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同。阿喜想,或许经过一番清洗,阿霞不仅身子干净了,连嗓子也清澈了。
阿喜坐到沙发上抽烟,烟雾从眼前升起,飘到天花板,再渐渐散去。
阿霞洗完澡出来,阿喜看到他的衬衫和布裤套在她瘦小的身上,爽朗又帅气。这样的她,洗掉身上的污垢,干干净净的,显出她原本的样貌。她挽起袖子,裤腿也卷了几卷,湿漉漉的头发用浴巾裹住,看起来像个阿拉伯少女。
阿霞身上散发着好闻的沐浴露的香气。
阿喜进房间,找出羽绒服给她穿上。天冷,别感冒了。阿喜说。阿霞小小的身子裹上他宽大的羽绒服,像只瘦削的雀鸟。两人都没说话,生怕声音会使原本不大的空间再次缩小。阿喜习惯了独居,现在屋子里多出来一个人,他感到不自在。但他转念一想,阿霞进来过出租屋几次了,只是他们从未在同一时间出现。所以严格来讲,出租屋不只他一个人,阿霞也在,她比谁都更熟悉这里。这一切在他身上激起一阵奇异的感受,好像此刻他成了借宿的,而阿霞才是出租屋真正的主人。
阿喜又抽起烟来。
烟是向越南贩子买的,黄色烟盒,印了黑色的“Nam Kinh”字样,越南人称这是他们的“中华烟”,抽起来像万宝路。阿喜烟瘾不重,却莫名喜欢上这款烟。
有天他下班从港口回来,顺路跟越南人买的,卖烟的都是些皮肤黝黑个子偏矮的越南妇女。她们戴斗笠,坐在矮凳上,跟前摆着货物,沿街排开。除了烟,她们也卖些药品,越南的老虎膏、跌打药、鼻炎药什么的,叠在一起装进竹筐,上头搁着写了中文的纸板。为了做中国人的生意,她们大多会讲中文。
阿霞盯着茶几上的烟盒出神。
阿喜问她,来一口?阿霞有些诧异。阿喜抽一支递给她,她接过来,咬在唇边,同时晾诧地盯着阿喜的断指,眼中皆是惊恐与好奇。阿喜意识到了什么,迅速缩回手,搁下来。他羞于展示丑陋的伤口,用另一只手拿打火机给阿霞点烟,阿霞吸了一口,猛地呛起来。阿喜说,慢点嘛。阿霞呛得眼泪流出来了。好苦,她说。阿喜说,不苦哪叫烟?阿霞学着阿喜的样子,笨拙地用手指夹烟,她蜷在沙发上,这时才稍微放松下来。屋内湿冷,她坐着坐着,不自觉地往阿喜身上靠过去。阿喜不禁缩了缩肩膀。这个亲密的动作让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温暖。他觉得横亘在他们俩之间的冰块慢慢消融了,他沉默地抽烟。阿霞看着烟袅袅升起。在这间窄小的出租屋,他们一起分享了抽烟的隐秘的快乐。
阿霞喃喃地问,你的手……怎么了?阿喜说,没怎么,以前在车行,机器绞的。
阿霞听了,没有问什么。
阿喜靠着沙发抽完了烟,等到他感到肩膀酸胀,再侧过头去看时,阿霞已经睡着了。她的头发还没干,水珠顺着发梢滴下来。阿喜小心地拿掉她手上的烟蒂,抱她进房间。她很轻,好像稍一用力就会被捏碎。
阿喜帮她枕好枕头,怕她着凉,又将浴巾垫在枕头上。
她睡着的样子像只恬静的小猫,阿喜盖好被子,退出了房间。
洗澡时,阿喜脸颊的抓痕烫到热水,疼得他龇牙咧嘴的。他忍着疼迅速洗漱完,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可出了浴室还是觉得冷。他在羽绒服外面披条毯子,在沙发上躺着。口岸这带白天热闹,入夜后就没什么人了,喧嚣消匿,夜色便如水一般漫过来。天气好的时节,傍晚下了班,阿喜会沿河堤走上一段。河边风大,走个一两公里,阿喜就开始往回走。收了摊的越南人过关回去,认识的,不认识的,相互擦肩而过。他们每天都挑着担子,过关来做生意,担子来时重归时轻,来来回回间,日子晃一晃就过去了。
在口岸做生意的越南人持有边民证,白天过关做生意,夜间回去,跟赶集一样。小贩和游客携着异质的语言汇聚到这里,也只有在这里,语言才能卸下它神秘的面纱,显露出原始的面目。河对岸越南境内,经常有汽船突突突地从河面开过去,有的是走私船,货物用帆布盖着,沿浅滩一路驰去。天气晴好的黄昏,晚霞低低垂挂天际,映着北仑河浅绿的水面,对岸的芦苇、水草在风中摇曳,煞是好看。
除了买烟,阿喜很少和越南人打交道。越南女人的勤快和持家是出了名的,而他见到的越南男人,大多戴绿色的圆帽子——当地人戏称为“绿帽”。他们沿街叫卖沉香佛珠,遇到中国游客便苍蝇一样围过去,用中文卖力地兜售。越南话并不好听,生硬地好像要扭着舌头才能说出来。但是越南女人对阿喜有着神秘的吸引力,遇到她们,阿喜会仔细地观察一番,他看她们的脸,看她们的穿着打扮,试着从她们身上揪出些共同的特征来。越南女人是看不显年龄的,她们肤色偏暗,鱼尾纹总是过早爬上眉角,只有目光还凝着生活的素朴与贫乏。比起中国女人,她们的眼神也浊些,穿衣打扮,更没有中国女人鲜艳。
阿喜想起他的越南母亲,他想从她们脸上嗅出些母亲的样貌,可看来看去仍是徒劳。二十几年前母亲丢下他,逃开她噩梦般的家,从此不知所踪。阿喜经常想,她会不会恰好就是这群越南女人中的某一个?他找不到任何和她有关的信息,不知她的名字,也从来没人告诉他。母亲自离家就和他们切断了关联。阿喜不知她为什么如此决绝,这个无名无分的人,决意让自己销声匿迹,就像水融进茫茫人海。
阿喜有关她的那点记忆也随时间流逝而日渐模糊,有时他做梦,梦见母亲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走一步,她退一步,等他伸手去抓住她,她已经不见了。醒来后他大汗淋漓,这个梦他做了又做,所有的场景和细节,在他醒来后清晰可见。但梦境所昭示的,大抵跟现实相反,所以这么多年,阿喜一直坚信,他会找到她。如今他到了离她尽可能近的地方,可还是觉得远。其实他只要办个签证就能过去了,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但过去了又怎样?那么多的人,那么渺茫的机会,一切都无法预测。因此他动了念头,又打了退堂鼓,一天天在这里耗着,观望着。
第二天,阿喜起床后到房间看了看,阿霞还在睡,裹在枕头上的浴巾不知什么时候掉到地上,阿喜走过去拾起来。怕惊醒阿霞,他的动作放得很轻。他给阿霞写了纸条,跟零钱还有钥匙一起压在茶几上。他想,等他去上班,阿霞醒来,看见了自会明白。他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对这个几次闯进屋里的女孩这么好。也许谈不上好,只是心里的善意促使他这样做。要是阿霞拿了钱从此离开,他就不再负任何责任了。
阿喜这样想着,很快走到了老板张姐家的铺头。张姐铺头在“越南街”,要穿过一个小广场才能走进去。老板张姐四十来岁,柳州人。十几年前,赴越旅游兴起,她从柳州过来这边做导游,带团过越南的芒街、西贡和下龙湾旅游,她和越南商贩混熟了,也带些越南那边的药品和特产回来卖。
如果不是那次下龙湾游船出事,也许她现在也经营起自家的旅行社,当起了老板。
那次游船触礁翻船,一船人差点没命,好在水警和救援船来得及时,才没淹死人。张姐捡回一条命,回来后心有余悸,便从旅行社辞了职。做导游那几年她攒了些钱,辞职后她嫁给一个本地人,心闲不下,便和丈夫商量着租下这间铺面,利用自己积攒下来的资源和人脉,改行做起生意来。
张姐家的铺头卖越南特产、烟酒还有药品。店面很小,三面墙做成货架,中间一张台,上搁货物,下面备货,是小间杂货铺的规格,甚至连个挂招牌也没有。阿喜问过张姐,怎么不做个招牌挂一挂。张姐说,没这个必要啦,你没看客人个个进来低个头,看见什么好的就买,这里那么多店面,谁费心去记呀?张姐语速极快,听得阿喜一愣一愣的。他注意到,张姐家名片做得精致,上头印有手机号、店铺地址和支付宝账号。大部分游客到口岸游玩,伴手礼就得买一大堆,买的也无非是烟酒、芒果干、西贡咖啡什么的,嫌携带麻烦,他们大多会掏钱托店家寄运。张姐家是最早提供快递服务的店铺之一。她嘴甜,会招徕顾客,回头客很多,生意要比其他人好些。招了阿喜之后,张姐将打包和发快递的活交给他。阿喜忙时,一天要打上百个包,客人挑了货,拿纸箱装好,称重,算运费,结账。现金阿喜收了放抽屉,支付宝的就全打张姐那里。阿喜手脚勤快,靠得住,张姐对他很是满意。
这天早上,阿喜神色憔悴踱步进来,他脸颊贴的胶布还没撕掉。张姐见到他,开玩笑道,阿喜啊,昨天“抠女”去啦?“抠女”是她从港剧学来的。阿喜尴尬笑笑说,没呢,昨天不太舒服,在家睡觉。张姐又问,你这脸怎么回事?阿喜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好说,逗别人的猫被抓了。邻铺看店的女孩也来凑热闹,喜哥这是闹哪一出啊?我看是被女人抠的吧?相邻铺头的人听见了,都笑起来。阿喜脸红,只好也乐呵呵跟着笑。
当初阿喜到张姐铺头打工,也是误打误撞。旧年他从广东过来,身上存了些钱。他租了房,宅了几天,闲着没事就去口岸逛,走进“越南街”,逛到张姐铺头,恰好见张姐在忙活。货架很高,张姐站在塑料椅上撅着臀摆货,脚打滑,顺势倒下来。阿喜手快,扶了她一把,人也差些仰躺到地上。张姐吓得脸色发青,手肘撞向阿喜,把他右边的颧骨撞得乌青。两人站稳后,张姐拍着胸脯压惊,又感激又愧疚的,向阿喜道歉,还拿出老虎膏给阿喜擦。阿喜摆摆手,不用不用,没事的。张姐哪里肯听。她给阿喜擦药,弄得阿喜很尴尬。擦完药,她又拉着阿喜问这问那。你不是本地人吧?在附近上班?阿喜说,我刚来,在、在找工作…一张姐说,多亏了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阿喜杵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张姐想了想,递了名片说,有事记得找我!
阿喜道了谢,揣了名片离开“越南街”。
回去后,阿喜晃荡了几天。在港口这边,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上午睡到自然醒,吃完饭就回屋待着。那时还是夏天,天气燥热,房间沒有空调,阿喜热得睡不着,便铺了凉席睡在地板上。日子重复,人也变得懒散。从“越南街”回来后,那张名片一直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有天阿喜起床,盯着名片看,觉得这张名片像一个神秘的召唤。他想,反正闲着没事,为什么不去张姐铺头帮手?挣扎了一阵,他鼓起勇气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张姐的嗓门很大,阿喜能感受到她言语间的惊喜和意外。隔天阿喜便到张姐铺头上班了。上了几天班,他却开始后悔了。整栋商业大厦,看铺的不是中年妇女就是年轻女孩,阿喜处在中间,怎么看都像个异类。他无所适从的样子让张姐察觉到了,有天她拉着阿喜,打趣道,阿喜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你是我们镇店之宝啊。阿喜知道张姐话里的意思,他又着手斜靠在货架上,看着张姐那张阔圆的脸,两片厚嘴唇咂巴咂巴讲个不停,脸上露出了微笑。
看铺头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心细点,手脚利索些就好,因此上班的大部分时候,阿喜都是相对闲的。张姐除了麻将没其他爱好,淡季一到,她把店交给阿喜看顾,跑出去打麻将。要是没多少客人光顾,阿喜不是低头玩手机,看视频,就是和对面铺的人说话解闷。这样的生活简单而枯燥,但至少它安稳,没有太多烦心事纠缠。阿喜甚至想,哪天自己也开一间半间铺面,就在这里安家,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有次他撞见张姐丈夫来巡店。他姓刘,大家都喊他刘哥,话不多,经常阴着脸,阿喜倒有些怕他。他听隔壁铺讲,刘哥以前做红木家具的,生意做得挺大,后来涉嫌走私,厂子给工商封了,更不幸的是他先前砸下的钱也让人卷走了。他被抓进监狱蹲了几个月,出来后人就颓掉了,大钱赚不了,小钱又不屑赚,整天无非是打麻将、接孩子上下学,家庭开支基本就靠张姐一人撑着。对于张姐招阿喜这事,他没什么反对意见,巡店见到阿喜,问几句话,也便沉默了。阿喜被他盯得有些心悸。阿喜知道他这样的人,先前阔过,什么人没见过呢,看人是很准的。他巡店,是想瞧瞧阿喜到底是个什么角色。阿喜战战兢兢的,不敢乱说话,跟他打招呼,他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嗯”。
这天阿喜心神不宁,打包时算错运费,还差点打翻一罐西贡咖啡。还好张姐顾着跟别人说话,没注意到这些。他眼前闪过阿霞那张脸,她像身处一片黑暗中,只有那只红肿的眼看着他。阿喜心底被什么给捅开一道口子,风呼呼灌进来,他知道瞒不过自己了,他在“惦记”阿霞。他既盼着她早点走,又隐隐感到,阿霞还在,她不会轻易走的。这些事,他只能揣在怀里,不能讲给别人听,包括张姐。阿喜知道张姐的为人,只要他开口,张姐肯定会替他做主张,但阿喜不想这样。这是他私人的事,他只想早点下班走人,回去看个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