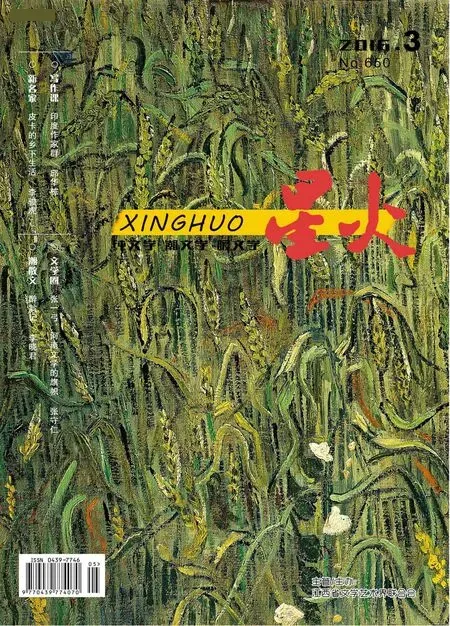夜轿
○李祚福
夜轿
○李祚福

李祚福,1979年闰6月生,江西兴国人。作品主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诗潮》《山东文学》,入选过多个选本。江西省2016年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
我已经有好些个年头没有回秦村了。
因为这次林改工作,我有了机会故地重游。
过了杨村河,再过蓑衣坝,眼前,就是秦村了。经过秦村水口的树下,一只喜鹊低飞而过。它也是从秦村出来的,飞向了对面稀土矿旧址,我内心涌起莫名的激动。不远处斜坡上的青石大楼,是曾经的矿场中心。这座大楼也曾经是秦村的经济和娱乐中心。我的目光扫过,唤起了脑海中一段二十多年前的记忆。这时,仿佛耳际又响起当年父亲对我的喊声:“夜轿。”
我们客家人通常是喜欢用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深切情感的。譬如“夜轿”这个词语,就是我们客家人骂人时的专属称呼。它的本意是来源于古时候寡妇嫁人时,夫家必须晚上抬轿子去接亲的习俗,这种轿子就叫“夜轿”。我们客家人就用这个词来骂人,甚至用来骂自己的女儿。
我的父亲喜欢在他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呼我一声“夜轿”。
也许有人会想,对自己的孩子是不应该这样骂的。可偏偏我们客家人就常常用这样的贱称来代替自己对人的某一种爱的。我想,这就跟有的人把自己的孩子取名叫“狗子”“牛蛋”之类是一个道理吧!
离开秦村这么些年,村子上头似乎还是当年的蓝天白云,除了路边上田磡下多了几幢新式的红砖房外,村中的水田和树却是少了许多。远远的我就看见了父亲正好从我家大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件什么家什,样子有些急切。太远,父亲并不能看到在水口的我。
那时,父亲每一次要出门时就喊一声:“夜轿。”
于是,我也就常常跟在他的身后。就这样,我小时候可是去过不少的地方,也没少吃别人家的东西。我的嘴比别人都谗。
话说回来,在秦村,有谁有我父亲的人缘好啊!家里三天两头就会来那么几个人,有找父亲榨油的,有托父亲办事的,有向父亲借钱的,也有来请父亲去做泥水手艺的。父亲是一边经营着祖业油槽坊,一边做着泥水手艺。我家是一个十几口子人的大家庭,收入全靠这些来源。我家怎么会有这么大呢?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担子:奶奶和我父亲与六个叔叔,加上母亲和我与弟弟。爷爷上山后,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常常站在大门边,手里钳着一根冒烟的喇叭筒,倚着门框,看着秦村的水口,说,你爷爷这手,还真敢放。
父亲说这话时,秦村水口那几棵水口树的枝枝叶叶,也似乎窸窸窣窣地动了几下。
父亲每天晚上都逼着我写字,写不好,就用一管竹笛辗我的手指。写好了,父亲便会给我吹上一曲。渐渐的,村里村外常有人夸赞我,说,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好字真是不简单,而且很像我父亲的手笔。父亲听了这些话便引以为豪,对我愈加疼爱。
很多时候,父亲是在家忙,忙到砸脚跟。如若相熟的人来,父亲多半是泡好一壶茶,忙一下折回来,说几句话便又忙开去了。油槽坊的生意就是那样,相熟的人都理解。剩下我坐在油槽坊里的八仙大桌前,老往桌上看,我的颈脖子要伸到老长才够得着桌面。其实桌上除了一壶茶和几只粗瓷碗,并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于是那些人无聊时就拿我开涮:“细妹子生得咁标致,听哇你蛮会写字,写得蛮好看。”
亮亮书记是我熟悉的唯一一个当官的人。
那是一个星期天,亮亮书记找父亲商量大事来了。父亲还是边忙活计边和亮亮书记谈着什么事。油槽坊就在正堂边,中间隔着水车,父亲的手,回来时都是顺便洗过一把水,将手上的油渍稍作了清涤,到了桌边,再往自己的衫上抹一抹,仍然是一边说着话。父亲和人说话时,我都是竖起耳朵来听的。听亮亮书记多次提到了日本人,中途父亲问:“日本人只是要货,那他多少钱买那块岭地呢?”亮亮书记就说:“二十万。村里将来可以建村委会大楼了。”我听了亮亮书记说的这个数字,禁不住插嘴说:“这么多钱?可以买好多糖果哦!”父亲听见我的话便对我笑了笑,说:“这个夜轿。”仍然是一副自豪的样子。
亮亮书记也冲我笑笑,接过父亲的话:“侄伢子,到时叔叔给你买好多糖哈!”说话时还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脸。我笑呵呵地跑出去玩我自己的了。
亮亮书记走的时候有喊过我一声,我冲他笑了笑,没应声。我跑回正堂,父亲在叠收八仙桌上的茶碗。我说:“爸爸,亮亮书记好有钱哦,他为什么要这么多钱!”父亲笑笑,说:“亮亮书记有神经病,要钱治病,所以亮亮书记要爸爸去包下建筑工程,由他来运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神经病”这种病,便问父亲:“神经病会很疼吗?”父亲说:“不疼,但亮亮书记会疼。”我又问:“那亮亮书记的妈妈呢?”父亲还是笑笑,说:“也会疼。”父亲说完便不再理我,又忙活开了。
得告诉大家的是,我父亲在我们乡泥水匠行里是小有名气的,特别是砌乱石,许多匠人都不能不服气的。而且听说这一行有个说法,匠人到了一定资历就可以学一种邪术,在某个地方做点手脚,下个降头什么的,如果东家对匠人过分苛刻,建好的房屋就会出大事。父亲是唯一有资历还有好名声的匠人。
因为我家有个油槽坊,父亲很少接大活,相比接下一个大活来说,父亲接的活计要划算多了。帮人砌个灶台是双倍工钱,帮人移个坟墓就更是有赚头了。刚刚和亮亮书记谈的这件事情,多半是没有谈好。
过了没有多久,亮亮书记又来我家了。这次他还带了一个人来,听说是投资建矿的老板。老板许诺让我父亲负责包工,亮亮书记包料。老板说,之所以会找上门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亮亮书记极力推荐。上次父亲没有答应,他不死心,以为父亲是在摆谱。
父亲之前多次上过亮亮书记的当。父亲说:“有几次,工程做到中途被迫停工,原因是和当地村民发生纠纷。”那个老板就说:“这次开这个稀土矿是有背景的,所有事情会有人出面搞好。”
我听不懂那些深奥的话,就去房间练字。我在练习写“人”字。写着写着,这“人”字写得却像个“八”字;有的又像个“入”字;有的笔画出了头,像是个英文的“X”字,又像是个中文的“乂”字。我是自己在乱写。一般晚上都是父亲坐在床头看着我写,他要我写正楷字。可我却偏偏喜欢草书。所以偷偷写字时我就乱写,我就是想写草书,也想学父亲签名时的潇洒。可我不敢写父亲的名字,于是就写起了“人”字来。一个个“人”字排在纸上,正看像撒开的网,倒过来又像一根根的草。我想这些“人”字要是真是个人,认出来是我,那不笑话死人了。哎,一个小屁孩儿。他们大人这时是不会注意到我在做什么的。我还在写字。写了个“糖”字,但我不知道有甜蜜的意思;又写了个“死”字,但不知道背后的内容。这时,只听到父亲在房间外喊:“夜轿!帮伌把台子上嘅算盘拿过来一下。”我应声快速跑出了房间。太阳的光也跟着我的影子在快速地移动。
我得告诉大家,秦村的事没有一件是父亲不上心的,河坝、田埂、水渠,甚至封山育林,样样父亲都要上心。也要上工,然后都要捐一份子人工钱出来。
“想不到秦村还有这种资源!”晚上父亲上床后同母亲说。母亲问:“听说是卖给日本人?”父亲说:“老板有靠山,听口气,是私自开采,规模不算大。”母亲又问:“会不会到时候又像以前一样,做到一半就停下来?”父亲就说:“停就停,你以为是好事呀,听说淘稀土是有毒的。真开了矿到时还不知道会把秦村搞成什么样呢!我答应包工就是考虑到能及时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开发的泥土要往河里田里流,我第一个就不答应。”我忍不住爬到床头,大声喊父亲:“爸爸,到时候我也要去?”父亲骂道:“去蹲夜轿,歇你嘅眼去!”我“哦”了一声,缩回到了床上。
我应声之后,窗外,后山猫头鹰跟着我“咕咕”了一声。父亲和母亲还在床头呢呢呶呶说些什么。慢慢的我便睡着了。醒来后天已大亮,父亲已经出门去了。
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之后只要是星期天,父亲都会带我去矿上的。还有几个叔叔和我母亲也都要同父亲到矿上去干活。因为母亲似乎爱弟弟更多一些,便不太乐意弟弟去那种地方。母亲听人说,在淘稀土这种地方待久了会失去生育能力,于是弟弟也就只能在家由奶奶带着。像秦村这样的小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母亲也不例外。
我一个人在一簇黄竹的阴影下玩弹珠,弹珠是红粉石头磨圆的,有三十毫米的直径。在这里补充一下,我一个人玩的时候都是玩这东西,两颗石头珠子随时都在我的裤兜里一荡一荡的,母亲便常因我这样说我不像个女孩儿。对母亲的话我并不反感,我想像个男孩儿有什么不好的呢!有时候亮亮书记从我身边走过,兴趣来了也会陪我弹几下,但他大多时候是不如我弹得准的。他弹输了总是会“咯咯咯”笑几声才走,这时我就发现他“咯咯”笑起来时也像个小孩儿。我对亮亮书记一直都有好感,我觉得他是很会疼小孩儿的那种大人,不像我母亲,出口就是大喊大叫,破口大骂;有时我是讨厌我母亲的,我想,她是把自己的不愉快强加给了我。比如,我母亲的脚趾被踢烂过,时不时会旧伤复发,忽然就烂一个小孔。她疼痛起来就会动手打我。当然,是在我不听她话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在她脚痛时躲开,远远地到别处玩弹珠去。母亲眼不见心不烦,也就少来找我了。
在矿上待了有个把月吧,母亲的脚就又开始烂一个孔出来,这次特别严重。那天早上,我上学的钟点到了,母亲痛得钻心。我看到她的脸在抽搐,整个身子也都震震颤颤的,似有万蚁在叮咬的样子。母亲要我去请医生来,我一脸的不情愿,母亲想起身打我,但又实在是做不到,便提气骂我:“读驴书,端屎缸板啊!读了书有嘛嘅卵用呢?”我就委屈着说:“本来我就是要上学了!迟到了老师要罚我站墙根。”母亲无奈,便交代我喊一声隔壁家的堂姐姐过来。之后父亲听说了这事,也只是用眼睛象征性地瞪了我一下,深吸一口烟,说:“这个夜轿。”
星期天又到了,矿上清基工作完成得差不多,父亲的活计将要搞起来了。亮亮书记拿着父亲的皮尺在四处比划着,一副很专业的样子。父亲是不屑于理会他的,他同父亲比,充其量是个提家伙什的,父亲精于砌墙,更精于风水学。父亲说,建什么山头地势都有个字项,不可随意违之。亮亮书记折腾了半天走过去和父亲说道,父亲突然说:“你是瞎子吹箫——莫管!”父亲的声音很大。
亮亮书记说:“泥沙往河里排,一涨水就冲走了,这有什么不好呢?堆在这山头上,还是个事!”我听出一点意思了。亮亮书记是要父亲砌疏通排放的管道,往河里排。父亲的要求是控制在这一个区域内,不要向外延伸。真被父亲言中了,矿上搞建设,可能造成秦村的水土流失,好不容易建好的水坝就成摆设了。
亮亮书记说不过父亲,就装着委屈的样子说:“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工程大了,赚不到几个钱。”
父亲回家说起这事,补上一句说:“也不知道这‘神经刀’又会生什么鬼盘子出来。”别个人都是这么叫亮亮书记的,说他像把“钎毙刀”,又有个神经病儿子,也就叫他“神经刀”了。我却不怎么讨厌这个人,至少我感觉,他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坏。
这不,又是一个星期天。亮亮书记一见到我,就喊我过去,让我写几个字给他看,写好了给我糖果。要我写字,我可乐意了,我的字写出来从来没有人说不好。在秦村只要谁说起写字,就不能不提到我,说一个小女孩儿字能写得这么好简直是奇迹。母亲却当着别人面打击过我,她说:“这种东西没吃没喝的,好又有什么用?还不如长大嫁个好人家!”听说我的表姐就是嫁了个大学生,一个月工资有七八千,这个数字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讨两次老婆。所以母亲不想我学写字,让我多学学针线。父亲说:“男人女人都慢慢会变,‘夜轿’也不可能永远跟你走老路过日子。你看这世道,三十年前是那样,现在又是这样,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理?”母亲说不过父亲,也就随我去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写父亲的名字,父亲的那几笔写法,是我看过的最帅的,所以我也想写出这么好看的字来。
亮亮书记也说他最喜欢看我写我父亲的名字。字写好了,亮亮书记真的给了我糖果。就这两颗糖,我也是回到家后偷偷地把弟弟喊上一人一颗分了吃。弟弟很可爱,有什么吃的总会给我一点,这让我知道,大人们背着我有多偏心,尤其是我的奶奶。奶奶把她生下的那七个男人当做是她一辈子最大的功德,一年一个,只有大叔隔了我父亲两年。奶奶说,到下一代就不如了,看看秦村人单苗独崽的太普遍了。她说,有人就有一切,人多力量大嘛!可是,她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样拼命赚钱才让大家吃上饭的。我虽不懂事,但有时看到父亲一天接一天做事起早摸黑,我也想,怎么只有我父亲有忙不完的事,一家人都这样清闲呢?我对奶奶的不理解,确切地说是她对弟弟的爱与对我的不上心形成的反差,叫我不能释怀。
就是回到家后偷偷地把弟弟喊上才一人一颗分了吃的那两颗糖,也被奶奶知道了。父亲被奶奶说偏心,没有给弟弟买糖果。父亲就问我糖果怎么来的,我才如实说了。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责备我。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对家人大声说话,甚至从没说过一句过分的话。对外人,父亲却常常不客气地针锋相对。
前前后后,亮亮书记让我写了四五次字,都是写我父亲的名字。只是这后面几次他都只给我一颗糖果。那纸一叠一叠的,真是白,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好的纸。亮亮书记让我把字写在那白纸上一处格子里,他说我写在格子里的字更好看。每一次他都双手紧紧地将白纸抓好,生怕白纸移动会影响到我写字似的。我看他样子就更加得意了。我想父亲是对的,我写好一手字,还可以自己赚糖果呢。
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大家一件喜事,我的大叔说上了一门亲事。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和父亲陪我大叔他们去看那家的姑娘,回来时顺路,父亲带我一起去老板家结钱。老板说:“钱都结材料去了,让神经刀先了一步。”老板也知道亮亮书记的大号呀。老板为了证明没有骗人,拿来了账目,父亲目光一颤,看到好几个写有自己名字的账单,接过来一看,材料数目不对。更可疑的是,这几份账单父亲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看了我一眼,对老板说:“这字不是我签的啊!从始至终我就没见过材料采购单。”老板满脸疑云,我抢着说:“这字是我写的,我认得这纸。可是我写的时候这纸上没有别的字呀,上面还是好白好白的呢!”老板若有所思,过了半刻钟左右,对父亲说:“我不妨告诉你实话,搞这个矿的钱都是神经刀找路子帮我借贷来的,刚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私自开采稀土,要罚款。钱只能到时候看看,我手头确实没钱了!”父亲领着我,很平静地离开了老板家。
我和父亲出了老板家的门,并没有回家。夜晚的山道,虽没有下雨,一样有些泥淌路滑。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忽明忽暗的星星在一闪一闪的。偶尔也可以从山中听到猫头鹰叫或一两只夜鸦的扑翅声。
父亲和我去了亮亮书记家。我没有进父亲和亮亮书记单独待的那个房间。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想,亮亮书记是怎样一个人?他会不会打我的父亲?如果真打起来了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是不是要跑到他的厨房去,拿刀杀了他?我不能让他打我父亲。我甚至偷偷探头去看他家的厨房。亮亮书记的妻子带着儿子睡在一张床上,很慈善的一个女人,她时不时看一眼儿子,又看看我,我猜她也是在想心事。多么可笑的女人,生一个神经病儿子,还不如生个女孩儿呢,她还不知道吧,亮亮书记让我签字,骗了我们的钱了。可我还是恨不起她,我想到我母亲从来没有把我这个女孩儿当宝贝,如果我母亲也能像亮亮书记的妻子爱孩子那样爱我,该多好啊!关于父亲和亮亮书记的谈话内容,我无从知晓,不过最后,父亲拿到了一些钱。
后来,矿被封了,再后来又开了。不过都与我父亲无关了,有关的一件事是亮亮书记同别人说是我父亲在矿上做了手脚,下了类似于降头什么的,所以矿上迟早要出事的。秦村的河一年不如一年,秦村的人都恨死了那家稀土矿,这山,方圆几里都生不了树木花草。
再再后来有一次,父亲说,稀土不值钱了,才四万元一吨,跟四十万元时相差十倍。我说:“跟等屋家又冇关系,一分钱都拿唔到。“
父亲会突然就对我喊:“夜轿,练你的字去!”有一回,我终于是忍不住了,就问父亲:“夜轿是什么意思?”父亲说:“不讨人爱的人,在社会上为害的人!”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父亲分明是对当年的一些事不能释怀。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大志趣,绝对比现在的我高尚。
此时,父亲正坐在大门口晒太阳。天气真好,太阳不辣,没有山风吹过。
父亲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快到家门口的禾坪上了。只见父亲对我笑了一下,就扭头冲厅堂内轻轻喊了一声:“哎,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