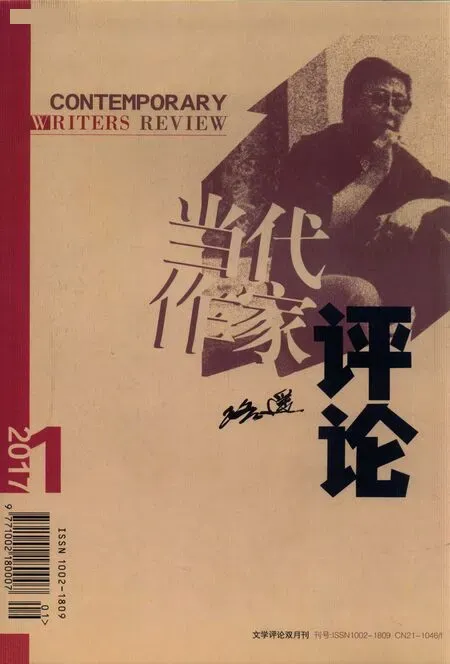主持人的话
王 尧 韩春燕

主持人的话
王 尧 韩春燕
主持人的话 将陈忠实《白鹿原》的经典化过程作为“问题”加以考察,是本期组稿时设计的话题。80年代以来,讨论一部作品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其时间之长,问题之集中,可能莫过于90年代出版的《白鹿原》了。而且,《白鹿原》甫一问世,就被一些批评家定位为“经典”之作。此后20多年,尽管对《白鹿原》的评价仍然有不少分歧,但《白鹿原》的“经典”意义和位置事实上已经被充分阐释和建构起来。它不仅是陈忠实自己用来枕棺的书,也被视为一个民族的“史诗”。因而,无论是《白鹿原》文本,还是《白鹿原》经典化的过程,都仍然是一个“问题”。
如何讨论这一问题,房伟在论文中提出了他的思路和方法:从《白鹿原》经典化过程入手,不以“经典永恒”本质论为思维方式,也不取单纯建构论文化研究,而是将《白鹿原》经典化作为“问题”,将《白鹿原》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与“十七年”、80年代的结构关系中,探讨争议内在因素,更深层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困境与机遇。徐刚的论文不约而同地显示了这种思路和方法分析《白鹿原》的有效性。——这与主持人的思路和方法比较吻合;需要补充的是:在结构关系中探讨争议的内在因素时,也将呈现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复杂路径而不以主潮论述遮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发现关于《白鹿原》的文学批评背后的思想文化分歧以及这些批评如何被取舍而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基础。
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在以变化了的、甚至是替换了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观重新处理政治史、革命史、文学史,重新叙述历史、革命史和重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后,文学反映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换。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关于“革命叙事”的评价发生了变化,相关作品的意义在文学史论述中也发生了位移;而在文学创作中,“宏大叙事”被解构,“经典”的标准也相应变化。我们今天仍然讨论的8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品,几乎都是这些变化的一种结果,但似乎缺少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变化结果,即差不多是公认的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和80年代主潮中的作家相比,陈忠实在80年代虽然也有重要的作品,但无疑不在中心或先锋的位置上,此时的陈忠实可以说一种沉潜的状态。如果我们注意到陈忠实在“文革”时期的创作,就会意识到,此时的陈忠实肯定经历了巨大的思想阵痛和裂变。当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后革命”时代的作家们在尚未处理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又忙于处理文学与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又一个巨变的年代,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反映世界。在一座城市,陈忠实回溯历史,承接80年代“建构”起来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成果,创造了《白鹿原》;贾平凹将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置于“解构”以后的困境,创造了“废都”这样的文学世界。这两部作品在今天也许都可以视为“经典”之作,但被建构的方式是有很大差异的。房伟因此认为:“《白鹿原》杂糅“十七年”、80年代与90年代年代诸多经典诉求,其复杂性形成经典阐释巨大空间,也造成经典通约性的难度。”徐刚则对《白鹿原》进行了再解读,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白鹿原》与话语权力的微妙关系以及文本的内在矛盾:“小说其实处处显出对主流思想意识、时代风潮与文化趣味的顺应,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通过小说及其周边文本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作者本人的内在旨趣、价值追求和心理因袭又与其文本表现有着微妙差异,这使得小说不失时机地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矛盾与龃龉,比如意识形态与历史观的选择,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微妙的批判等。”
在对《白鹿原》的“批评史”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房伟提出,如何看待《白鹿原》对不同时代叙事规则杂糅式的共时性呈现呢?我们是否因争议否认《白鹿原》是文学经典?要看清这个问题,除了关注《白鹿原》的经典因素构成特质,《白鹿原》的经典化过程,更要理解问题的另一个背景,即文学经典正面临着终结。《白鹿原》的经典化困境,也存在于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王安忆等中国最优秀作家的优秀之作:“利用暧昧的价值杂糅,制造有限的“禁忌冒犯”与阐释多样性,这几乎成了很多90年代以来优秀作品的套路,也是作品在体制内获得经典许可的方案。但如果中国文学要真正形成民族经典,就必须有更具审美通约性的经典尺度,即内容的丰富复杂性,审美的独创性,与民族意识的独特性来衡量作品。这样,经典塑造才能摆脱无益的内耗与焦虑,也摆脱西方影响的后殖民色彩,形成真正的中国现代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