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關係再平衡:中國的“集體勞權”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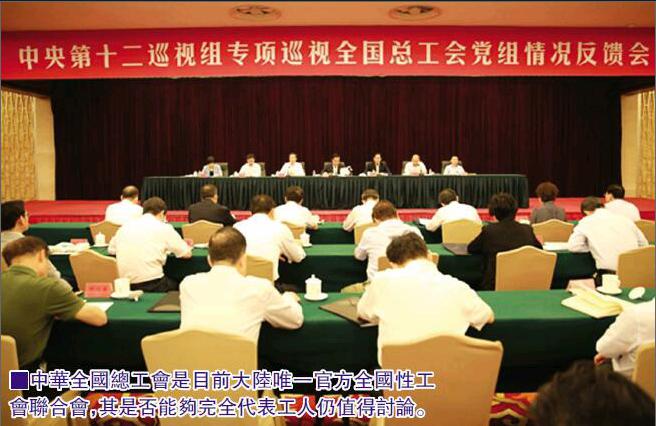

勞動權益保護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雖然兩岸四地具體情況不一樣,但是大家都面臨到不少普遍性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以來,勞權保護屢屢遭受越來越多的挑戰,特別是勞資雙方力量的不對等,使得工人維權、發聲受到了較大的壓制。
誰的工會
在中國大陸,總體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勞動法制化的趨勢不斷加強,通過各項制度與法規的建立來改善中國的勞動環境。從1994年訂立的《勞動法》,以及2008年修訂的《勞動合同法》這兩部重要的法律有效地規範了中國的勞動環境,特別是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工人個體的權益保障比起以前有了明顯的變化,勞動合同法在制度層面上對於工人的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合同期限等都有了更加明確的保障。
回顧歷史,血汗工廠曾經在中國大地上屢屢出現,1993年深圳葵涌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案,87名年輕的女工在火災中喪生,57人受傷,那樣的慘烈狀況換來了隔年《勞動法》的誕生。20多年來隨著勞動法律的不斷完善,勞工自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血汗工廠在國內得到了大力的排查和整治,雖然目前不排除個別地區仍存在少數嚴重的血汗工廠壓榨勞工的情況存在,血汗工廠的存在意味著工人基本的生存權利得不到保障,目前總體而言,絕大多數勞工的生存權利得到保障,他們希望提高各項權益的保障水準,而非是僅僅停留在最低標準之中。
而當工人權益受損時,理論上工會扮演了維權的重要力量。在不少成熟國家與地區,工會的正常化、合法化使得勞資雙方力量得到平衡,畢竟工人勞動權益的保障,只靠單個工人的自我維權是難以實現的,而將工人的權利保障託付給資方的管理改善來實現更不現實。在中國,工會一元化是其基本的國情和中國特色,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境內各級地方工會和產業工會的領導機關,“全總”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工會對於監督資方、政府,以及內部的民主制度運行上顯得不足,無法發揮原有的功能。同時,全總能否有效地代表全體工人,還存在質疑,仍與理想狀況存在較大距離。在中國,目前工會的目標是一方面促進企業發展,一方面保障工人利益,這是與其他地區鮮明的不同之處,在市場經濟成熟地區,工會只對會員負責,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會不考慮企業利益,而是更加強調保障工人的合法權益。而在我國,全總(工會)強調要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依法保障職工的利益。當企業與工人利益、目標一致時,這個主張是可以實現的,企業也會盡力解決相關的問題;而當企業與工人利益相衝突時,工會的身份問題就顯得較為尷尬,也就很難處理這樣的矛盾。目前,我國產業工會的力量比較弱,地方工會的地位不明,企業工會中勞資力量不平衡,大部分企業工會都被企業行政力量、僱主控制,根本無法發揮工會原有的功能。比如前一段時間,沃爾瑪的工人反對新的用工制度,抗議“綜合工時”,沃爾瑪的工會組織不僅不能代表職工發聲,反而站在僱主一方來對付工人。為此,沃爾瑪工人將這一工會視為“黃色工會”,並要求上級工會予以改組。嚴重脫離工人群眾,是中國工會長期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中央也已經看到了問題嚴重性,特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工會改革的問題,明確指出要克服“四化”的問題:即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應該說,這個問題提得很中肯也很尖銳。但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
在中國,雖然工會組織龐大,但難以真正代表工人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於工會無法完全代表工人,所以中國的勞資關係就成為一種特殊的現象,勞工運動更是一股薄弱的力量,在維護勞動權益的路上仍舊艱難前行。當然,全總在多年的工作中也有為工人權益保護而努力,特別是在勞動立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地方工會,比如廣州、大連、天津都有一些堅定維護勞工權益的工會負責人湧現,但在中國,這樣的個案和人物還尚未有更多的普遍性。
當下,關於工會與勞工力量的分離衝突在一部分行業和地區是可以清晰看到的,機關化路線和自下而上路線並存也是客觀事實,未來這種力量的分離衝突,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靠誰救濟
當然,在一般的制度設計中,工人除了工會以外,面對權益被侵害時仍有兩種救濟途徑,第一種是勞動行政處理途徑,通過勞動監察等來進行維權,接受舉報等,特別是相關違法行為。第二種是勞動合同爭議處理途徑,包含了仲裁、調解、訴訟等方式。在制度面看,這樣的設計是有效的,但至於效用有多高,始終都會面臨到實施、執行的問題。就比如《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全國各地拖欠工資的情況得到了改善,個體勞工特別是農民工欠薪的情況大幅減少,但是當面對集體性、大面積侵權時,很多時候制度發揮的功效又出現了其局限性。在東莞就出現了未給上萬名工人辦理社保的集體侵權爭議,包括多年不漲工資的爭議,在現行的制度下很難解決,很多時候企業把最低標準當成了正常標準,大行其事。例如集體合同普遍存在著走形式的問題,這種合同與工人的期待差距較遠。在一般的認知中,工人除了有公權力的救濟之外,罷工給企業施壓的權力應該擁有,但在實際的救濟途徑中幾乎不存在。關於“罷工”,目前缺乏制度建設和法律規範,現實中有些罷工事件由於政府方面的“理性對待,法制解決”,使得罷工事件能夠妥善解決,並促使勞資關係達到新的合作,比如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的處理。但也有一些勞資經濟糾紛性質的罷工事件,被政府作為“維穩”事件來處理,由國家機關的強力介入而把問題複雜化,勞資矛盾演變成工人和政府的矛盾。
因此現階段以及未來一段時間要更加關注集體勞權的保障和行使問題。《勞動合同法》實施十年以來,工人的個別勞權保障有很大的提升,但集體勞權則長期受到漠視。對於工人而言,不僅擁有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為主要內容的個別勞權,還應該擁有集體勞權:團結權:組織、參加工會的權利;談判權:與僱主、企業等對等談判的權利;罷工權:用罷工方式反映訴求的權利。這即是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的“勞工三權”。在市場經濟國家,通常不用擔心工人的組織問題,團結權能夠充分保障,工會代表工人進行集體談判,談判破裂後可以通過罷工權的行使,形成壓力手段逼迫資方再回到談判桌上。在我國,由於工會的“四化”問題的存在,致使工會不能有效地代表職工,而僱主對於企業工會的介入和控制,又使得工會缺乏獨立自主性,並且,在集體協商談判中工會又不具備壓力手段。由於“勞工三權”無法有效落實,使得勞資之間無法形成一種集體性的力量平衡關係。應該說,《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勞動者個別權利的維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集體勞權得不到落實,個別勞權是沒有保障的。目前我國的集體勞權體系尚不健全,要想系統性地解決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要走。
我們強調勞工三權的目標不是為了對抗和鬥爭,而是希望通過老勞資集體權利的對等和平衡來構建出一種和諧的勞動關係。雖然近年來一些機構、專家學者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指標來測量勞動關係是否處於和諧的狀態,但是在實際的運作中難以根據指標來實行和運作。比如南海本田汽車企業通過部分罷工、談判等方式最終形成了一個理性溝通的機制,滿足了企業發展生產與工人要求加薪的狀況,二者兼顧,這就是和諧最簡單的狀態: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就是和諧。而一方特別強,另一方特別弱的情況下,二者就不可能達成和諧的狀況,因此在中國特色的勞動關係中,政府直接保護工人當然重要,但政府沒有能力直接保護每一個工人。市場經濟下勞動法治的一個普遍的做法就是,授權工人形成集體力量,通過勞資自治來實現工人保護。只有這樣勞資雙方關係才能對等,雙方力量才能平衡,勞資關係和諧才能實現。
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帶來了正面的、積極的改變,未來勞動關係的長遠發展更多地要依賴於集體化的規範與調整,只有鼓勵勞工形成集體的力量,才能夠勞資雙方平衡,讓勞動關係更加和諧。在現行的制度體系內,勞工問題不僅僅被看做是經濟議題,涉及到政治、社會層面,因此中央對此慎之又慎,知曉其中的利害關係,故而未來在逐步解決的過程中,應該難度亦很大,必須克服重重障礙。
言尤至此,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前提是要保護勞工權益,這一目標要通過勞、資、政三方的共同努力。而勞工權益究竟包括哪些,我們究竟清不清楚?現階段,我們發現一般大眾都對勞權保護的內涵認知過於狹窄,太過具體。而且勞動權益保護不僅僅是單項權利,而是“一捆”權利,一個權利束,一個權利體系,不應該完全狹窄化。勞工權益應該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工人個人權益,包含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後在形式上就對這些個人權益進行了具體化的保障,當然由於目前社會環境的影響,勞工的工資佔據社會財富的比例過低,工人對於加薪的渴望與訴求正在持續增加,需要得到各方的重視;而在“工時”方面,超時工作的情況仍然存在,但相較於十多年前而言,現在確實改善很多;至於“勞動條件”,很長的一段時間,社會與勞工界都在關心“安全衛生條件”,以前的礦難事故頻發,近兩三年得到了明顯的改善,而職業病特別是慢性職業病的影響,比如塵肺病,確實在影響著中國勞工的身體健康,有NGO組織指出,中國大約有500-600萬的塵肺病患者,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同樣在社保問題上,雖然有勞動合同的強制規定,但是對於農民工群體的保障仍然相當有限,不僅納保率低,更有保障標的也低,對於弱勢的農民工群體而言,保障幾乎難以達到。因此當外界有人認為中國的勞工標準過高時,在事實面前,這完全是一種荒唐的說法。這個過程中仍然反映出當前中國,集體勞動權的薄弱,工人們無法通過集體談判、集體行動來督促企業繳納社保、保障基本權益,加上工人無法在現有工會的處境下成立第二工會,對於“虛位工會”只能不承認,卻無法擁有實際的組織權。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工人應該在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有權要求工會為工人發聲,鼓勵工人對等、集體談判,只有明確的集體行動才能夠讓弱勢的勞工團體掌握話語權。當然,目前現行的法律中並沒有賦予勞工罷工權,因為考量到對於企業、國家、工人而言,罷工的成本都是很高的,但是長此以往,惡性循環下去,其實對全體利益造成的損害更大,因此與其單純禁止和壓制罷工,不如考慮如何規範罷工權、規制罷工權,形成多贏的局面。
多方定位
這十多年來,中國勞動法制建設快速,法律體系也得到了較大的完善,從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的頒佈實施,有效地規範和調整了中國的勞動關係,不僅保障勞動權益,更能夠促進企業穩定、社會發展,儘管外界有少數聲音認為法律的完善,加大了製造業等的成本,使得中國的用工成本增加,迫使企業、產業向外轉移,其實從最近玻璃大王曹德旺前往美國開設工廠的案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國並非勞動合同法增加了成本,而是在於稅收負擔、物流負擔、不透明成本的增加使得工業成本不斷提高,讓不少企業難以負荷。《勞動合同法》只是增加了合理的用工成本,其標準仍屬於最基本的層面,而遠遠沒有達到合理的水準。臺灣在1984年通過了《勞動基準法》,當時也是爭論、反對的意見強烈,不少企業界反對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中增加用工成本,但今天回過頭來觀察,就可以發現,正是因為勞基法對於最低標準進行了規範,對於勞動權利做了基礎保障,才有了三十多年來台灣在勞動權益日益得到保障的同時,經濟也得到快速发展。
對於大陸的《勞動合同法》很多人認為我們的保障比其他國家更嚴格,比如關於“書面合同”的硬性要求。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社會信用問題,沒有書面的合同簽署,一旦出現勞動爭議,勞工幾乎沒有有力的武器來保障自身的權益。而關於勞動合同終止補償,在海外通常以“資遣費”的名義支付給員工,中國並不高於國外的規定。這些規定並非是立法者希望獨樹一幟,增加企業用工成本和社會成本,而是立足中國現實並借鑒國際經驗所作出的規定。這種規定不僅只對工人有利,對於穩定企業勞動關係,增強企業的持續競爭力都是有促進的。
由於大陸的勞資環境與港澳台地區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在組織、談判、罷工權利上,港澳台都已經基本實現,因此大家所面對的問題並不一樣,特別是中國特色下的工會制度,更對於中國工人的維權之路帶來變數。在中國語境下,想要合理保護勞動權益,推動社會良性健康發展,各方扮演的角色都不可或缺。特別是中國勞資關係的“三方四主體”的特點必須要充分認知。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一般只有工人、資方與政府三方,但是在中國同樣的三方,卻出現了四個主體:工人、工會、資方、政府,這樣的特色就決定了各自發揮的功能也多有所區別。
從政府來看,應該明確定位在勞資雙方之上,以勞權保護為基準,實現勞資力量的平衡,和諧整體勞動關係,特別是改善勞資關係中勞方弱勢的這樣一個局面。如果政府只依靠行政力量來進行勞動監察或者處理,這些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畢竟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問題面向。政府要努力賦予權利給工人,讓勞資雙方“自治”,在集體勞動關係形成的背景下,雙方力量平衡才能有效“自治”,當然政府有其希望控制局面,維護穩定的壓力,但是如何一方面保證社會穩定,更一方面放權給勞工,賦予集體權利,是值得探索的,政府在未來的施政過程中,應該站在總結過去30年中國勞工環境、經濟發展的成功與不足的基礎上,制定更加長遠的目標。
對於資方而言,西方社會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形成了資產階級,擁有了穩定的“資方力量”,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在30多年的時間內快速地形成了這個群體,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認知還停留在“賺錢、發財”的資本原始積累、聚集的階段,對於公平、正義的認識還未能充分,在成熟的社會中,資方需要的不僅僅是賺錢,自己也必須在和諧的勞動關係與社會責任中承擔重要角色。特別是企業中的HR角色,現在往往是用來管住工人,企圖減少成本,提高企業效率,這並非是一個可持續的企業發展之路,而真正的關鍵在於調動雙方的積極性,發揮出最高的效能,力求多贏。
對於工人而言,中國3億多勞工,目前仍舊處在一個沒有組織的“原子化”狀態,雖然有名義上的工會,卻非“工人的名義”,無法真正有效地代表廣大工人,工人在沒有充分組織救濟的情況下,更多地會希望通過自力救濟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對此無論是國家、資方還是現有工會都應該充分看到工人的變化,特別是階級意識逐步形成的變化,需要合理來引導,要用善意、法制的方式來不斷回應工人的訴求,引導工人集體勞權的保障,從力量的角度平衡勞資雙方。
也只有多方在清晰的定位下,才能在一個博弈的局面中共生共進,打造一種和諧的勞動關係與社會狀態。
常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中國勞動關係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