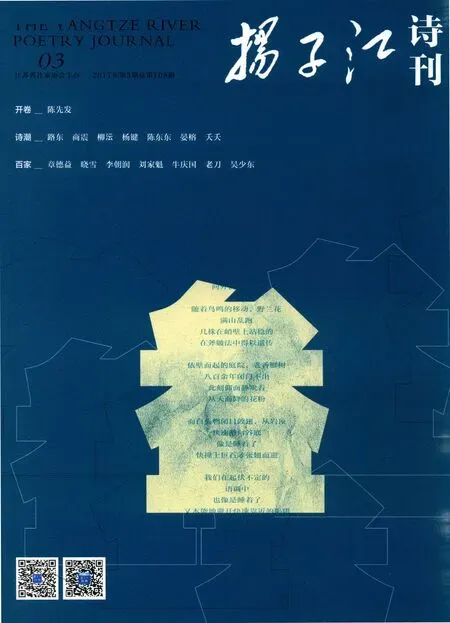黄梵的诗
黄 梵
黄梵的诗
黄 梵
秋天让人静
安静了,就在心里深深享受
只想被一棵巨大的水杉囚住
那些藏在心里的话,不过是被秋风再次说出
安静,使声名变得遥远
在一座山上,提起它已等于放弃
晚霞是山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没人在意
山吐出的血是多么美丽
几只麻雀,好像小心安放着惊恐
直到今天,我走过的路都弯得像年轮
我羡慕,天上那一团团厮杀的星群,有对安静
的执迷不悟──
我不住地仰头,学会用安静在深夜里走路
中 年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中年人的胡子
胡子,总向来人低头
不是凭吊,就是认错
甚至像围巾,悉心裹着一个人的叹气
只要有风经过,它也想飞起来
它一直往下长,是想拾捡地上的脚印?
是想安慰被蚯蚓钻疼的耕土?
是想弄清地上的影子,究竟有没有骨头?
是想长得像路一样长,回到我初恋的地方?
它从不记恨我每天刮它的疼痛
它从不在乎,我是它飞不高的祸首
当然,它也像一根根铁链
把我锁进了中年
一旦睡梦来临,它便腾出一千只手
彻夜为我化妆,让一个陌生人
在清晨的镜子里等我
二胡手
过去的日子是人民的,也是我的
是野花的,也是制服的
是码头的、处女的
也是河流的、毒妇的
下午醒来,我说不清
自己是盾牌还是利剑?
广场上,有人拉着忧伤的二胡
他有理由让弦曲中的毒蛇伤及路人?
他的脸儿整个隐没于旧时代的黑暗
如果来得及,我愿意
让女儿也把两只小耳朵准备
此刻,我感到过去就是他的表情
不再渴望新生活,像哭湿了的火柴头
与今天再也擦不出火花
过去变成泪珠,但没有地方往下滴啊
蒙尘的盆花也害怕它来洗刷
过去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听曲的新人背着双手,就找到了热爱?
孜孜不倦的二胡手啊,用弦曲支起一道斜坡
我奋力攀爬着,并且朝下滑落
老 婆
我可以谈论别人,却无法谈论老婆
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如同我的左眼和右眼——
我闭上哪一只,都无法看清世界
她的青春,已从脸上撤入我的梦中
她高跟鞋的叩响,已停在她骨折的石膏里
她依旧有一副玉嗓子
但时常盘旋成,孩子作业上空的雷霆
我们的烦恼,时常也像情爱一样绵长
你见过,树上两片靠不拢的叶子
彼此摇头致意吗?只要一方出门
那两片叶子就是我们
有时,她也动用恨
就像在厨房里动用盐——
一撮盐,能让清汤寡水变成美味
食物被盐腌过,才能放得更长久
我可以谈论别人,却无法谈论老婆
就像牙齿无法谈论舌头
一不小心,舌头就被牙齿的恨弄伤
但舌头的恨,像爱一样,永远温柔
帽 子
风一来,头上的帽子就想跳崖
想倒光它装满的黑暗
想抱住地上青草的卑微命运
它不喜欢被我顶礼,高高在上
它要像柳条那样,弯下腰去
看虫蚁花草没有一个穿着衣裳
地上的纸屑、痰迹,也拥有自己的忧伤
它不知道,它用口含住的这颗头颅
其实是一滴浑浊的大泪珠
我坐在山间的风口
知道它像一只鸟,想回到正在盘旋的鸟群
知道它对我,早已日久生厌
当风把它吹落在地
心高气傲的我,也只得向它低头弯腰——
拾起帽子的一瞬
我认出,它就是儿时的我啊
玄武湖即景
那些快艇,让湖里的浪也长大成熟了
我恍然大悟,堂皇的浪花已娶妻生子
风筝让树木仰起头来,我的女儿
还想稳住最初的慌乱,一轮白日残月
要 把谁的心来搅动,那眼神像鹰,让我直冒虚汗
像浪花在闪烁的,还有老人脸上的皱纹
他们站在湖边,努力要平息心中的迷乱
是湖水的一生,让落日小得像一只酒盅
它沉到湖水里,去挽留腰身妖冶的乱流
前 湖
湖水发暗,像害着疾病
我最多像麻袋,再帮它动几下
飞鸟快速地,“它只剩下一条路了”
湖水多么像我,这辈子被困在这里
但它的眼里,看不出有丝毫的遗憾
活着,就枕着逐波的快乐
风再小,湖的生命依然刺目
像深夜的灯,一直苏醒着
湖还要以它的涟漪、战栗、心绞痛
为湖边的恋人做些什么……
金陵梧桐
一条梧桐路,可以让我停下手中的活
每片叶子都是小小的耳朵
就算隔着最宽的马路,我的自言自语
依然会让叶子在风中侧目
一排风华正茂的梧桐,多么优美
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才能
一样的多情,一样的徒然忍受!
我要把去过的城市,都简化成一条梧桐路
听凭叶子把声音的波涛安排!
不能接受梧桐的街道,难免肤浅
在梧桐面前,我显得废话连篇
冬天是它扎起长辫的时节
我嘴唇微启,无限感慨
一排梧桐在怎样忧戚地看着我呀!
小 路——致钟山
小路沿着围墙,独自遁入林中
它要逃离窗户的眼睛?
它要聆听知了试吹的号角?
它要到林中,带回一只迷途的狗?
哗哗的风,让树都弯着身子恭迎它
它在林中越走越消瘦
脚印和落叶是它的主食
它用越来越细的毛线,护住山的脖子
翻过悬崖时,它凝视着人类的惨剧
它忍受着秋天这张黄疸的脸
向戴着山岚假发的峰顶走去
谁也不知,它究竟要干什么?
当黑夜来临
它成了月光下蛰伏的一条眼镜蛇
慢慢在山顶昂起头——
莫非它自不量力,想给
挥着月亮银盾的黑夜,致命一击?
老码头——致黄州码头
我小时居住的码头,已经消失
只剩远处永不迟到的钟声
江水曾把渔火捧在掌心
不理会星光发出的邀请
码头——那颗镶在黑夜大衣上的金纽扣
我曾用打滚的身子,想把它擦得更亮
江水——那副软如乡愁的好嗓子
我曾聆听到天明
某天,为了长大,我弃它而去
我的脚步从此无法入眠——
它们像不停搬家的蚂蚁
打算永远陪着百感交集的道路
直到没法医治的皱纹,爬上我的脸——
中年像尘土,哪怕被阳光照亮
也带着沉沉浮浮的不安
甚至带着囚车的擦伤,乱拾地上丢弃的处方
许多年后,我回到码头——
只看见夜里已经变瞎的江水
渔火的动人眼睛,已不知被谁挖走
曾经热闹的码头,已埋入十亩安静的良田
只剩几根月光的寒鞭,不停抽打我的记忆
无声的塔尔寺
到了塔尔寺,我无话可说
我不可能再比塔尔寺清白
纷纷涌来的诗人,都是好演员
我们转一圈出去,就转出了心里的黑暗?
一个上午,我把祖国在心里搬来搬去
我 多贪婪,既想守着城市,又想在这里度过一世
这里安静的慈悲,真能让一个罪人安静吗?
这 些冰冷的酥油花多么令我钦佩,它用一生躲避着温暖
还 有那些千里叩拜的人啊,这里的干净、清澈
哪样不是他们叩拜的贡献?
和他们一比,我们便像沙漠中的流水
始终来路不明
我一生的愤世嫉俗,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我家乡的残寺污水,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垦丁①的海
浪像孕妇,可以生浪
而我,可以从浪尖找到许多东西
找到磨亮的锄头、擦亮的皮鞋
找到汹涌的泪水、醉醺醺的酒瓶
找到垦丁的白灯塔、画画的白纸
我找到的所有白花,很快都会凋谢
我找到的所有白天鹅,很快都会飞走
我找到的最白的纯洁,像一把亮剑
很快把我划伤
作为千里之外的来客,我听得见自己在浪尖呼喊
①垦丁系台湾最南端,面朝太平洋,海碧蓝,浪雪白。
作家简介
吉狄马加,彝族,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多次荣获中国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组织机构的奖励,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2014年10月获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2015年7月获第十六届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2016年6月获“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2016年11月获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卓越诗歌奖和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诗歌奖。2007年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担任该国际诗歌节组委会主席和“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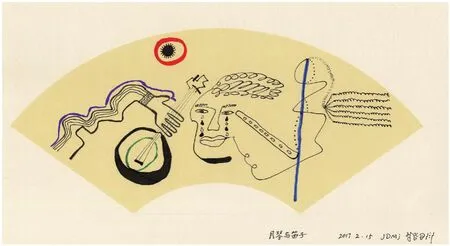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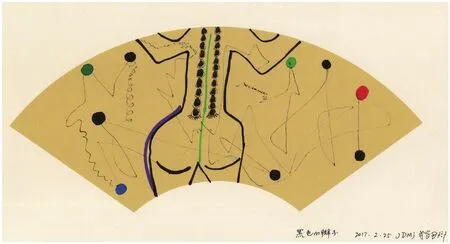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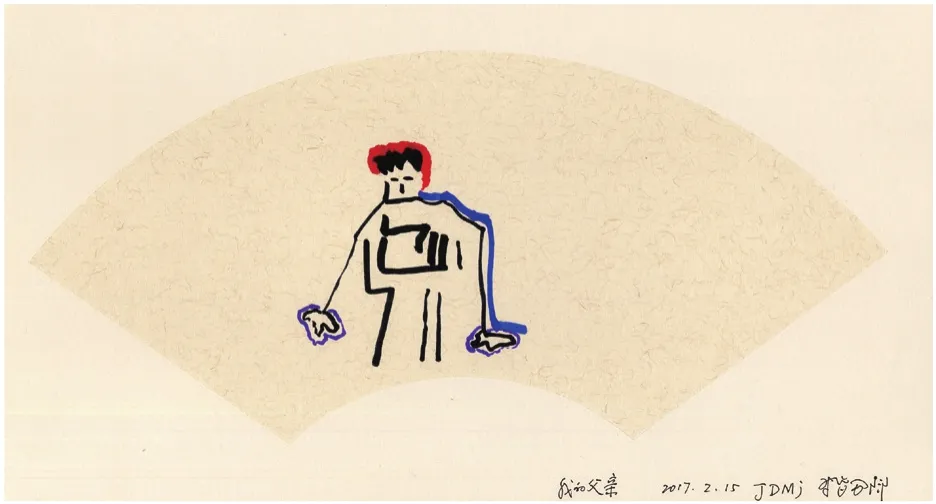

- 扬子江诗刊的其它文章
- 奥拉·克莉斯迪诗歌选
- 陈先发的诗
- 蕙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