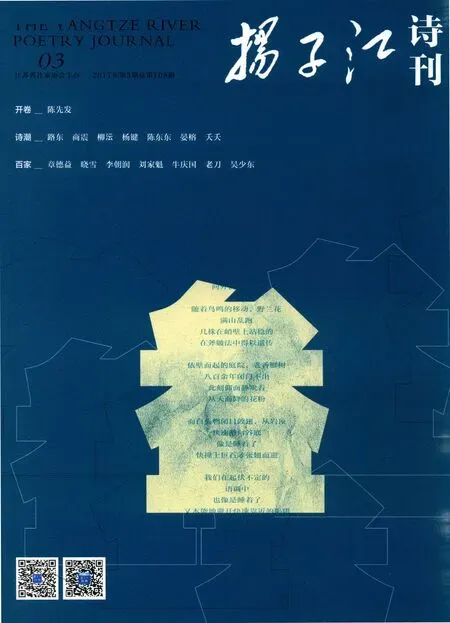奥拉·克莉斯迪诗歌选
高 兴 译
○ 译介 ○
奥拉·克莉斯迪诗歌选
高 兴 译

奥拉·克莉斯迪(Aura Christi,1967-),罗马尼亚著名女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1967年1月12日出生于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希讷乌。1990年毕业于摩尔多瓦国家大学新闻系。1993年移居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现为罗马尼亚著名文化杂志《当代人》主编。
奥拉1983年发表诗作。至今已出版诗集:《在影子的另一边》(1993)、《反对自己》(1995)、《盲目仪式》(1996)、《国王山谷》(1996)、《别碰我》(1997)、《最后一道墙》(1999)、《北方哀歌》(2002)、《诱惑之书》(2003)、《质朴的花园》(2010)、《寒冷球体》(2011)、《悲剧梦想者》(2013)等;散文集:《生命片段》(1998)、《流亡迷宫》(2000)、《山那边》(2005)、《生者宗教》(2007)、《三千个符号》(2007)、《命运练习》(2007)、《生存饥渴》(2010)、《尼采和伟大的正午》(2011)等;长篇小说:《夜鹰》(2001)、《雕刻家》(2004)、《异乡人之夜》(2004)、《羊羔之雪》(2007)、《黑暗中的房屋》(2008)、《狂野的圆圈》(2010)等。此外,她还翻译过阿赫玛托娃等诗人的作品。
奥拉深受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经典诗歌的影响,常常在诗作中探讨生存、苦难、自我、命运、流亡、生与死、黑暗与光明等主题,其诗歌内在,深沉,幽暗,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和感人的内在光芒。她的诗歌得到了罗马尼亚读书界和文学界的充分认可,曾获得过罗马尼亚科学院诗歌奖、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诗歌奖、摩尔多瓦作家联合会诗歌奖等无数诗歌奖项,还被译介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俄罗斯、美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她还曾应邀参加过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近几年来,积极介绍中国文化,出版中国诗歌,渴望通过文化和诗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
庙 宇
我居于肉身,就像居于母亲体内。
对我而言,它不是绿洲,
不是庙宇,不是土地,
不是草木,不是脚掌,
不是港口,也不是记忆。
我的肉身不像我,
不像我的父母,
也不像我父母的父母。
但在它异端的脊椎里,
在漆黑中,深渊寒冷,
让一切保持着缓慢的生长:
记忆,血液,水,梦,
任性,父母以及
所有祖辈的睡眠。
我的肉身并非
依照我的相貌和特征造就。
它其实像另一个人,
一个更年轻、更美丽、更热情的人。
谁又能否定
我居于一个完美肉身中的愿望呢?
我的守护神走来,跟随
罗马神祇大军,命令道:“选择吧!”
我站在这道美丽,生动,几乎
像人类一样战栗不止的墙壁前。
可我实在无法,无法做出决定。
神圣的游戏
正义早就遭到瓜分。
我们海豚般弯曲的背上
驮载着沉重的空气,生存的欢喜——
从未被海豚身上的巨人梦见过的
神的可怖的叹息。
从陈旧的、落满灰尘的形式中
我们选择了圆圈。其实,恰恰是圆圈本身
选择了我们,出于唯有它直觉到的原因。
我们奔跑,梦想,就像在一场神圣的
游戏中,没有尽头,由钟乳石口授。
我们奔跑,越来越孤独,我们
漂浮,看上去,更加有力,更加美丽,
远离真理,正义,被无形之手用一块
活岩石雕琢,在贝壳、海藻、石子
或者分布于自然中的庞然大物中间。
惩 罚
我 在手掌上,在雾气腾腾的窗玻璃上画着世界地图
我聚拢起冬天的思想——那些支撑我
生 命的堡垒,反复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当一队队看不见的钟乳石,
喧嚣着,在我的空无中出现。
它们抵达我的心脏,随后我的锁骨,
接着又爬上我的眼睛,直到我看到处处都
插 上长长的声音:红的,黄的,淡紫的,蓝的,灰的……
有人惩罚我,让我看到声音的颜色。
有人逼迫我从气味中建造起宫殿。
还有人命令我时常成为我自己,
倾听一个夏季,一片音响,一朵云,
一 个天使,或神话如何在我的每根肋骨周围生长。
我将通过爱来惩罚那些惩罚了我的人。
犹如多重喊叫发出的音响
仿佛你居住于一只钟下,
钟口朝地。
寻了好半天,你都没有
找见那钟的边沿。
一道雾蒙蒙的光,看上去
恰似药棉,包围着你,
千百年来,不停地瑟瑟作响……
有一刻,既聋又哑,
你跑开,远远的,
跑到那里,你内心的地下室中,
并一步一步,通过一束
生动、徐缓的光,走下。
仿佛你正在穿越一只钟,
钟口朝天。
无人。绝对无人。
一切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
漆黑就像在羊水中。
你品尝着他者的孤独,
那他者即你自己,陌生人。
随后,你描绘你沉默的方式。
你内心某人,惊恐万状,在等候。
他在等候,并看到另一人开始
同时敲响两只钟……他的铁手
在空中,沙沙作响,隆隆轰鸣,
犹如多重喊叫发出的声响。
悲剧梦想者
他第一个犯了错。
他仅用一个思想
雕刻出飘逸的身体
精确得令人气恼,
几乎无人所知,
并愿死心塌地
完完全全地相信
新世界已经开启。
他犯了错,不停地犯着错——
直到,真是让人晕眩,千年时光
将他那无可匹敌的错误
一个字一个字地转化成神话。
可他,即便在那时,也没打住。
他一直享用着
那几乎无人所知的
思想的冰光轮,
独自参加了
并未为他提供庇护的
旧世界的悲剧演出。
他以黑暗当家,当修道院,
在那里导演新世界的演出,
但新世界不明白
你该如何
身处死者和生者中间,
该做什么,如何移动,
坚持多久,坚持到什么地步,
该梦见什么,怎样发疯,
睡多长时间,如何去爱,
才能一刻又一刻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令人信服地死去
而上帝,如此的孤独,
乏味,焦躁,
你可以像他那样选择
没完没了地重新死去
一遍又一遍
在那一思想
总在说谎的身体上,
悲剧,
绝妙的梦想者
传奇般的错误就在那里
完美无瑕地流淌,
在你面前,在他们面前,
朝向未来世纪,
他就走在那世纪的前列,
悄悄地,驼着背,步履蹒跚,
他,第一个罪人
第一个错误者,
骄傲于自己的往昔,
时时刻刻都在死去
在离坟墓三步之遥的地方。
灵魂转生
我爱并坠落。雪下着。我蓦然醒来。
那些雪片让我生出永恒的感觉。
我用莫名的力量备好令人迷醉的
美餐,同魔鬼和新郎一起享用。
雪下着。雪下着。多么悲伤又理想的
盛宴,那是我朝向冬天的敞开,
在天空,平静,却又生硬一如珊瑚,
被寒冷逮住,急切地想要分辨
冬天的等级……它们会在哪里?
在世界的何处?跟随着谁人?
雪下着,就仿佛我将不再存在。
雪缓缓下着,仿佛有人惧怕我。
我坠落并爱。雪片蓦然将我唤醒。
永恒只是记忆,仅此而已。
十二月中
十二月中。寒冷。
太阳就像一块游手好闲的碎片。
雾神将烟书
夹在腋下,
好似在送
一位年轻的死者
最后一程。
邻居院子里,
一位父亲在教儿子
如何放风筝
接着,怎样
打弹弓。
众神纷纷跑开
从白桦,从松柏,
叮叮咚咚地往上爬,就像
守望中的世纪那好战的
蜜中发出的音响。
生与死,就像水母
撞击着陡峭的岸。
没有一丝微风。时间停滞不动。
今天一遍遍重复。同一个今天。
一种预感撕扯着你,将你
同海豚,同那个你即将坠落的
瞬间结为亲戚。
迷 失
我在滑行。我在滑行。我在滑行。
这是歌之夜,也是血之夜。
无人。也无被云蚕食的月亮,
或者树木绿色的影子,
或者房屋大神。
哦,此刻,他在奔走,
沿着瞬间之轴,歌唱,
大笑,哭泣
无人。仅仅一声叹息
为事物笼罩上自我。
而我,滑行时,扭动身子,
仿佛睡眠中在做恶梦。
或者就像某人,从夜的恐惧中
恢复镇定,在飞神的鞭策下,
超越了自我。他通过我大笑,
哭泣,燃烧,叹息和歌唱。
和这首诗中
我在写。我学着安居于墓穴中;
当 我忘记什么是寒冷时——它的疾病就在我身上。
几乎每天——一场地震发生在幽灵中。
我不相信,但还是同我亲爱的伪善的朋友
一起庆祝——并非生命——而是词语!
我们希望相信;在绝望的踪迹里
建造起其他什么:更加深沉,更加彻底。
我们戴上枷锁,形容憔悴,因为同一首诗,
从那里,我们归来,肩上栖息着灰烬星辰。
此地,此刻,惊讶耽搁了我们片刻。
我在写吗?我学着安居于墓穴
和这首诗中:比我稚嫩的手更加真实,
比内心地震更加真实。
我急切地想用我的肋骨
去塑造我亲爱的伪善的朋友……
我 不相信;可我还是同他,我无与伦比的孪生兄弟
一 起庆祝——并非生命,并非爱情,并非诗歌——
而首先是,灰烬。是的。灰烬……
符 号
仿佛当你抓住你的含义时,
你惊恐不已,退隐至内心,
执着者,就像进入一间大地下室,
淹没在当当的钟鸣中。
夜晚匆匆触摸了你一下,
又突然撤退,没有留下
任何符号,或踪迹。
依据你内心某人的理解
当当的钟鸣是
飒飒的振翅声,
夜晚只是某个
途经此处的
更加强大者的房子……
而你只是一个异乡人的
符号,似乎为另一种
生命所熟悉,那里,
你曾是他人的梦。
也许。是的。一个异乡人
在你肉身的墙壁中
时而表达,时而隐藏,
就像蝙蝠,在墓穴中。
狂 热
夜晚。空气炽热,可怖。
火星不久就将升起,在我们面前。
狂热。感觉你正在咀嚼沙粒。
启示录片段遭到碾压,在呓语中
在睫毛下,像桃核——在牙齿间。
睡意昏沉,天使们对灵魂
施起火刑。神在打盹。
空寂。天空小如音节。
荒芜,甚至不止于此。
极度罕见:某人送来
一阵风,犹如莫名者
萌生死亡的叹息。
一切搅合在一起,掀起
漩涡,远离善,远离恶。
难以呼吸的空气。生活在此
仿佛经历死亡。逃离。隐藏。
你的世界呢,上帝?一片切断
你呼吸的丛林。甚至不止于此。
恐惧降临
夜晚降临
清晨降临
你的目光缓缓提起
拧在地平线上的沉重的橡树。
它们生长。开始成熟。
它们壮大,注视着光的孩童
模仿那被最亲近的人
放逐的先知的步伐,
朝你走来的样子。
恐惧降临。
黑夜降临——
我的姐妹在炽热的血中流淌。
为时太晚了,生命降临,
我时刻朝它前行,主啊,
遥远的植物,那么生动的地峡
——虽然你牵着我的手——我却从未抵达。
我们面对面站着:精神对精神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