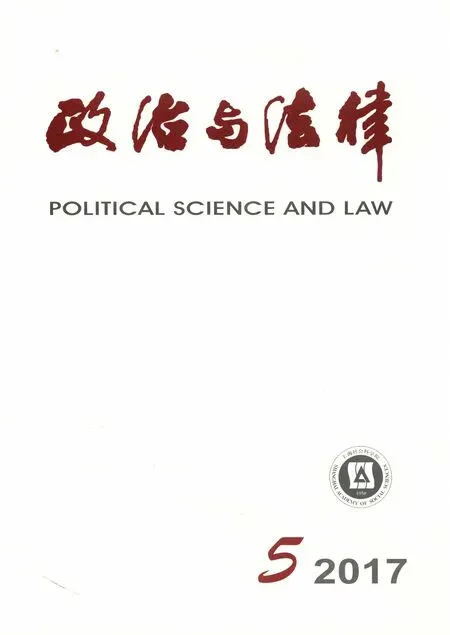论配偶刑法上的作为义务
冯 军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论配偶刑法上的作为义务
冯 军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在重要的法益遭受危险时,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信赖关系,配偶之间才产生互相保护和救助的特别作为义务;配偶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并不是无限制的,生活的通常情形和配偶的自我决定都应该成为排除配偶另一方作为义务的正当事由。我国的司法实务在解决配偶的作为义务这一问题上,大多过于形式地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存在配偶关系,就负有作为义务;也有少数刑事判决实质性地考虑到必须限制配偶作为义务的范围,对这种实务做法更需要刑法学界予以充分关注并给予理论支持。
配偶; 作为义务; 不作为犯罪;犯罪阻却事由
我国司法实务在解决配偶刑法上的作为义务这一问题上,往往是过于形式地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存在配偶关系,就负有作为义务,这种在配偶关系内对不作为犯罪成立范围的扩大化理解和适用并不符合现代刑法的理念,需要探讨配偶之间作为义务的范围,以及阻却犯罪的事由,以改善目前此类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并推进这个问题的规范化发展。
一、配偶作为义务的根据
要解决配偶间作为义务不履行的刑事责任,首先必须澄清的是“配偶”在刑事法上的含义。虽然我国宪法仅仅使用了“夫妻”一词,我国《宪法》第49条第2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我国民法没有使用“夫妻”一词,而是仅仅使用了“配偶”一词,规定了“配偶”特殊情况下的监护人地位,及作为配偶失踪后财产的第一顺位代管人地位。同样,我国《刑法》第258条使用的也是“配偶”一词,没有使用“夫妻”一词。我国《婚姻法》多处使用了“夫妻”一词,但是,有四处例外地使用了“配偶”一词:我国《婚姻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32条第3款第1项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规定为调解无效时应准予离婚的情形之一;第33条对“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的情形作了特别规定;第46条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规定为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之一。因为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所以,我国《婚姻法》中的“配偶”一词,有时也指夫妻中的一方。然而,民法中的“配偶”一词,很可能也包括虽不具有婚姻关系却正在共同生活的类似夫妻者,否则,就在特定情形中难以妥当解决正在共同生活的类似夫妻者的监护人和财产代管人的问题。关于刑法中的“配偶”一词,学界的通常学说认为,它“既包括经过合法的登记结婚而形成的夫妻关系,也包括事实上形成的夫妻关系”中的一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27页。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中的“配偶”,既包括夫妻中的一方,也包括事实上共同生活的伴侣中的一方。本文在狭义上使用“伴侣”一词,即指虽然不具有法定的夫妻关系却事实上以夫妻相互对待的共同生活者。无论是夫妻中的一方,还是伴侣中的一方,都会涉及刑法中成立不作为犯的条件之一的作为义务问题。
(一)夫妻的作为义务
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婚姻”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虽然夫妻双方并不像未成年的子女依赖父母一样依赖对方,但是,夫妻都自愿地进入了一个婚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内容之一就是进行互相的保护和照料。夫妻中的一方都有权利相信在自己处于紧急状态时对方会给自己提供保护,而不需要进行反复的约定和考验。
婚姻是一种法律制度,婚姻的有效缔结就产生了特别义务,从婚姻这种法律制度中产生了各种一般人并不负有的而夫妻必须负有的法律义务。例如,在夫妻之间存在互相扶助的义务、在配偶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死亡危险时进行抢救的义务,不履行这些义务,在刑法上就可能成立遗弃罪或者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从婚姻中能够产生成立不作为犯所要求的特别作为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夫妻才具有的作为义务,正是婚姻这种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之一,换言之,作为法律制度的婚姻制度本身正是产生夫妻作为义务的根据。
夫妻之间的保证人地位的保护方向只涉及对另一方法益的保护,而不包括对另一方行为的监管。在夫妻中的一方知道另一方的犯罪计划时,没有阻止另一方实施其犯罪计划的义务。在婚姻共同体中,不存在监视婚姻伙伴的生活决定的义务。“婚姻的保护范围或者控制范围也扩展不到阻止伴侣的犯罪行为上去。婚姻配偶的控制是为相互保护服务的,而不是为保护公众服务的。这个婚姻伴侣对于另一个来说是一个帮助人,但不是他的监护人。”*[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主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547页。
当婚姻已经破裂,导致夫妻分居生活时,就不再存在夫妻之间的互相保护义务。因为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并不能给保证人地位提供充分的基础。然而,只要夫妻还共同生活在一起,婚姻的“破裂”也不能消除保护义务,因为依然经营着的共同生活本身就意味着不能在紧急状况中置对方于不顾。
(二)伴侣的作为义务
在虽不具有法定的夫妻关系却事实上以夫妻相互对待的生活伴侣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由婚姻所缔结的生活共同体,由于伴侣关系是完全私人性的,缺乏法律的认可,所以,就不存在与婚姻同样的规范效力。但是,伴侣在事实上经营着男女双方的共同生活,正是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伴侣之间往往会更信任对方,自觉地在彼此之间承担保护功能。因此,虽然不存在源自婚姻的作为义务,但是,存在基于相互信赖的自愿承担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缺乏官方机构出具的结婚证,不能改变双方隶属于对方保护范围之内的事实。”*同上注,罗克辛书,第548页。
与一种真正的生活伴侣关系不同,一种恋爱关系或者订亲后被承认的亲戚关系并不能确立一种保证人地位。因为在恋爱关系或者因订亲所成立的亲戚关系中,仅仅包含着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承诺,还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共同生活本身,它们都是双方可以自由取消的。但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似乎认为恋爱关系或者因订亲所成立的亲戚关系也能产生作为义务。例如,在李家波一案中,李家波与同厂女工项兰临相恋并致其怀孕后,李家波向项兰临提出分手并要求其去流产,项兰临不同意并几次欲跳楼自杀。在一次争吵后,项兰临在李家波住房外的走廊上服敌敌畏农药自杀身亡。法院认为,李家波与项兰临相恋并致其怀孕,在未采取措施加以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即提出与项兰临分手,并在争吵中扔打火机刺激项兰临,致使项兰临坚定服毒自杀的决心,当李家波发现项兰临已服农药后,非但未施救,反而持放任态度关上房门离开,且李家波对项兰临及其腹中胎儿负有特定的义务,而不予救助,致使项兰临在李家波单身宿舍这种特定环境下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服毒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家波有期徒刑五年。*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金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这一判决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从恋爱关系中并不能产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因为恋爱关系并不能建立一种牢固的信赖关系,无法确立一种保证人地位;另一方面,从恋爱怀孕后因未妥善处理而发生争吵这一行为中也不能产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因为这种争吵完全属于下述“生活的通常情形”。因此,恋爱怀孕后因未妥善处理而发生争吵本身不足以产生成立不作为犯所要求的作为义务,即使引起了一方的自杀,也不能追究另一方的刑事责任。*如果项兰临的怀孕已近临产,胎儿当时处于离开母体也能在正常情形下独立存活的状态,那么,李家波也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而具有抢救胎儿的作为义务,就可能因为不作为而构成对胎儿的故意杀人罪。当然,这已经不是配偶之间而是父子之间的作为义务问题了。
总而言之,在重要的法益面临危险时,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信赖关系,配偶之间才能产生互相保护和救助的作为义务。
二、配偶作为义务的排除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认为配偶之间负有作为义务,但是,没有很好地探讨配偶作为义务的限制或者排除问题,以致司法机关大都无限制地追究了配偶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配偶的作为义务并不是无限制的,“生活的通常情形”和“配偶的自我决定”都应该成为排除配偶另一方的作为义务的正当事由。
(一)生活的通常情形
在配偶的共同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不愉快的情形,如果配偶中的一方由此而自杀自残,倘若是理智健全的成年人的话,只能自我答责。这种成年人的自我决定应该排除其配偶的作为义务,即使其配偶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也不应该就其财产损失、伤害甚至死亡承担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
现有如以下案例:2000年4月25日,天津市西青区某村26岁的王男某与妻子王女某因家务事吵了起来,被邻居拉开后,两人又边吵边来到南河镇大南河村西污水河旁。一气之下的王女某跳进了污水河里,污水深约1米。站在一旁的王男某见状也跳进河中劝说,王女某不听,王男某随即独自回到岸上扬长而去。随后,王男某先到亲戚家,讲了妻子跳河的事,又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当公安民警和他的亲戚赶到时,时间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王女某已经死亡。天津市西青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男某与王女某是夫妻关系,负有特定义务,王女某在河中,被告人王男某明知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却自行离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放任结果发生,其行为已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鉴于其犯罪后有自首情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男某有期徒刑六年。*参见刘荣庆、陈彦、孙永根:《吵架了,就可以不管妻子吗?》,《检察日报》2002年4月30日,第7 版。
在上述天津市西青区法院判决的这个案件中,除了是否能够论证被告人王男某存在杀人故意这一问题外,*因为“水深约1米”,为了死亡,需要“王女某还把头探进水中,” 以致于在现场的王男某当时有理由认为这种浅水河最终不会导致一个成年妇女被淹死。王男某是否具有不履行就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也是问题的关键。天津市西青区法院没有同时从王男某的先行行为中,即没有同时从王男某与妻子王女某因家务而发生吵架的事实中推导出王男某负有应该在王女某自杀时有效地救助王女某的作为义务,*是因为家里丢了一只会下蛋的母鸡而在争吵中王男某责怪王女某不会管家以致于王女某去自杀,还是因为王男某发现家里存有三万元的存折找不到了而在争吵中诬蔑王女某把钱给了王女某其实没有的情夫以致于王女某去自杀,对特别作为义务的产生,应该会有不同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至少目前中国的实情是:一个村妇不会因为“家里丢了一只会下蛋的母鸡而在争吵中被丈夫责怪不会管家”就气愤得失去理智地决定自杀,如果她竟然作出了这种决定,那么,就应该把她的这一决定作为冷静的理智决定来尊重;一个村妇因为“丈夫发现家里存有三万元的存折找不到了而在争吵中被丈夫诬蔑为把钱给了她其实没有的情夫”,往往会因此而失去理智地要自杀,如果她去自杀,那么,就应该把她的这一行动视为不冷静的、非理智的举动,必须予以救助,就像当“一个看家的10岁女孩在家里丢了一只会下蛋的母鸡而被母亲责怪不会看家而气愤得去跳河自杀”时必须救助该女孩一样。而是直接从“王男某与王女某是夫妻关系”中推导出王男某负有防止王女某的特定作为义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男某有期徒刑六年。
尽管天津市西青区法院以我国刑法理论目前的通常学说为依据,从“王男某与王女某是夫妻关系”中推导出王男某负有防止王女某死亡的特定作为义务,但是,基于配偶的自我决定原则,从“夫妻关系”中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夫妻一方负有防止对方自杀死亡的特定作为义务。问题是,在这一案件中,能否从王男某与妻子王女某因家务而发生吵架的先行行为中推导出王男某负有应该在王女某自杀时有效地救助王女某的作为义务。对此,我们应该作出否定的回答,从先行行为的角度来看,王男某并不负有应该在王女某自杀时有效地救助王女某的特定作为义务。*许成磊:《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从生活的通常情形中,并不能产生刑法上的特定作为义务,即使通常的生活情形中包含着错误,因为生活的通常情形理所当然地具有错误的成分。所以,“错误行为或者轻微不法行为(如一般辱骂)引起他人自杀的,也不成立犯罪”。*同前注①,张明楷书。
(二)配偶的自我决定
配偶一方的作为义务是通过配偶另一方独立自主的范围进行限制的。配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独自对他们私人的各种事务负责。在这个范围内,就没有保护义务被接管,并且不能形成保证人地位。
首先,配偶的一方没有义务通过能够直接防止结果发生的强制行动去阻止另一方的自我损害行为。
例如,妻子仅仅因为无聊难过,就以自杀相威胁,逼迫丈夫留在家中陪伴。即使丈夫知道妻子真的会自杀,并且因为丈夫没有留在家中而导致了妻子的自杀,丈夫也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妻子无权用这种不符合法规范的方式剥夺丈夫的行动自由。当然,如果配偶一方的自杀是一种排除了意思自治的心理疾病的表现,例如,妻子因为患有强迫症而在丈夫离开一天后就会割腕自杀,配偶另一方就仍然负有保护义务,因为对处于疾病中的一方进行保护正是配偶之间法定的义务。
在有效地缔结了婚姻之后,配偶是否还具有意思自治呢?由婚姻的缔结所产生的特别义务是否能够与婚姻伙伴的自由意志相对抗?这个问题在刑法学上具体表现为,如果配偶的一方在没有任何外在阻碍的情形下决定实施自我损害行为,配偶的另一方是否具有特别义务阻止这种自我损害行为的实施。例如,一个警察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他身边的妻子就有义务抢救受伤后失去知觉的丈夫,如果妻子有能力抢救却故意不予抢救而导致丈夫死亡的,妻子就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但是,如果该警察在周末开车与情人去海边游泳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情人面部严重烧伤,他因此不想继续活下去,回家把事情告诉了妻子之后,拿出手枪准备自杀,妻子能够阻止丈夫自杀,却不希望丈夫继续活下去,甚至宁愿丈夫立即死亡,因此,她没有夺下丈夫手中的枪以阻止丈夫自杀,以致丈夫自杀身亡,这个警察的妻子是否也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呢?
欲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追问婚姻这种制度到底具有怎样的形态。婚姻是以共同塑造生活为目标的,夫妻在塑造共同的生活时拥有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在缔结婚姻之后,夫妻双方都像在缔结婚姻之前和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一样,具有其独立的自由人格,只要夫妻的一方没有丧失自我决定的能力,处于一种能够自我答责的状态,夫妻的另一方就仅仅有义务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即夫妻双方都只有义务向对方提供第三人有义务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夫妻一方丧失自我决定的能力,处于一种不能自我答责的状态,另一方才具有提供比第三人有义务提供的帮助更多的帮助之特别义务。强制地阻止有答责能力的配偶实施故意的自我损害之保证人义务是不存在的,就像不存在阻止有答责能力的配偶实施犯罪之保证人义务一样。*Vgl. 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 Auflage, S. 822 f.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配偶行使强制力,都不是由婚姻制度所确立的法律义务,因为婚姻的缔造和存续是以尊重具有答责能力的配偶的意志为前提,而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配偶的意志在客观上是值得尊重的现实意志,否则,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配偶的意志就容易被另一配偶主观的任意所干预和侵犯。对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人的意志进行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这个人本身。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人自己更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活。这同时意味着,如果一个具有答责能力的人作出了决定,只要这种决定并未受到外部的强制,就必须由该人自己负责,无须配偶为这个具有答责能力的人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其次,通过劝说或者提醒促使另一有答责能力的配偶产生确信,从而阻止其实施故意的自我损害或者实施犯罪之义务,也是不存在的。
劝说、提醒和确信都属于共同生活的缔造过程,而这种缔造过程的不可强制性正属于配偶共同生活的形态。如果配偶的一方基于爱而通过劝说、提醒来促使另一配偶放弃实施故意的自我损害或者放弃实施犯罪,那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只是把爱和婚姻或者类似婚姻的构造捆绑在一起,仅仅是一种稀有的东西,而不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一个人有权利拒绝缔结没有爱的婚姻或者让这种婚姻不再存续,当然也有权利缔结没有爱的婚姻并且努力维持这种婚姻,这种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障。在人们还没有实现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之前,就不能把基于爱的行动转化为源于婚姻制度的法律义务。
再次,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果配偶的自我损害行动源于一种心理的重大不幸(认识错误、意志消沉等等),那么,配偶的另一方是否负有阻止这种自我损害行动的特别义务呢?雅科布斯(Jakobs)认为,在这种情形中,只要能够通过阻止自我损害行动来消除这种心理的不幸,配偶就作为保证人而负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粮贩用他全部的财力在收割前购买了谷物,有人开玩笑地说他预先收购的所有谷物都被冰雹打坏了,他相信了这个说法,并且想自杀,如果他的妻子看清了这个认识错误,她就必须向他澄清,在必要时也必须阻止自杀结果的发生。*Vgl. a.a.O., S. 823.
然而,笔者看来,对处理这种心理不幸的事例而言,在进行客观归责时,不仅要考虑导致实施自我损害行动的心理不幸是否重大,而且,要考虑谁应该负责消除这种心理不幸。纯粹的心理不幸,无论是微小的,还是重大的,都应该由具有这种不幸心理但是仍然是理智的人自己负责消除。只有在配偶一方的心理不幸并非基于其自由意志而已经成为使其丧失答责能力的心理疾病时,配偶的另一方才负有特别义务帮助配偶一方消除由这种心理不幸所可能造成的自我损害。例如,冯某用他全部的积蓄在德国购买了十箱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德文刑法专业书籍,通过邮局海运回国,冯某在中关村邮局工作的朋友知道他十分珍爱这批书籍,却开玩笑地打电话对冯某说十箱书已经全都被海水泡烂了。 冯某把这个玩笑当真了,于是,觉得他的生命太无意义,绝望得想服毒自杀。如果冯某的妻子早就看清了冯某的这个认识错误,却不向冯某澄清,也没有在必要时阻止冯某服毒自杀,那么,冯某妻子的行为连是否成立见危不救都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意思自由者的自我损害行为所造成的希望状态或者至少是愿意忍受状态,恐怕很难说是紧急危难,除非在这种自我损害行为所造成的状态中明确地表现出自我损害者的意思改变(咬着牙割自己的手碗,就不能说改变了自杀的意思,尽管脸上显得异常痛苦)、明确地希望排除自我损害的状态。更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即使冯某的妻子希望冯某早死,因此,既未向冯某澄清真相,也没有在冯某服毒自杀时夺下冯某手中的毒药,她也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她没有参与开这个玩笑,也就没有义务通过澄清真相来防止冯某由于重大的心理不幸而自杀。*如果冯某的朋友在电话中说发现仅有一本书被泡烂了,那么,冯某产生的自杀心理就已经很难说是一种“重大的心理不幸”。对那个玩笑进行正确的处理,完全是冯某自己的事情,没有进行正确的处理,是冯某自己的错误。对于冯某的死亡,应该由冯某自己承担责任。不能因为冯某已经死亡,实际上不能承担责任,就把冯某死亡的责任转嫁到冯某妻子的身上,尽管冯某妻子的行为对冯某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和主观意愿。*人们也可以这样论证:在这个例子中,冯某负有不侵害自己的消极义务,冯某的妻子负有救助冯某的积极义务,由于在刑法中消极义务优越于积极义务(因为不作为犯要比照作为犯从轻处罚),所以,冯某要优先于冯某的妻子对冯某的死亡负责。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没有说服力,因为一个人不履行义务并非另一个人不履行义务的理由,按照这种论证,仅仅应该对冯某的妻子从轻处罚。
然而,如果是另一种情形,就要作出不同的解答。冯某非常疼爱他十三岁的女儿,一个星期六的深夜里,冯某突然接到妻子的女友马某打来的电话称其女儿食物中毒,有生命危险,正在抢救。听到这个电话后,冯某感到极为不幸,认为如果女儿死了,自己也没有必要活着,于是,他急忙起床,尽管他知道自己可能摔死在山沟里,还是冒着大雨赶往医院,结果在途中从山坡上滑倒,掉进山沟里,被洪水淹死了。而真相是:马某与冯某的妻子在夜里聊天,得知冯某疼爱他十三岁的女儿胜过疼爱他自己,马某不相信,于是,冯某的妻子对马某说:“不信你打电话试试看,他肯定会为他的女儿做一切的!”马某想:“如果跛腿的冯某在这个暴风雨之夜能够赶去看望他的女儿,就证明冯某真是不顾一切地疼爱他的女儿。”冯某的妻子同意用这种方式来考验冯某,尽管冯某的妻子当时认识到冯某可能摔死在山沟里,却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因此,没有在冯某出门之前,再次打电话告诉冯某真相。在这个例子中,冯某的妻子很可能要对冯某的死亡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因为冯某的心理不幸和行动都是由于存在(被捏造的)客观原因而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马某所开的玩笑是一种在客观上并非完全被允许开的玩笑,冯某的妻子与马某共同组织了这个直接导致冯某行动的玩笑,并且,冯妻具有因为婚姻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然而,仅仅因为编造了一种在客观上并非完全被允许开的玩笑(例如,马某给冯某打的那个电话),或者仅仅因为存在婚姻关系(例如,冯某的妻子也是在冯某接电话时才知道那个玩笑,但是,认识到并且希望冯某的死亡),都不足以产生特别的作为义务。在这种结果的产生也是出于被害人重大心理不幸的事例中,行为人(例如,冯某的妻子)实施的在客观上不能完全被允许的先行行为(例如,组织了在客观上不被完全允许开的玩笑)并未对被害人产生的重大心理不幸发挥优势的支配作用,被害人更谨慎地处理的话,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心理不幸和不采取后续行动,因此,如果要行为人对被害人基于重大心理不幸的行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负责,就需要用行为人在制度(例如,婚姻)上承担的作为义务来补强他并未发挥优势的支配作用的先行行为所具有的效果,也就是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在客观上并非完全被允许的先行行为与婚姻制度结合在一起,才产生了刑法上的特别作为义务,但是,当客观上并非完全被允许的先行行为与婚姻等制度相分离时,都不能产生刑法上的特别作为义务。
最后,即使配偶的一方在其理智清醒时实施自我损害行动之后丧失了对死亡过程的控制,配偶的另一方也不负有特别的作为义务。例如,一位丈夫只有在看足球比赛时才不停地大量饮酒,一旦比赛中没有射进他认为应该射进的球,他都气得倒在地板上,过一会儿就拿刀割自己的手碗,他的妻子看到他的这种行动,每次都劝阻救治。丈夫有一次在看足球比赛时喝醉了酒,他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在看到丈夫倒在地板上之后,妻子拿着手提包去看电影,出门前说了一句:“你要死就去死吧!”丈夫后因割破手腕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对此,妻子要对丈夫的死亡承担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责任吗?丈夫有权利用自己头脑清醒时作出的喝酒决定所造成的自己完全预见到的不可避免的无责任能力状态来限制甚至剥夺妻子的行动自由吗?笔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丈夫这种醉酒后的状态不过是其头脑清醒时作出的决定之延续,不具有独立的规范含义,否则,这样一种保证人义务并非法定,并且和婚姻制度是不相融合的。
在以保障自由为己任的法规范中,被害人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并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理由。自杀是自杀者对自身生命的自由支配和处分,不应当认为他人有义务对之加以阻止。因为作为义务的目的与意义在于防止对被害人的法益侵害,而不是在被害人不愿意接受保护时干涉其意志自由。尤其是不能将保护义务转化为对被保护者的约束和管制。因此,认为被害人的自主决定限制了作为义务的成立范围才是正确的立场。*参见王钢:《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评价》,《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三、中国的司法实务现状及应然的转向
(一)形式思考后得出有罪结论的判例
在大部分案件中,我国法院仅仅基于形式上的思考,认为只要存在配偶关系,就具有作为义务,不予救助的一方就成立不作为犯罪。尤其是对夫妻之间因为琐事吵闹, 一方自杀, 另一方见死不救, 结果导致自杀者身亡等类似案件, 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日渐增多。*参见黎宏:《“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前注⑨,许成磊书,第343页以下。下面以典型的“孙多琴故意杀人案”为例来说明。
2008年5月31日中午1时许,被告人孙多琴要去农五师83团看望儿子刘元和孙子,其丈夫(被害人)陆九斤(刘元的继父)不同意,二人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被告人孙多琴拿出“小黑子”鼠必死药液准备喝,被陆九斤夺去自己喝掉。陆九斤喝完后出现中毒反应,被告人孙多琴未予救助,陆九斤中毒死亡。之后,被告人孙多琴将陆九斤的尸体拖到自己家院门口垃圾坑内焚烧掩埋后逃往其儿子刘元处,并向儿子刘元说明了情况。2008年6月2日,被告人孙多琴在其儿子刘元的陪同下到芳草湖垦区公安局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经法医鉴定,被告人孙多琴行为当时出现应急相关障碍的精神病理症状,为限制责任能力人。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多琴因家庭纠纷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准备服老鼠药自杀时由被害人夺去自己喝掉,其购买鼠药后的自杀行为引发被害人服毒,在被害人出现中毒症状时,被告人未予救助,没有履行其先行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作为夫妻,被告人亦有救助义务,但其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对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态度。在被害人死亡后,被告人又焚尸。故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孙多琴有期徒刑四年。*参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芳草湖垦区人民法院(2008)芳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
这是一个混杂了很多问题的判决。法院认为存在孙多琴应履行的从先行行为中产生的救助义务,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孙多琴购买了鼠药,但是,她并不是为了杀人而购买鼠药的,孙多琴只不过是在发生争执后拿出鼠必死药液准备自己喝,虽然鼠必死药液也是具有危险的东西,但是,不属于能够产生作为义务的制造危险源,因为如果不是陆九斤自己夺去喝掉,孙多琴拿出的鼠必死药液就不会对陆九斤产生任何危险;法院认为作为夫妻,孙多琴也有救助义务,就是没有考虑到陆九斤的自我答责行为已经排除了孙多琴的责任,“我没有故意杀人,而是陆九斤自己喝的药”,孙多琴自称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孙多琴的辩护人认为,由于陆九斤喝的老鼠药中检出毒鼠强成分,该药毒性剧烈,加上孙多琴患有精神病,客观上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施救助行为,因此,孙多琴没有救助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是有道理的辩护意见,如果孙多琴即使实施了救助行为,陆九斤也必然死亡,就当然要否定孙多琴的不救助行为与陆九斤的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将在被害人死亡后,被告人又焚尸的行为,认定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因素之一,是明显没有道理的,焚尸行为或者只能是已经成立故意杀人罪情形下的量刑情节,或者只能是不成立故意杀人罪情形下的侮辱尸体行为。
法院的上述做法与我国刑法学界的通常看法是一致的。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妻子自杀时,丈夫是否具有救助义务?倘若认为自杀行为属于行使自主决定权,当然会否认丈夫具有救助义务。但本书持肯定回答。诚然,自杀是妻子自己决定的,在此意义上说,妻子应当自我答责。但是,刑法对生命实行绝对的保护,妻子的自我答责只是意味着妻子对自己的自杀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免除了丈夫的救助义务。”*张明楷:《刑法学(上)》(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刑法对生命实行绝对的保护,也必须证明这种对生命的绝对保护应当由丈夫来实现。一方面说“妻子应当自我答责”,另一方面又说“并不意味着免除了丈夫的救助义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因为自我答责的本来意义就是免除他人的义务和责任。

(二)实质思考后得出无罪结论的判例
在某些比较特殊的具有自杀性质的案件中,法院进行了实质的思考,认为即使存在配偶关系,也存在排除作为义务的情形,行为人的不予救助行为不成立犯罪。在李银建被控故意杀人却被宣告无罪一案中,法院很显然地表明了这种倾向。
2002年7月17日,被告人李银建与其妻肖世花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后,肖世花去李银建父母家吵闹,经村干部劝解,肖世花仍提出离婚,即与被告人李银建去孙家乡政府办理离婚手续,因小孩抚养问题未协商好,离婚未果。当天下午6时许,二人回家路过油坊村一组山湾堰塘时,肖世花要李银建一块歇息,李银建不予理睬,二人发生抓扯,被当地村民何裕坤劝开。当被告人李银建朝回家的方向行走50余米时,肖世花跳入水塘中,何裕坤见状大声呼喊李银建救人,李银建回答:“她自己跳的水,我又没有推她。”又继续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后肖世花被何裕坤和闻讯赶来的周书坪等人救起时已死亡。
二审判决认为,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生活经验,二人之间的抓扯行为通常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自杀情况的发生,被告人也不能预见或者认识到其妻会跳水自杀,可见被告人和肖世花的抓扯行为与肖世花的自杀结果之间不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刑法意义上合乎规律地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如果说肖世花的生命健康权利处于危险状态的话,则引起这一危险状态的先前行为是肖世花自己跳水的行为,而不是李银建与其发生抓扯的行为所必然引起的,更不是李银建继续往回家的方向走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原审被告人李银建与其妻肖世花之间在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情,不足以成为导致肖世花自杀的具有现实危险性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境下,在肖世花跳水自杀的现场已有群众及时地实施了救助行为,但是仍然没能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告人即使从50米以外的地点赶到现场施救,死亡结果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可见该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并无刑法意义上合乎规律地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李银建不可能预见其妻会自杀;当其妻跳水自杀时,其心理状态是:“她自己跳的水,我又没有推她。”可见李银建对其妻自杀的行为不仅没有预见,而且基于其认识水平,李银建也不可能明知其具有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义务。据此,法院认为,李银建对其妻肖世花的自杀行为不存在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其没有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与肖世花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亦不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罪的主观要件,据此,宣告被告人李银建无罪。*参见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02)万刑初字第606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渝二中刑一抗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这种无罪判决虽然在目前是少数,但是应该予以重视且应成为引导的方向。
(责任编辑:杜小丽)
冯军,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2JJD820002)的阶段性成果。
DF611
A
1005-9512-(2017)05-00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