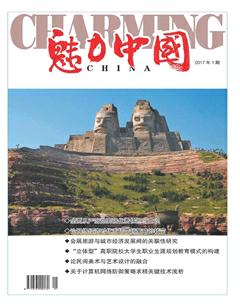浅析《生死场》中金枝的悲剧命运
邓增弟
摘要:萧红的《生死场》通过对王婆、金枝、月英等生存悲剧的抒写展现女性的悲剧人生,表达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本文以金枝为视角,试图透过金枝的宿命轮回从爱情、婚姻、生育和生存等方面分析金枝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萧红 《生死场》 金枝 女性悲剧
《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动物般“生”与“死”以及在日本入侵后初步觉醒的故事。在《生死场》中作者萧红描述了一些女人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活和死亡。金枝就是典型的一位。本文创新性地以金枝的宿命轮回为线索,从金枝的爱情、婚姻、生育、生存等方面展现其悲剧命运:
一、 活在娘家,爱情幻灭
十七岁的金枝在娘家和母亲忙农活,在和成业的缠绵中她初次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但金枝的爱情不是正常的爱恋,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人的本能支使发生的爱情。
“金枝听着金鞭响,听着口哨响,她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的走出菜圃。”哨声是爱情的呼唤,金枝期盼这样的哨声,也在害怕这样的哨声,她惊惊怕怕地去回应。这样的哨声不是金枝能控制的,她没有这样的主导权,换言之在和成业的爱情中,金枝是不平等的,她只能盼望和等待,每次“口笛不住的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她乖巧顺从迫不及待地回应口笛的呼唤。而这样的回应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金枝不同于农村任人摆布婚姻的女人,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恋爱。因此在结婚前她不得不独自忍受着来自身边妇女的流言蜚语,“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然而这样的议论只是针对金枝,从不会指向发起性行为、主导着这场爱情的成业,影响的是金枝的声誉和未来的幸福,对成业的一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在《生死场》中,金枝和成业的爱情都是以性叙事呈现的,“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成业就像一个侵略者在金枝身上得到了灵魂和肉体的满足,吹着哨声他“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的,他丝毫没有感受到流言蜚语给金枝带来的痛苦,也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挺着的肚子带给金枝的害怕。即使金枝已经害怕得像病了似的,他仍然“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墙上”,一个男人如此不体贴乃至可以说是粗暴,他和金枝的关系根本谈不上是爱情,只是人的本能驱使他在金枝身上得到性满足罢了,金枝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使自己快乐的工具。日益挺起的肚子,昭示着这场非正常爱情的破灭,最终金枝“收拾”好所有爱情的幻想走进了这个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坟墓。
二、 嫁到夫家,幸福落空
金枝的肚子不是病,尘埃落定,得知此事的母亲好像本身有了罪恶,“立刻麻木着,很长的时间她好像不存在一样”,金枝的行为让母亲感到很羞耻,“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完了,于是也只能很温柔地让女儿嫁到成业家。母亲知道,顶着肚子嫁到夫家的女儿苦命的日子要来了。从娘家到夫家,金枝开始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
单凭性爱建立起来的家庭根本无法彼此扶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更不要说成为对方的精神支柱。金枝和成业建立起来的家庭没有超越性的沟通和交流,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下,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物质生活。当为了生活疲惫得早出晚归时,成业留给金枝的是责备和骂声。金枝即将临产,仍然洗衣、做饭,从早忙到晚,晚上还要随时满足成业的性欲,还因此险些难产而死。于是金枝“出嫁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从呼应哨声到出嫁的短短几个月,金枝寄托在成业身上的包括爱情的幻想和婚姻的期待都已破灭和落空。更可怕的是,因为繁重的生活压力成业竟摔死了小金枝,生命就这样被无情地践踏,“在农村,菜棵甚至是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如此冷血,金枝固然没有幸福可言。
由此可见,在夫家的金枝并不能感受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是感受不到做人的尊严,卑微得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保障不了。金枝已经落入这片“生死场”和其他一切动物和人忙着生,忙着死。
三、 走向城市,遭到凌辱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和十年前一样”,日本的旗子在山岗上飘扬。金枝成为了年轻的寡妇,她选择了从农村走向城市,她到城市去是对城市文明化想象的结果,她认为在哈尔滨能够逃避家乡“年轻女人都被抓起来”的危险。在乡村苦难中,城市总是首先被作为获得拯救的地方。
“金枝在夜的哈尔滨城,睡在一条小街阴沟上”,她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金枝通过一些简单的缝补工作在幻化的哈尔滨城中站稳了脚步。但是进入了城市这一大染缸就不可能干干净净地走出去,“她无助地撕狂着,圆眼睛望一望锁住的门不能自开,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发生”,被诱奸的金枝痛苦着,羞恨摧毁着她,这羞恨又把她赶回来了乡村。
走向城市,是金枝放下爱情婚姻走向独立生存的开始,这一举动反映了她主体意识从无到有。然而城市的票子并没有给金枝带来生活的新希望,相反在城市受到的凌辱最终让金枝选择了回到满目疮痍的乡村。至此,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于金枝而言,都是悲剧发生的场所。
四、 重归乡村,何去何从
急急切切地回去乡村是因为有母亲的安慰,被凌辱的羞恨通过骨髓麻寒着金枝的皮膚,金枝希望马上躺到母亲身上哭。可是,回到家里“母亲拿着金枝的一元票子,她的牙齿在嘴里埋没不住,完全外露,一面细看票子的花纹,一面快乐有点不能自制地说:‘来家住一夜就走吧!”最后一道防线都破灭了,母亲的冷漠彻底寒了金枝的心。最终金枝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此我什么都不恨。”
重归乡村,金枝感受到来自亲情的冷漠,充斥他们灵魂的永远是物质,乡村人永远体验不到灵魂。自我觉醒的金枝在饱受种种苦难和蹂躏后,选择走向另外一个归处——尼姑庵,希望通过信仰、宗教去实现自我的救赎和解脱。然而现实残酷到“她想出家庙庵早就空了”,最终的藏身之所也不可得,悲痛绝望的金枝又该何去何从。
小说没有交代金枝的归处,但悲剧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纵览金枝的经历,从娘家到夫家,从乡村到城市到最终回归乡村,她始终在 “生死场”进行着宿命式的生命悲剧的轮回。尽管她有反抗,有自我觉醒,但在各种压迫下还是难以逃脱属于她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萧红著.生死场[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陶娥.论《生死场》的悲剧意识[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05)
[3]张丽军,姜现甲.何处是归程——《生死场》 金枝的女性生命救赎意识解读[J].德州学院学报.2009年2月第25卷(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