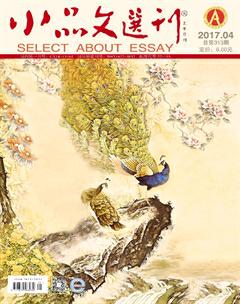淘书往事
傅月庵
旧书摊,卖旧书的摊子。在台湾,有时也当专有名词用,特指1970年代之前,台北牯岭街的旧书铺子。所以称“摊”而不称“店”,原因是店家摆设几乎霸占了整个人行道,往前延伸到车道之上了。逢到假日人多,几乎仅能以“水泄不通”四字形容之。
余生也晚,等到我对旧书大感兴趣,成日浸淫其中时,牯岭街早因拓宽街道而摊商四散,几乎都被迁置到光华商场去了。有一说法,牯岭街昔时为总督府高级文官宿舍区,国府迁台之后,党国大老纷纷入住。旧书摊影响交通,妨碍大老进出,遂有拓宽之举。这是台面下的政治运作,是耶非耶,恐难证实了。但我也并非没到过牯岭街。国中二年级某次周六,上完半天课,下午一名读建中的同学哥哥领着我们几个几乎不曾单独跨过淡水河的小鬼搭上14号公车“朝圣”去了。说朝圣一点没错,原因是口袋里不过10几元,吃过中饭加根冰棒,去掉大半,真只能面圣朝拜,看的比买的多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牯岭街原貌,东挑西拣,抓了一本《黄克强先生传记》。感想一:“书真多,真便宜!”感想二:“赶快回家,明天考数学,都还没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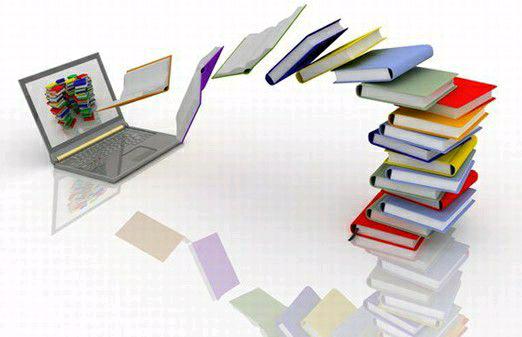
谁知一年后考入台北工专,一头栽进光华商场去了。商场书商虽然源自牯岭街,却不好称“摊”,毕竟有个店面,走道也不让乱堆书,真要叫,“旧书笼”相对合适,一格一格像鸟笼,密不通风。炎夏之时,又闷又热,逛一圈,汗流浃背,学生制服白衬衫湿透了,但毕竟“书真多,真便宜!”也就不好计较,有课天天报到,没课在家,心血来潮还去晃晃,反正学生车票便宜,30元60格随你坐!
台湾旧书摊灭绝后,本以为再碰不到,没想到20多年后,两岸开放交流,竟然有缘在彼岸到处寻逛。北京、南京、上海、福州、保定……不亦乐乎。
2000年前后的北京潘家园杂乱无章,四邻乡民都来赶集,书画古董旧书钱币……什么都有,真假难辨,但看运气与功力,淘到宝算你命好。潘家园列名“鬼市”,鬼市者,清晨4、5点摸黑交易,天亮即散,注过册的才准留下继续。鼎盛时期,光是卖旧书的,便有几百摊商,塑胶布地上一摆,书或叠堆或平放或插摆,便卖了起来。逛这摊子,腰力不好(老弯身),脚力不好(得蹲跪),肯定撑不久。
这种野集,混乱中求生存,矛盾中求发展,特别新鲜!那几年,只要进京赴会,必定报到。有一回寒冬,清晨4点多,起早赶集,朔风野大,冻得像根冰棍儿,在脏得一塌糊涂的小摊连喝两晚热豆汁,方见暖和。冷摊闲看,一路过去。北方人身高力大,自忖难敌,人多的即跳过。偶见转角一妇人摊前无人,弯腰才知都是洋文书,难怪乏人问津。蹲下翻弄,本本原版,装帧、纸张都好,要價极廉。匆匆拣了一套《蒙田随笔》,一套《白朗宁夫人书信集》便走了。回到旅馆,点检战利品,方才发现书前贴有备忘牌记,说明这是身世坎坷,命运多蹇的民国学者朱湘的藏书,当下大惊,想回去再找,却见窗外,天早大亮,阳光柔照,我们回不去了。
选自《大家》